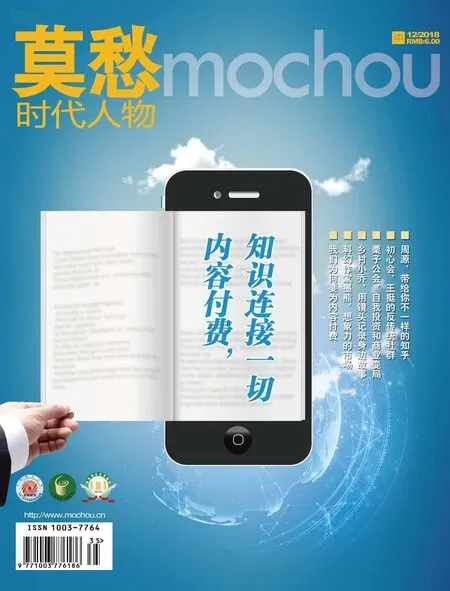最后的棒棒精神
文/十月
他們如螻蟻一般爬行,如高山一樣佇立,如細流一般蜿蜒,又如洪流一樣兇猛。
2018年,《最后的棒棒》成為紀錄片中的一匹黑馬,豆瓣評分9.7。片子的導演是毫無專業基礎的轉業軍人,用一年多的時間做了一名棒棒(挑夫),并拍下了這個即將消失的行當里的人與事。
用笨拙的方式,記錄一個時代
2014年1月19日,38歲的何苦按照退役前制訂好的計劃,把存款交給妻子,準時出現在租住的房屋——距離重慶市解放碑不到300米的自力巷53號,一個隨時要拆遷的破樓房。
軍官身份已成過去,何苦拜了一位有22年工齡的棒棒老黃為師,還給自己起了個有力的藝名“蠻牛”。一根竹棒、兩條麻繩,作為山城的特殊名片,挑夫在重慶有著一個再直接不過的名字——棒棒。在機械無法發揮作用的樓梯和坡地,棒棒們依靠體力支撐起這座城市最基礎的人工運輸網絡。
從重慶警備區政治部正團級軍官,變成出苦力的棒棒,何苦的父母萬般阻撓。何苦以一封家書告知父母:“我小學八年級的愿望實現了。”原來,兒時上學,何苦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小學六年級念了三年才勉強考入初中。當年,母親教訓他時,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再不好好上學,長大當棒棒。”
面對親朋好友的不解,何苦說:“一個沒啥文化的人老在那兒賴著,就會拖部隊建設的后腿,在我即將把背影留給軍營的時候,重慶街頭有一個佝僂的老棒棒也正在把背影留給城市。我去做棒棒,只是想踏踏實實回到勞動人民中間,踏踏實實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依托自身所長順便做點事情,自然再好不過。”
何苦以每月2000元聘了小伙張炎做攝影師。張炎不會用攝像機,何苦手把手地教。只跟拍了兩天,張炎說壓力有點大,何苦寬慰他:“見啥拍啥,我們就是要用最笨拙的方式追蹤一群背影,記錄一個時代,講述一種人生。這與藝術無關,全是力氣活兒。”
走近他們,了解他們的故事
上街第一天,扛著棒棒卻等不來活兒的何苦備受煎熬,紀錄片中有句話描述了他和師傅老黃當時的狀態:“我們就像兩個稱職的邊防戰士,一遍又一遍地在解放碑商圈例行巡邏,苦苦期待著掙錢的機會,卻一直沒有開張。”
下午1點,師徒倆終于等來雇主召喚。三件貨物100斤出頭,要走兩公里路才能送到目的地,工錢只有10元。挑了不到500米,何苦肩部的肌肉已經由酸麻變為刺痛。之后的時間里,兩人又接連完成了挑臘肉和挑飲料瓶的活兒,每次都有上百斤重。半天下來,何苦累得夠嗆。干完活兒,他算了算,兩個人一天的收入只有67元,其中的20元還是師傅徒手從廁所里掏狗勺得到的報酬。
棒棒們掙錢不易,吃飯盡可能地節省,經常一頓稀飯就能打發肚子。由于衛生狀況差,住進自力巷的第一個月,何苦從未在房間里做過飯。然而,一個月后,他最終突破了心理底線,不再考慮做的飯干不干凈,而且接連吃掉自己做的兩碗肉,喝光三碗湯。吃完,喉嚨里不停地往上冒油,他卻并不反胃,反而覺得這種感覺真好。
何苦漸漸與棒棒們熟悉起來,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天亮之前,一群光膀子的男人追著載貨的汽車狂奔,只為能搶到活兒。這個時候,手里的棒棒不再派上用場,他們會把麻袋扛在背上,或用自制的手推車推貨。實際上,從前一天晚上11點開始,批發市場所在的街道就已進入“戰備狀態”。滿載著衣服的貨車一輛輛駛來,棒棒們忙著追車扛貨,整條街人來人往,忙碌如戰場。他們追的不是車,而是對生活最真誠的夢想與渴望。夢想與渴望不同,但每個故事都足以讓人心底一顫。
何苦的師父老黃,因為曾被劃分為地主,一直討不到老婆,最后和一個帶著三個孩子的寡婦同居,并生了一個女兒。為了維持生計,老黃不得不出門打工,最后迎來的卻是另一個男人在這個家庭的合法入住,他只能帶著女兒另謀出路。女兒寄養在親戚家后,他做了棒棒,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女兒成家立業,有了孩子,買了大房子。女兒女婿很孝順,但老黃為了減輕女兒的壓力,幫助他們還清房款,推遲了放下棒棒的時間,沒曾想還沒達到目標就患了病。自力巷被拆遷后,棒棒們流落街頭,老黃身體不適,仍舊喊著不去醫院……
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婚,老甘一氣之下當了棒棒,一做就是二十五年。他喜歡制訂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掙的開面館的1萬元被偷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掙的準備開雜貨鋪的2.5萬元也被偷了。自力巷突然拆遷,老甘和棒棒們的生活物品被埋,老甘不顧危險,沖進廢墟里去挖,雙手鮮血淋漓。老甘目前的理想是賺足1萬元,回老家風風光光地辦60歲大壽。
隨著拍攝推進,棒棒們漸漸忽略了攝像機與何苦的存在。何苦跟工友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同甘共苦、同命相憐。他們身上或許有這樣那樣,在外人看來難以容忍的個性與習慣,可當他走近他們,了解了他們的故事,深深地理解了他們——他們對生活的熱情如野草一般堅韌,他們的勤奮、樂觀、努力、付出、掙扎與哭泣,讓人想起一次,內心的力量就厚實一點。
正是這些細節,使得紀錄片《最后的棒棒》實現了對真實的無限接近。然而一開始,何苦并不被信任。紀錄片播出后,二房東大石在一次交流會上吐露,為了驗證何苦是否真的來做棒棒,他曾在好幾個夜晚偷偷來到屋里,結果發現何苦一直都在。師傅老黃最初同樣對他的目的抱有懷疑,何苦苦笑著問他:“如果真是為了錢,有哪個騙子愿意吃這么大的苦來做棒棒?”

心存夢想,對生命保持信仰般的熱愛
從大寒到隔年立春,何苦的棒棒職業維持了一年多,這段生活最終呈現在13集紀錄片《最后的棒棒》中。2016年,這部片子贏得首屆金樹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短紀錄片獎”,豆瓣評分更是高達9.7分。
2018年8月17日,電影版《最后的棒棒》全國公映。有觀眾泣不成聲地說:“他們用厚實的肩膀,挑動了一個城市。”有網友寫道:“許多底層人物的寫照,真實感人,雖然片中講述的是重慶棒棒故事,卻也是全天下許多小人物的狀態。”有人一口氣看完13集,在夜里擦掉眼淚,寫下反思生活的話語。更多人聯想到的,是默默無言、辛苦勞作的父母。
透過這些一線觀眾的反饋,何苦更清楚地看到影片的社會意義。不光棒棒群體受到了更多的關注與關愛,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從電影中得到了一次心靈的滌蕩。
《最后的棒棒》上映后,何苦來到重慶萬州的一座棒棒公寓免費放映電影。他知道大家不舍得花錢走進電影院,即使是一部和他們有關的影片。何苦還想到了偏遠山區的老人和小孩,他們同樣沒有機會走進電影院。于是,他推掉了發行方為他安排的二十幾座城市的路演計劃,租了一輛二手面包車,天天往四川和貴州的大山里鉆,只為帶去免費的電影。
何苦因紀錄片而成名,他說盡管以后不能做棒棒了,但會繼續像棒棒們那樣,雙腳踏實地站在地上,心存夢想,誠實勞動,對生命保持信仰般的熱愛,做一頭堅韌而樂觀的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