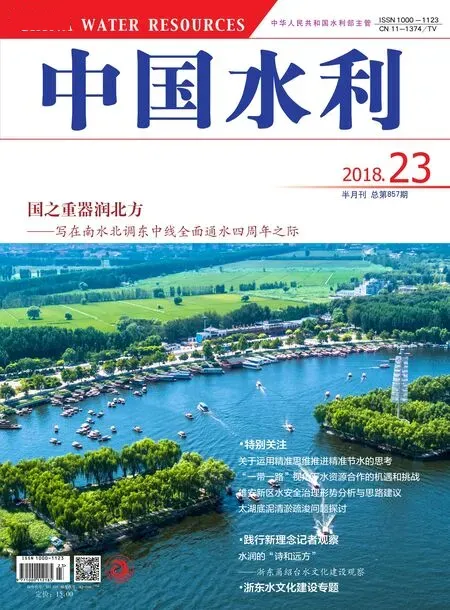論城鄉地下水系遺產發掘的展開

孟憲民: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中國港口博物館理事,曾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浙東水文化給我教益很多,近期是來自象山古城的。由《中國城池史》引縣治圖看,水系精妙,中部以九曲溝為特色。去探望時,見東西澄河長方池尚存,八卦墩位置有宋刻銘“淳熙三年”井。后讀到網絡(象山港論壇)文章《城記之思水》,文中寫道:“依靠下水道解決排澇,是一廂情愿。”“我們現在和將來該做些什么,繼續去填埋,還是恢復?如果恢復,怎樣來恢復?”6年前“老丹城人”已“點穴”值得討論的時代課題。
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城鄉遺產,是新時代的新要求,但落實不易,必須確定哪些遺產必須保存或修復。展開對城鄉地下水系遺產的調查發掘,浙東水文化研究有優勢,可爭取新突破。
一、何為城鄉地下水系遺產
城鄉建設范圍內已掩埋的一切歷史水系,包括古城古村內外的、原在地上地下的、在用非在用的、工程非工程的及毛細水,皆可稱城鄉地下水系遺產(以下簡稱水系遺產),它們是水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曾定義水文化遺產為:與水文化有關之一切遺產,不限于文化遺產而含自然。水系遺產能涵養生態,又很脆弱,任何建設都須十分關注。
我最初接觸這知識是30年前在曲阜孔廟,問及古樹為何都要支撐?答曰爛根子,附近水坑被填,排水不暢。長期以來,學界更關注地上建筑和水景觀,忽略作為生物存活要素的水系。現在都說城鄉建設要傳承歷史文脈,但僅重地面遺存,其實水脈也是文脈,最具說服力的形象表達非宋代贛州“福壽溝”、廣州“六脈渠”莫屬。
分布廣、尚豐富是水系遺產的特點。水系遺產過去的破壞多系填埋所致,較古建筑基礎并未像某些專家所說“蕩然無存”。這可引申出一個重要結論:對于所謂傳統風貌盡失的古城古村,不必喪氣,地下還有巨大潛力,尋根尋鄉愁可從水系遺產做起。
水系遺產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用性不明確、不明顯。在用遺址屬“活態遺產”,已漸得重視。福壽溝即典型,由于有城市暴雨淹人,曾引得各地對其進行訪問;其實它沿用的只一部分,大部分包括地表水塘,已被填埋,作用不明。其價值突出,完全有必要全面發掘與修復。
二、發掘的必要性與可行辦法
文獻研究、實地訪察等,屬于初步調查,在價值辨析的同時,重要的是覺察破壞的威脅,因為表面的知識也能構成保護措施的起點(《考古遺產保護與管理憲章》)。調查包括發掘,既是遺產,應能不挖就不挖,留給后人;但該挖不挖,連破壞程度都不知情,也是大錯,更何談保用。
以往水系遺產發掘鳳毛麟角,如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世界遺產中國大運河。與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同一天通過的《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指出:就人類平衡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的是保存合適的環境,以便人類與自然及其前輩留下的文明痕跡保持聯系,把當代成就、昔日價值和自然之美納入一個整體;遺產代表著財富,不僅由巨大價值者組成,還包括隨時間流逝而具有價值的“較為一般”者。大量水系遺產正因具有普遍價值,發掘更有必要廣為展開。
各地棚戶區、城中村改造現仍熱火朝天,城鄉出現大片空地或待拆房屋,正是發掘水系遺產的大好時機。然而,要讓可行成為現實,急需改革習慣做法。還如福壽溝,由大拆大建轉而“繡花”固然好,但若仍是注重打造“風貌”建筑及地下設施,福壽溝就難以發掘修復,甚至被糟蹋了。
精致地發掘修復,正是“繡花”,應成為建設的主角,若其僅前置于某些規劃設計,為其服務,要求過低,仍易被動。新時代要帶著新要求新課題探索新辦法,如:凡發掘必創造條件開放現場,做到邊發掘邊參觀,向民眾“表演”科學文化節目,并接受質詢和監督,使之成為城鄉生活有質量的標志和風景線;把發掘與修復聯系得更緊密,提前開展復原研究,并由民眾參與;最要緊的仍是決定留下什么,長期形成的水問題需長期解決,發掘出的遺跡可暫作綠地濕地展示,以待未來之水。
三、發展從事發掘的學術團體
“比起浩浩蕩蕩的基建隊伍來,那簡直是 ‘滄海之一粟’。需要和力量之間,相距得很遠。”中國首任文物局長兼考古所長、文化學術大家鄭振鐸先生,在社會主義建設伊始最關切發掘力量的增長和組織,曾說“建設人員應該不僅是工程師、建筑人員,同時也應該是考古工作者。”在他1958年飛機失事遇難后不久,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成立。新時代更需新發展,但很多考古人員對水系遺產“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任務”并不敏感。
國家文物局幾年前引進的《法國文化遺產普查的原則、方法和實施》一書,解答了不少困惑。該國給定“文化遺產”時間框架:下限為調查之時前30年,上限公元400年,因通常意義上“以前的遺跡屬于考古學的研究范圍”。填補“考近”發掘力量的缺欠是緊要的事,文化人科學人不該只作壁上觀,專業學術團體更應有大作為,從事發掘。這并非易事,別看民眾眼巴巴看著,由于觀念和利益固化,卻有得一搏。
水文化建設的提出是個重大創新,首次將自然屬性的水與文化合二為一,響應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主題,還表達了寬廣胸懷,使廣泛的跨領域合作有了良好開端。水系遺產發掘,需要多學科組織和社會協作,水文化研究會促成其事,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