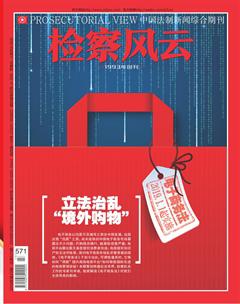文學能不能決出冠亞軍
瘦豬
唐人薛用弱有部小說集《集異記》,里面有一則故事。說的是開元年間,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齊名。一日,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登樓會宴。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辭多者,可以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吾之一絕句《芙蓉樓送辛漸》。”尋又一妓謳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吾之一絕句《哭單父梁九少府》。”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半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吾之一樂府《長信秋詞》。”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眾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紫衣貌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諸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與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值得玩味的“唐詩排行榜”
諸君聽來是不是有點像現在的流行歌曲排名?這個小故事不一定是史實,卻很值得玩味。我曾給一家報紙的閱讀版面撰寫過兩年的圖書榜評。表面上,圖書以口碑、銷量等綜合指標排出前十位,透明、公平,其實里面的水很深。類似的排名,常見的還有“人生必讀十本書”,“年度十大好書”,如是等等。古人沒有這么明顯,但從歷代唐詩宋詩選本的異同上看,也帶著優劣比較的痕跡。前幾年,唐宋文學專家王兆鵬教授出了一本《唐詩排行榜》,利用電腦的計算能力,以古現代選本、諸家點評、現代論文引用及網絡鏈接等考核指標,排出了唐詩前一百首。甫一面市,就引發了較大爭議。例如,李白《靜夜思》和孟浩然《春曉》僅排名第三十一和六十一位,陳子昂《登幽州臺歌》與杜牧《清明》居然名落孫山,頗令讀者大跌眼鏡。有媒體稱,“古往今來,在古典名著和普通讀者之間架橋的人非常多,采取的方法、推出的版本也數不勝數,卻沒有一個人采取排行榜這種違背常識常理的做法,既挑戰了讀者認知底限,又涉嫌夾帶了利益訴求。公眾的反感,事實上等于宣告了這個策劃不那么成功。”網友則發揮一貫的惡搞精神,“李白感到壓力很大,杜甫表示相信政府,王維認為排名神馬都是浮云,白居易承認奪冠有困難,唐太宗宣布本人及家屬不參加比賽。”當然也有不少支持者,認為用現代人比較習慣的接受方式來激發讀者對唐詩的興趣,于普及唐詩有功。唐詩究竟能不能排名?換言之,文學能不能決出冠亞軍?同樣專治唐宋文學的陳尚君教授給出了他的回答。
陳尚君首先厘清了科學排名和民間排名的本質區別。并指出唐詩(或文學)不能用西方“科學”的統計數據作為排名的絕對標準。就歷代選本來說,即使經過時間檢驗,“大家公認比較有眼光亦較公正的殷璠《河岳英靈集》,以常建為第一,李白、王維都在其下,杜甫沒入圍”,放在今天,引起的爭議不會比《唐詩排行榜》小。唐詩大多曉暢明白,無須專家點評。古人批點,皆附在選本之上,這就與選本標準重復了。唐詩在現代論文出現的次數與通常意義的引用率關系基本不相干,因為值得做論文的唐詩,多為“主題復雜、文本歧義、寓意不明、評價徑庭、歸屬有異和系年未定”,和詩歌的影響沒有一毛錢關系。陳尚君“對于網絡,最為懷疑”,“檢索試題和詩句會有很大不同,詩題、詩句常見與不常見又有很大不同。何況網絡經常提供大量類似或相關的檢索結果。”同樣是王兆鵬選編的刊發于《文學遺產》的一百首唐詩,與前者相比,不僅同一首詩位置不同,且有截然不同的十三首,“僅隔三年,何以如此差異?只能說參評數據取資不同。”陳尚君總結說:“排行榜是物欲盛行的現代社會商業文化的一部分,帶有很大程度的娛樂成分,不可不認真,也不可太認真。今人讀古詩,最大的意義是陶冶心情,增加學養,奔波不必在乎別人如何評議。”此觀點,我深以為然。
自古就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之說。文學(還有繪畫、雕塑等藝術)的好壞,主觀性太大,而且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人群,面對同一審美對象都會有不同感受和評判。陶淵明在《詩品》里,只是中品。白居易的名句“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要改成“晚來天色好”,才能在當時中下層人群里流傳。若論文學造詣,無疑前者佳,但這不能阻擋廣大人民群眾喜歡后者,正如民諺所說,“白菜蘿卜各有所愛”。
而我認為最值得深思的是陳尚君由此提出的幾個唐詩問題。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沒能入榜,為眾人詬病。陳尚君專寫一文《〈登幽州臺歌〉獻疑》論之。唐以后的歷代集子、選本,不見此詩,直到清人楊澄刻本《陳伯玉文集》(陳子昂,字伯玉)才有。此詩最早見于其好友盧藏用《陳氏別傳》,乃是從子昂詩句中引申化用而來。陳尚君論證,如是子昂所作,盧必收錄;若如盧所說,此詩為子昂登臺歌唱,而盧彼時正在終南山隱居,何以得聽?“那么只有一種可能,即此四句是盧根據陳贈詩內容,加以概括而成,目的是在為陳所作傳中將他的孤憤悲凄作形象之概括。”《登幽州臺歌》到底是不是陳子昂所作,那是學界的事,并不影響我們喜歡它。但也從側面說明,詩歌流傳歷史、接受歷史是極其復雜的話題。類似的例子,還有《春曉》為什么也可叫《春晚》,《靜夜思》存不存在中日版本差異等等諸多問題。陳尚君在《行走大唐》一書中皆有篇幅短小而論證嚴密的文章,給予解惑。
“行走”大唐的所見所聞
書中作者還特意寫了幾篇他人不太重視的唐代女詩人的文章,有著名的魚玄機、李季蘭,也有不為人知的張氏、趙氏,也有諸多文采飛逸的妓女。在古代,罕有女詩人能入選詩集,就連當代的《唐詩排行榜》也不見一個。陳尚君先寫女詩人身世,再論其詩,最后由詩論人,讓我們看到了一貫強盛的大唐的另一面。《心與浮云去不還,吹向南山又北山》結尾寫道:“在時代的劇變前,任何個人都很渺小,但統治者經常希望每一個微小的人,都要如事變平定后的結論般選擇自己的人生,否則就是叛逆,就要以你的生命來償還本來該統治者承擔的罪責。很不幸,李季蘭就此走完一生,大唐王朝繼續展示它的輝煌與偉大。”語氣沉重,寓意深遠。回顧歷史,哪一朝哪一代不是如此呢?
我們跟隨唐宋文學專家陳尚君“行走”大唐,看見唐朝的偉大,唐詩的魅力,也看見了偉大之下的卑劣,魅力之后的謎題。向來為人稱作英明賢君,從善如流的唐太宗,“也有極其荒唐、幾乎敗政的另一面。”陳尚君引《冊府元龜》史料,說李世民在繼嗣的國家大事上昏聵不堪,做出好幾次錯誤決定,為日后武則天登基埋下禍根。更有“妃嬪列于紗窗內,傾耳者數百人,聞帝與無忌等立晉王議定,一時喊叫,響震宮掖”的鬧劇,被陳尚君譏諷,“幾乎是后宮全程直播”,真可謂“稍遜風騷”。
文章即使沉痛,行文亦莊諧并用,《唐太宗的另一面》就是一例,反映了作者的匠心。縱觀《行走大唐》全書,概莫能外。全部文章都是陳尚君數十年治學的厚積薄發,“發”得能讓普通讀者興味盎然,乃是又一種功夫。近年來,以搞笑、大話等形式敘寫歷史的書籍,俯首皆是,但史實確鑿、見識獨到、文字優雅且不失幽默者罕有。這不禁讓人無比懷念十多年前出版的“大家小書”系列叢書。《行走大唐》是“青青子衿”系列之一,其風格亦如“大家小書”,這個優秀的出版傳承得以延續,令讀者滿意歡心。社會文化需要多元,既要有正襟危坐的高頭講章,也要有下里巴人的《故事會》,兩者若能無縫接駁,豈不皆大歡喜!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