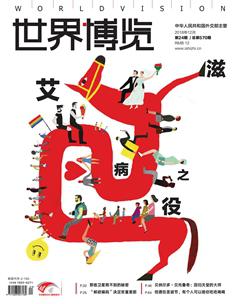失去大志的日本年輕人

《低欲望社會》
作者: [日]大前研一
副標題: “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
原作名: 低欲望社會:「大志なき時代」の新·國富論
譯者: 姜建強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8年10月
頁數: 260
定價: 48.00元
日本真正應該實施的最重要的增長戰略之一,就是教育改革。雖然美國有許多制造業外移,但依然是世界上創造就業機會能力最高的國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美國教育讓思維奇特的“突出人才”輩出,也因此能夠連續誕生高度專業的新興產業。比如,蘋果創始人史蒂芬·喬布斯(Steve Jobs),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共同創辦人以及特斯拉汽車(Tesla)的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推特(Twitter)與Square公司(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代替信用卡支付服務)創辦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等。這些新興產業并不是靠“天才”或“偶然”就能誕生的,它是培育這類人才的教育以及社會的產物。
反觀日本的教育,還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時代的原地踏步,培養整齊劃一的人才。學校教育只是要求學生一味地記住老師給出的“答案”。而老師的“答案”,則是來自文部科學省的指導要領。這樣的教育,就算能提供傳統產業的基礎勞動力,卻也無法培養出“突出人才”,更無法誕生高度專業的新興產業。
培養能挑戰世界的杰出人才
根據產業能率大學的調查,2016年新進公司的員工當中,最終人生目標是想當“總經理”的在9.5%與10%之間,只想當“部長”的比率為21.1%,想當科長的比率為10.7%,都有增加的趨勢。從結果看,他們整體缺失以企業領軍人物為目標的氣魄。相對于在公司出人頭地,他們更注重“長期且安心的工作”。
該大學在2015年還以公司人數超百人的上市公司擔任科長職的651名科長為對象,實施了一個調查。從調查看,99.1%的科長一邊擔任現場的管理職,一邊還要處理具體的一線業務。也就是說既是普通職員又是管理員。而在回答最終想尋求的職位時,有14.9%的人想“恢復成普通的職員”。與上回調查相比,高出1.4%,創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相比較辛苦多勞的中層管理職,還是看得見業績又相對輕松的普通職員來得更實惠一些。有這種想法的人增加了不少。
而在另一方面,如今日本年輕人當中的尼特族、宅族、單身寄生族,也成了家常便飯到處可見。周刊雜志還以“不工作,不結婚,不出家門的小孩”為社會問題而加以系列報道。日本的年輕世代會如此的“向內向下向后”,我認為,這個現象的背景原因是日本的教育制度。
為了讓日本人重拾以往的雄心大志,為了讓日本社會和企業再次騰飛,我認為只有徹底變革高中和大學教育。
迄今為止,日本在“追趕歐美,超越歐美”的口號下,戰前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戰后是加工貿易立國。規模和速度成了成功的關鍵。為了培養與社會化大量生產模式相符合的均質人才,我們實施的是只顧提升平均值的教育。另外,只要在工作中經歷過晉升與加薪,或者積累了相當實務經驗,就能成為一名像模像樣的上司,因此,也就沒有過多的負擔。
但是,如今的均質人才在世界上已失去挑戰力。工業國家的教育模式,那就無法戰勝包括中國在內的工資低廉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日本為了日后取勝,在教育上不應再量產均質人才,而必須培養能挑戰世界的杰出人才。50名學生的一個班級,哪怕只冒出一到兩名也行。為此,高等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其實,培養杰出人才的教育,在音樂和體育的世界里早已司空見慣。如作為結果來看,在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大賽上,諏訪內晶子、佐藤美枝子、上原彩子、神尾真由子獲得過優勝;在網球世界,錦織奎選手是世界排名第四,在跳臺滑雪方面,高梨沙羅作為日本選手首度亮相世界杯,并以史上最年輕的16歲4個月,成為個人綜合冠軍。
總之,普通教育也不能依據文部科學省指導要領,實施全國一律的均質教育,而是要像音樂和體育一樣,對將來有希望有潛力的孩子,必須施以“英才教育”。
日本的大學過多過濫,根據文部科學省2015年度的“學校基本調查”,目前日本全國共有779所大學,其中國立和公立大學有175所,私立大學有604所。依我而言,原本國立公立大學只要有10所就夠了。現在有這么多大學,真是毫無意義。國際競爭力強勁的瑞士和新加坡,國立公立大學也分別只有12所和4所,而人均GDP都超過日本,還能誕生世界級企業。
此外,來日本的大學留學的眾多留學生中,中國留學生占了一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留學生(即便是用日語授課的課程)比日本學生要來得優秀。其實,來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已屬二流的學生。一流的學生都去美國的一流大學留學了。連二流的中國留學生都比不過,這就是日本大學生可嘆的現狀。
歐美的大學校園,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比如,芬蘭從小學開始就推進英語教學,其結果就是現在的大學授課,大半都是用英語。這一舉措吸引了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大批留學生來芬蘭留學。簡言之,大學變成了全球化社會的一個縮影。雖然想在其中取勝存活難度會很大,但能夠提供學生與國內外優秀人才接觸的機會,提供在競爭中互相切磋琢磨的環境。這對培養杰出人才是極為重要的。
為此,日本應該減少大學的數量,縮小班級的人數。為了吸引世界各國的優秀留學生,應該不斷增加英語授課。與此同時,在小學或中學階段,對于顯示出自己興趣或才能的學生,必須配合其程度,請專業指導老師進行個別輔導。特別是進步快速的學生,讓其升到高中或大學,甚至讓其學習實業等級方面的知識。總之,必須導入量身定做的教學方法,而那些全國統一的指導要領等,應該直接扔進垃圾箱。
“畢業生的工資”決定學校的名次
不對。或許會有這樣的反駁,教育再生實行會議的建議,為今后所要實施的教育,融進了培養新型人才的理想。如全球型人才、理工科人才、能兼顧技術和經營的人才、創新的人才等。不過,恕我直言,這是不知經貿最前線的現場狀況,只是“桌上空談教育”的人們作出的摘要罷了。
不妨嘗試當著教育再生實行會議或文部科學省官員的面,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么,什么叫以人為本?”或許會有這樣的回答:“和誰都能干得很好,有協調性的人”,或“有日本人的品行,會英語,做事認真之人”。問題在于,如是這樣,日本根本出不了像創立蘋果的喬布斯或創立亞馬遜的貝佐斯那樣的“突破型人才”。
這個世界并不缺乏有協調性的人或只是很認真的人,缺乏的是能與喬布斯或貝佐斯匹敵的震撼社會的變革之人。
據我所知,至少在美國,大學的排名是以“畢業生的工資”來決定的。依據投資(學費)帶來的回報(畢業生的工資),基于能回收多少金額這個“投資利潤率”的純粹想法,來決定學校的名次。

2013年的一場日本畢業生招聘會
這也就是說,畢業生是否具有“賺錢力”,是否具有“價格品牌”,將會決定大學的“級別”。除非提高大學生的市場競爭力,否則排名就上不去。反過來說,只要日本企業不是按照每個人的能力發放初次任職的工資,日本的大學就進不了世界前排。
削減大學數量,增加職業訓練學校
如前所述,日本大學的數量過多過濫。所以,我認為應該削減大學數量,替而代之的是多增設培訓具體職業的學校。
目前在世界上較為強勢的是德國和瑞士。這兩個國家的大學錄取率都在四成左右,其他學生則是從高中時代直接邁入職業訓練專門學校。比如在德國,許多職業訓練專門學校都是“雙系統”制。也就是說,每周有兩天是在學校學基礎理論知識,另外三天是去公司實習。即便大學畢業后,22—23歲就業,基本上要有個五至六年的時間,才能具備實戰能力。但如果是畢業于職業訓練專門學校,20歲就養成了靠自己本領吃飯的技術力(參見圖表28)。
當然,進入公司時,也不全是工業類別,包含事務類在內約有350個職種,自己可以在其中選擇一門作為個人專門領域,更好地磨煉自己。假如在350個職種中,選擇了A這個職種,該職種又依能力分一二三四等不同等級,隨著排名的提升,薪金也同時提升。
最高等級是“師匠”。一旦成就了師匠,不但可以去其他公司教學徒,也可以獨立開業。這就是德國公司里的師匠制度。在社會上,職業訓練和高等教育具有同等價值。畢業于職業訓練專門學校的學生畢生所得,與大學畢業的學生畢生所得并無差異,因此社會非常安定。而且,即使失業也有再雇用制度。為了讓失業者能在其他職種上崗,政府提供18個月的免費職業訓練。
這是德國前總理庫爾特·施羅德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結果,德國成功地將原先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轉向了靈活多樣,盡管其薪金屬于世界最高水準,但仍具有國際競爭力,失業率也大都保持5%不到。
而美國的情況則是,雖然公立教育制度遭到崩壞,但私立學校作了很好的填補。特別是在美國的中西部,有很多水準很高的人文學院(一般設有基礎教養課程,學校規模較小)。美國的精英在這些學院學習哲學或歷史,養成廣泛的人文修養,然后再進入研究生院,打磨專門知識領域的“賺錢力”。研究生院的排名由學生工作時的起薪來決定,從這意義上說,研究生院又成了專注于賺錢力的“職業訓練場所”。
這樣來看,無論是哪一個歐美發達國家,也并非公平地對待每個人,而是讓有能力的人賺取他們能賺取的錢。然后讓他們對社會做出廣泛的貢獻,形成能夠應對信息化社會、知性社會的21世紀教育體系。與此相比較,從工業化時代至今還未有任何變革的日本教育,是如何落后于世界,是如何成了今日日本現有問題縮影的,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吧。
“不工作、不結婚、不出門的孩子”是其理所當然的歸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建樹與過去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的高等教育,應該盡可能早地把孩子放置于世界的荒波洪流中,感受沖擊。
沒有“雇傭不均衡”問題的德國
就德國的“雙系統”制,稍許再做些說明吧。
這是一套在企業實習培訓占三分之二時間,在定時制的職業學校學習占三分之一時間,二者并行實施二至三年的二元(雙系統)化的職業培訓。以一個星期為五個工作日來計算,在固定的課程計劃之下,三天用于企業實習,兩天用于學校上課。招生對象是完成了義務教育(15歲為止)的年輕人,或是畢業于“文理中學”(7年制或9年制的普通中等學校),并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年輕人。前者在18歲之前至少有兩年時間,可以得到專業人士的實地指教,磨練技術。
雙系統職業教學種類,并非都是汽車機電整合工、商業機械工、電氣設備工、涂裝工等藍領工作,也包括信息工程技術人員、旅館專職人員、商業事務性專職人員等白領工作。大約有350種公認培訓職種,由國家、州地方政府、企業、工會等組合而成的公共機構“職業教育培訓研究機構”(BIBB),進行具體而細致的運營管理。
在德國,孩子們的將來前途,從小學4年級的階段,就開始觀察其能力及適應性,并加以指導。孩子們從10歲左右開始考慮,自己是進文理中學然后考大學,還是進雙系統制或全日制的職業培訓學校,習得一技之長。到12歲時,就必須擇其之一。
最為受歡迎的是雙系統制職業培訓學校,與選擇文理中學的人數相比,比例是7∶3(采用同樣教育制度的瑞士是8∶2).
雖然從狀況上看,選擇哪一條求學之路,其畢生所得并沒有太大差異,但實際上相較于大學生,18歲就習得一技之長的人,似乎更能擁有安定的生活。
再來看日本。根據厚生勞動省發布的資料來看,2012年3月畢業的畢業生,其3年之內的離職率,大學畢業生為32.3%,高中畢業生為40%,初中畢業生則達到了65.3%。但在德國,由于有雙系統制的職業培訓學校,就業后立即辭職的事例極少。這是因為如前所述,孩子在10歲時,學校就指導其將來的發展,并讓他們學會自己思考。進職校后,又用上二至三年的時間,在企業進修(最后會有六成年輕人在進修公司就業)。這也就是說,年輕人與企業之間的“相親期”較長,因此不存在像日本那樣的“雇傭不均衡”或“黑心企業”等現象。毫無疑問,德國或瑞士正因為擁有這套職業教育系統,中小企業才能確保優秀人才的穩定。
戰后日本一味地仿效美國。但是像美國那樣活用優秀移民,打造用創造力決勝負的硅谷,日本又是學不來的。這樣一來,日本又只能模仿德國或瑞士,重拾古已有之的“匠人養成”制度,并以此來決勝負。
但問題在于,仿效美國,“濫造”大學的一個結果,就是日本進入了每兩人中有一人進大學的所謂“大學全錄取時代”。以往的初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畢業后進入城鎮工廠,由此支撐了日本“造物”技術力。但現在的這個結果導致原本的技術力難以維持與傳承。由此,日本的匠人技術,不久也將走向消失的命運。
支撐國家的是人。對國家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人才培養。盡管如此,日本還是量產了一大批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連今后靠什么吃飯都不思考,就直接踏入了社會。還有不少人到了三十多歲,還在摸索自己的人生究竟想做些什么。無法傳承“吃飯技能”的日本大學,如果不徹底實施一次打破一切的重大改革,用不了多久,這個國家就會消亡。對此,我抱有深深的危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