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務(wù)實(shí)”
將近二十年前,在楊振寧教授榮休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晚宴上,楊先生的老朋友戴森(Freeman Dyson)發(fā)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將他稱(chēng)為“保守的革命者”。為什么呢?因?yàn)樗m然破壞了宇稱(chēng)性守恒的思維結(jié)構(gòu),卻建立起由數(shù)學(xué)對(duì)稱(chēng)性支配的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chǎng),那日后成為物質(zhì)結(jié)構(gòu)根本理論的基石;此外,他雖然終身從事西方科學(xué)探索,卻仍然服膺于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所以,“革命領(lǐng)袖可以分為兩類(lèi):摧毀的比創(chuàng)建的多,建立的比摧毀的多。無(wú)疑,楊是屬于后一類(lèi)的革命者,……他愛(ài)護(hù)過(guò)去,盡可能少摧毀它”。這話(huà)講得非常中肯,因此深受楊先生欣賞。
戴森所謂“保守”,并不等于固步自封或者墨守成規(guī),而是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建設(shè)、改良,穩(wěn)步前進(jìn)之意,這從楊先生和夫人翁帆最近合作編著的 《晨曦集》(分別由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和新加坡八方出版公司出版)可以看得很清楚。集子里面的24篇文章剛好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演講、文章和座談?dòng)涗洠坏诙糠质撬麑?duì)媒體發(fā)表的談話(huà)和家人對(duì)他的印象、觀察;最后則是學(xué)者(包括他的學(xué)生)和作家對(duì)他的回憶、觀察。從這些文章我們得到的整體印象便是,楊先生一輩子講求進(jìn)步創(chuàng)新,在見(jiàn)解上卻極其穩(wěn)重、謹(jǐn)慎,甚至到了獨(dú)排眾議,乃至得罪同行的地步。
最顯著的例子,自然便是他基于經(jīng)濟(jì)和發(fā)展程度理由,堅(jiān)決反對(duì)中國(guó)造大型對(duì)撞機(jī)。為此他曾經(jīng)數(shù)度和國(guó)內(nèi)外眾多高能物理學(xué)家以及相關(guān)學(xué)者激烈交鋒,《晨曦集》收入的(文章編號(hào)16e)僅是其中一篇而已。我們絕對(duì)想不到的是,遠(yuǎn)在四十六年前回歸中國(guó)之初,他就已經(jīng)在一個(gè)大型座談會(huì)上,為同類(lèi)問(wèn)題對(duì)高能物理學(xué)的年輕學(xué)者大潑冷水(72a)。當(dāng)然,更令人驚訝的例子,是他在1980年國(guó)際座談會(huì)上對(duì)著一眾頂尖理論物理學(xué)家宣稱(chēng) (高能物理學(xué)的)“盛宴已經(jīng)結(jié)束!”那句令人震驚的話(huà)(A00g),以及早在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學(xué)院百年校慶討論會(huì)上對(duì) “未來(lái)基本理論”要“敲一下悲觀的警鐘”,“加入一些不諧的聲音”——那時(shí)他還不到四十,風(fēng)華正茂,離規(guī)范場(chǎng)理論被重正化,和粒子物理學(xué)“標(biāo)準(zhǔn)模型”的建立、驗(yàn)證還有十幾二十年!楊先生刻意提起半個(gè)多世紀(jì)前他這表面上并不中肯的預(yù)言,是要強(qiáng)調(diào),物理學(xué)還有大量“底蘊(yùn)”有待發(fā)掘,例如量子力學(xué)的波束塌縮、場(chǎng)論的重正化、粒子的質(zhì)量譜系等根本問(wèn)題之徹底解決仍然極其渺茫,甚至可能永遠(yuǎn)懸疑。因此他強(qiáng)調(diào),“我不是悲觀,我只是務(wù)實(shí)”(15a)。而務(wù)實(shí),應(yīng)該說(shuō)是“保守”的最高境界吧!這種態(tài)度不僅見(jiàn)于他所反對(duì)的,也同樣表現(xiàn)于他所贊同的發(fā)展方向。像他在清華高等研究院大力倡導(dǎo)凝聚態(tài)物理學(xué)(A17n),鼓勵(lì)余理華回國(guó)協(xié)助建造自由電子激光實(shí)驗(yàn)室(A17o),兩趟忠告趙午轉(zhuǎn)向加速器物理學(xué) (A17q),以及對(duì)激原子束的高度重視 (A00g)等等,都是務(wù)實(shí)態(tài)度的最佳例子。
當(dāng)然,楊先生的“保守”表現(xiàn)得最透徹之處是晚年的落葉歸根。他早年遠(yuǎn)渡重洋奔赴新大陸,投入物理學(xué)的廣闊天地之后成大名也飽受西方觀念熏陶,在那邊辛勞大半輩子更且加入了美國(guó)國(guó)籍,但終究還是要回到神州大地來(lái)方才能夠心安理得(A17c)。也唯有如此,他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認(rèn)同才得以從多個(gè)不同方面落實(shí),對(duì)中國(guó)前途的關(guān)注才得以盡心盡力。而回歸之后,他的忙碌奔波主要還是為了推動(dòng)物理學(xué)發(fā)展和教育改革。在這兩方面他都很冷靜地看到也指出了中國(guó)的落后和困難,但和許多致力于“批判”的知識(shí)分子不同,他同時(shí)也看到了中國(guó)體制的長(zhǎng)處和由此帶來(lái)的巨大希望 (A11q,A86k)。當(dāng)然,在這些高度復(fù)雜的問(wèn)題上他的見(jiàn)解未必完全正確,但他采取的,卻無(wú)疑是一種最務(wù)實(shí)也最保守的態(tài)度。
2016—2017年間阿爾法圍棋軟件打敗了所有人類(lèi)頂尖高手,轟動(dòng)一時(shí)。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因此對(duì)人工智能發(fā)生極大興趣,認(rèn)為在不久的將來(lái)它就有可能徹底改變世界。但楊先生對(duì)這個(gè)觀念卻完全不能夠接受。他認(rèn)為,即使再過(guò)半個(gè)甚至一個(gè)世紀(jì),人工智能恐怕都還趕不上一個(gè)小孩子的頭腦,它大概永遠(yuǎn)不會(huì)能夠和人類(lèi)比肩。“現(xiàn)在不是都熱衷于人工智能嗎?這些東西離小牛跟它母親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那還是差得很遠(yuǎn)呢!”他如此保守的態(tài)度到底是從何而來(lái)呢?歸根究底,就是來(lái)自對(duì)于大自然的敬畏:“我認(rèn)為我們永遠(yuǎn)不會(huì)把所有的宇宙的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都完全了解,……因?yàn)槿耸怯邢薜模钪媸菬o(wú)限的,所以沒(méi)法能夠完全了解。”(A17l)
他這句話(huà)自然立刻就讓我們想起牛頓晚年的喟嘆來(lái):“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樣看我,但對(duì)自己來(lái)說(shuō),我像是一個(gè)在海邊玩耍的小孩子,以不時(shí)找到一些特別光滑的石卵或者漂亮的貝殼自?shī)剩麄€(gè)真理的大洋就躺在我面前等待發(fā)現(xiàn)!”當(dāng)然,楊先生經(jīng)常提到的牛頓同樣是一位極其保守的革命者。他必須革命,因?yàn)橐⒖缭娇臻g,無(wú)遠(yuǎn)弗屆,無(wú)物能夠阻擋的萬(wàn)有引力,便要打破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牢牢地建立起來(lái)的笛卡爾“機(jī) 械 世 界 觀 ”(mechanical philosophy),其核心觀念便是,物體必須相互碰觸才能夠傳遞力量。然而,他又極其保守,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流行的代數(shù)方程式過(guò)于繁復(fù)抽象,自己發(fā)明的 “流數(shù)法”(即微積分學(xué))又不夠嚴(yán)謹(jǐn),所以寧愿選擇自古流行的幾何證題方式作為他畢生巨著 《自然哲學(xué)的數(shù)學(xué)原理》的論證和推理工具。甚至,在宗教上,牛頓也同樣是個(gè)保守的革命者。他一方面通過(guò)自己的研究,判定教會(huì)奉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三位一體”信條為根本錯(cuò)誤,另一方面又堅(jiān)信科學(xué)定律只會(huì)彰顯上帝之大能,《啟示錄》所預(yù)言的末日必將來(lái)臨,彗星則可能是上帝用以毀滅地球的非常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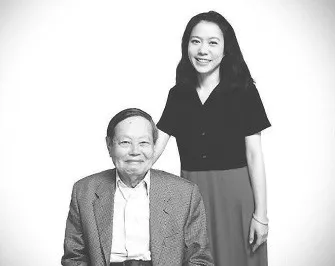
楊先生曾經(jīng)多次承認(rèn),自己非常幸運(yùn):從天賦、家庭、教育、事業(yè),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但我想,他覺(jué)得一生最幸運(yùn)、最高興的事情,應(yīng)該莫過(guò)于見(jiàn)到中國(guó)終于脫離屈辱,而日益富強(qiáng)起來(lái)。他在八十五歲的時(shí)候?qū)⒆赃x文集定名為《曙光集》,又在九五高齡將現(xiàn)在這本文集定名為 《晨曦集》。如在此書(shū)“前言”所說(shuō),這都是要表明中國(guó)已經(jīng)度過(guò)漫漫長(zhǎng)夜,行將見(jiàn)到旭日東升的意思。
同樣,牛頓也極其幸運(yùn),可以說(shuō)比楊先生還幸運(yùn)得多。他生于殷實(shí)務(wù)農(nóng)之家,寡母不解他的志向,卻由于中學(xué)校長(zhǎng)和舅父的斡旋,得以進(jìn)劍橋圣三一學(xué)院。當(dāng)時(shí)大學(xué)暮氣沉沉,毫無(wú)學(xué)術(shù)氣氛,教師大都尸位素餐,他卻碰上校內(nèi)唯一有理想有學(xué)問(wèn)的教授巴羅(Isaac Barrow),遂由于后者的賞識(shí)和另一位熟人的提攜,得以留校當(dāng)院士;不久巴羅更另謀高就,退位讓賢,他接任之后不問(wèn)世事,專(zhuān)心閉門(mén)治學(xué),以迄成就大業(yè)。這連串的碰巧,不是受到幸運(yùn)之神的額外眷顧是什么?更不可思議的是,在他出版《原理》之后短短一年,英國(guó)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政治巨變,舉國(guó)痛恨的信奉天主教的國(guó)君被逐,信奉新教的荷蘭執(zhí)政被迎立為王,那就是眾所周知的“光榮革命”。牛頓在大學(xué)里向來(lái)孤僻耿介,獨(dú)善其身,此時(shí)卻萌生兼濟(jì)天下之志,出來(lái)競(jìng)逐劍橋國(guó)會(huì)議席,并隨即當(dāng)選,諒來(lái)他其時(shí)心情,當(dāng)不止于見(jiàn)到曙光或者晨曦,而是天的大亮了!事實(shí)上,自此英國(guó)也就一帆風(fēng)順,在科學(xué)、文化、經(jīng)濟(jì)、政治、外交等各方面蒸蒸日上,以至成為歐洲最先進(jìn)和強(qiáng)盛國(guó)家——當(dāng)然,那還有待一個(gè)多世紀(jì)的努力方才能夠?qū)崿F(xiàn)。所以,楊先生很謹(jǐn)慎地以晨曦來(lái)形容他所見(jiàn)到的今日中國(guó),是非常之恰當(dāng)?shù)摹?/p>
我們無(wú)法知道,就對(duì)中國(guó)的長(zhǎng)遠(yuǎn)期望而言,他的幸運(yùn)是否也會(huì)及得上牛頓。不過(guò),在全球化浪潮鋪天蓋地的沖擊下(它目前在許多國(guó)家所激起的抗拒恰好說(shuō)明其力量之龐大),屆時(shí)國(guó)家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將蛻變成何種形態(tài),甚至這種競(jìng)爭(zhēng)是否仍然有意義,恐怕就沒(méi)有人能夠預(yù)見(jiàn)了。
(摘自9月28日《文匯學(xué)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guó)文化研究所榮譽(yù)高級(jí)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