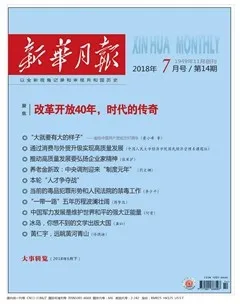國家賠償的算法
為什么申請三倍人身自由賠償?
2018年5月23日,遞交完國家賠償申請,律師屈振紅被問到這個問題。她的當事人、吉林男子劉忠林,因被指控犯故意殺人罪遭羈押9218天,不久前終獲無罪改判。
按照國家賠償法,人身自由賠償金以上年度全國職工日平均工資為標準,按實際羈押天數累計計算,并無三倍之說。
屈振紅的理解是,這個規定不合理、不公平:劉忠林每天24小時都在坐牢,怎能按每天8小時的工資標準賠償呢?
與之類似,在江西樂平案、錢仁鳳案等冤錯案件中,律師也都曾申請“三倍賠償”,但沒有一家法院予以支持。
刑事國家賠償標準偏低問題由來已久。中國政法大學一名教授曾對記者回憶,1994年國家賠償法通過伊始,便被稱作“國家不賠法”,有司法考試培訓講師開玩笑,“說(選擇題)不知道怎么選的時候,選最少的一項就對了”。
“國家賠償法(2010年、2012年)修改之后,情況已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評價,近年來國家賠償制度的程序趨于科學,標準不斷提高,但賠償的案件數量與實際支付金額,與學界預期仍有距離。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
2018年5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年度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經計算,上年度全國職工日平均工資為284.74元。
次日,284.74元被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賦予了新的身份——侵犯人身自由權的日賠償標準。這比去年高了25.85元,幾乎是10年前的3倍。
5天后,福建的趙璟婭收到一份法院的國家賠償決定。她的丈夫江先路卷入房屋租賃糾紛引起的一場沖突,被以涉嫌聚眾斗毆罪羈押,一審獲刑一年零三個月,二審被改判無罪。被羈押456天,換來人身自由賠償金11萬余元。
趙璟婭想不明白,丈夫原本是億萬富翁,投資著過億元的項目,而錯誤羈押帶來的損失與日平均工資的補償,明顯“不是一碼事”。
“人家是在里面坐牢啊。換作你,一天坐在里面,國家給你一天的‘工錢’,你愿意嗎?”燕山大學法學系副教授徐昀說。
普通人的困惑,也是法學家的困惑。
六年前,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學術論壇,北大法學院教授王錫鋅當時回憶,一名美國學者曾對他提出,用工資作為支付賠償標準,或會引發道德上的問題,即“坐牢、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民的一份工作”。
論壇上,曾參與國家賠償法起草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也回顧,當年制定標準時,有人覺得,該按照地區平均工資計算,但落后地區堅決不干;有人提出城鄉有差別,也被反對;還有人認為,收入高于日平均工資的人,賠償金額可以高一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國家賠償委員會主任陳春龍向記者解釋,統一的標準賠償符合中國國情,“不能說老板就多賠,農民就少賠。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老板和老板之間也不一樣”。
不少學者曾公開呼吁提高人身賠償標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的方案是做乘法,2至4倍的日平均工資“合理一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建議做加法,用日平均工資加上實際收入損失。
精神撫慰:冤死者賠最多
相較而言,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得更少,賠償標準也更難把握。
2010年,國家賠償法第一次修訂后,精神賠償才被納入法定賠償范圍。4年后,司法解釋為其劃出兩條線:最高,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作此規定的考量因素,既包括精神損害事實和嚴重后果的具體情況,也包括侵權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過錯程度、手段、方式,以及公民罪名、刑罰的輕重,糾錯的環節、過程,還有相關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陳春龍等受訪者均表示,精神損害撫慰金一般不好衡量,需要結合個案的實際情況。有學者認為,賠多賠少,和案件的輿論影響也有一定關系。
近年來一些冤錯案件的精神賠償突破了35%的上限。福建念斌案賠償總額為119萬元,其中精神損害撫慰金55萬元,占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86%;浙江張氏叔侄案、江西樂平案精神賠償比例分別達到69%、65%。
就數額來說,被告人已被執行死刑的,家屬獲賠最多。呼格吉勒圖案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為100萬元,聶樹斌案的130萬元則曾“創下紀錄”。
這種彈性,某種程度上被作為特殊彌補的空間。聶樹斌在羈押217天后被執行死刑,人身自由賠償金一項僅為52579.1元。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沒法多給受害人人身自由賠償金,但可以通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方式來達到撫慰的目的。”一名參與國家賠償法立法論證的學者對記者透露。
從思明法院、廈門中院到福建高院,趙璟婭一路申訴,精神損害撫慰金均止步于3.86萬元——這已到達35%上限,法院未再予突破。
趙璟婭覺得,家屬所受的精神創傷,遠非3.86萬元可彌補。丈夫江先路被羈押后,公司關門,損失數億,官司不斷。因為病情惡化,江先路在被改判無罪半年后就去世了。兒子的精神狀態也出了問題。
“自己‘判’自己,肯定賠的少”
在趙璟婭看來,法院不愿突破 35%上限,與她堅持要求追究司法機關錯案責任有關。3.86萬元的精神賠償決定,最早由思明法院作出。而其丈夫的有罪判決,也來自該院。
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公檢法均有可能是賠償義務機關。在中級以上法院內部,都設有國家賠償委員會。
“自己‘判’自己,肯定賠的少。”徐昀建議,類似案件可異地管轄,法院和有關部門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否則,即使賠得公正,也易被認為不公正。
應松年曾回憶,當年立法論證時,有人建議設立一個國家賠償委員會,吸納公、檢、法人員及學者、律師參與。還有建議認為,應將其設在人大之下。
這些建議未被采納。“(有人提出)學者、律師為什么要參加到國家賠償委員會里面?那不行。”應松年說。
在刑事案件中,公安可能錯拘,檢察院可能錯捕,法院可能錯判,該找誰?兩高2016年出臺司法解釋:以有罪方式作出最后處理的國家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換句話說,只需找最后出錯的機關,它得負責把案件前前后后所有的錯誤都管起來。
但還是有人不得不來回折騰。念斌所獲119萬元國家賠償,包括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兩項,而傷殘賠償請求一直未被支持。
2017年1月,最高法院駁回念斌的申訴:福州中院侵犯的是念斌的人身自由權而非生命健康權;如認為看守所違法使用警械造成身體傷害,賠償義務機關應當為公安機關。
“念斌提出傷殘賠償,法院卻以與其審判行為無關為由,讓他去找看守所索賠。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判死刑,就不會夾戴工字鐐銬。責任顯然在判決機關。”應松年在發表于《法治社會》2017年第2期的論文中寫道。
念斌的姐姐念建蘭告訴記者,2017年5月,念斌以福州、平潭兩級公安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的案件在福建高院開庭。目前,該院尚未就針對福州市公安局的賠償申請作出決定,申請平潭縣公安局賠償的案件,則已以程序性理由駁回。
刑訊逼供:認定少,舉證難
從張氏叔侄案、念斌案、陳滿案,到著名的聶樹斌案,最終的無罪判決均未認定案件存在刑訊逼供。
而證明自己遭受刑訊逼供或違法使用械具等情況,是當事人申請更多精神賠償和生命健康賠償的重要理由。
北京世紀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鐵雁介紹,他代理的吉林孫寶東三兄弟涉黑案再審開庭前,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調取了刑拘后進看守所前的入所體檢報告,顯示孫寶東雙腿內側有擦傷。
雖然最高法院再審認定孫寶東不存在涉黑犯罪,但判決載明無證據顯示其曾受刑訊逼供。
孫寶東因此未申請生命健康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拿到5.7萬元。“(若認定)受到刑訊逼供,撫慰金相對就會提高。”張鐵雁說。
張鐵雁曾從事十余年公安工作,他坦言,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來證明受到過刑訊逼供,是不可能實現的。
反之,需要賠償義務機關證明自身與事情有無因果關系的情形,目前僅有“被羈押人在羈押期間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兩種。輕傷、重傷等情況不在此列。
徐昀建議,擴大舉證責任倒置的范圍,“有關部門掌握整個監控資料,應當承擔證明責任。這在技術上很容易,成本也是很低的”。
財產損失:只賠直接損失
對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和精神三大類損害,主要支付賠償金。而涉財類案件的國家賠償方式,一般是返還財產或恢復原狀,通俗地說,就是要“物歸原主”。
但是,涉案財物往往在法院判決前已被處理,出現難以原物奉還的兩種情況:要么扣押單位不愿還,要么返還多少有爭議。
吉林商人牟洋名下的一家公司,2005年因偷稅等罪被法院處罰金250萬元。牟洋繳納了罰金,而吉林省公安廳先前多扣押的2020萬拖了十余年未返還。2016年9月最高法院國家賠償委員會作出決定,要求吉林省公安廳本息全付。
遼寧“黑老大”袁誠家,二審判決后的罪名和量刑都沒變,但財產部分作了改判,最主要的是17個其名下與黑社會犯罪無關聯的企業及賬戶資金被判返還。
2017年,遼寧省公安廳作出國家賠償決定,返還袁誠家超范圍查扣款本息共計6.79億元,媒體稱這創了國家賠償額的紀錄。
但袁誠家并不滿意,他提出的申請額高達37.3億元,最主要的就是“17家企業及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企業正常經營所產生的收益”,該項共計26億元。袁誠家的代理律師王殿學介紹,2017年9月向公安部提出的國家賠償復議申請目前暫無結果。
前述企業可能取得的收益,實踐中往往會被認定為間接損失。馬懷德表示,國家賠償法僅賠償直接損失,不賠償間接損失,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的損失,比如,一輛車被違法扣押了,而這輛車出門拉貨3年或許能賺幾萬元,但這部分錢是不賠的。
馬懷德認為,任何商業投資都有風險,不可能穩賺不賠,因此間接損失的金額不易計算。徐昀也推測,立法這樣規定,可能是擔心某些間接損失“沒有邊際”,容易“雞生蛋、蛋生雞,引起無限連環”。
“(賠償某些必然可得的利益)曾經討論過。”應松年認為,相關條文可考慮修改。
在多名學者看來,某些案例中的間接損失,是因辦案機關的違法行為(比如超范圍查扣)所導致。陳春龍多次提出,應進一步擴大刑事賠償范圍,以實際損害為準,盡可能彌補受害人遭受的損失。
“法定”的局限,“法外”的爭議
記者從多名冤錯案當事人及律師處獲悉,除了法定賠償,部分地區有關部門還會提供“法外補償”,補償數額有時能逼近法定賠償數額的二分之一。
拿錢的前提,可能是放棄追責、息訴息訪,各不相同。
“等賠償標準修改哪是這么容易的事?當事人等得到嗎?”一名曾代理冤錯案國家賠償的律師對記者訴苦,“私了”就是博弈的無奈結果。
“‘法外補償’是中國法治進程當中,成文法和潛規則的互動。”周漢華用“陣痛”形容這種現象,“它對案結事了、定分止爭起到了現實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從法治發展角度(來看),它破壞規則的權威性,也會導致(當事人之間)相互攀比。”
在徐昀看來,“法外補償”實際上可能造成納稅人的損失,“還是應該把標準提上去,把賠償公開化,這樣大家也沒什么說的”。
在法學界人士的設想中,國家賠償法還有盲區需填補。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只有改判完全無罪或部分無罪的受害人,方有資格申請國家賠償,而改判為輕罪的,不在法律允許申請的范圍內。
此外,幾乎所有的冤錯案當事人都會申請賠償申訴費、交通費、律師費等等,但獲得法院支持的是極少數。
馬懷德解釋,這是因為我國目前采取法定賠償原則,即按照法律規定的標準、方式和金額支付賠償金。申訴費等損害雖然實際發生,但因未納入法定賠償項目,通常難以獲賠。
馬懷德一直堅持,國家賠償法改革需遵循兩原則:一是合理賠償,有些實際損失雖未進入法定賠償范圍,但不賠償顯然不合理;二是有利于受害人原則,刑事司法機關的侵害對受害人而言是百分百損失,而國家支付的賠償金僅是九牛一毛,可賠可不賠時應當判賠。
一些法院正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浙江高院2015年曾發文指出,律師費等賠償請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不超過冤案受害人實際支出的前提下,可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適當賠償金額,以其他直接損失名義納入賠償范圍,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訴。
“下一步需要進行系統的改革。”周漢華對記者分析稱,不能孤立地談論國家賠償制度,只有在整體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轉變賠償義務機關的觀念和評價體系,提高公權力機關的權利保護意識,才能解決實踐中存在的“玻璃門”“彈簧門”現象。
(摘自5月31日《南方周末》。作者為該報特約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