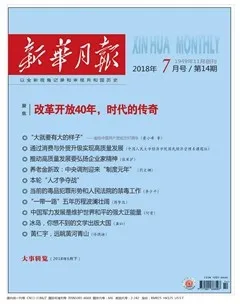美國對華戰略:從兩面下注到全面防范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對美外交在中國外交中的相對地位與所占比重已經明顯下降,中國對“周邊外交”的重視程度從2016年起已經超過了對“大國外交”的重視程度。但就國別外交而言,對美外交依然排在第一位,并具有示范作用。因此,準確判斷美國對華戰略干系甚大。筆者的基本判斷是: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從“兩面下注”轉變為“全面防范”,但并沒有把中國看成蘇聯那樣需要加以遏制的敵人(enemy),而是看作需要嚴加防范的對手(rival)。
“遏制”是個被中國學界與媒體濫用的詞匯,許多人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對此,筆者曾經在兩篇學術論文中進行了辨析(見《接觸中有防范,但沒有遏制——冷戰后美國對華戰略的再解讀》,載《太平洋學報》2004年第9期;《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5期)。這里想說的是,遏制是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采取的戰略或政策,其核心內容是:對蘇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對外擴張”與交往行為進行全面的“圍堵”與“隔離”。政治上美蘇各主導一個陣營;經濟上各主導一個“平行市場”;軍事上分別主導北約與華約;文化、教育、科技上兩個陣營之間很少往來。美國對蘇采取遏制戰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認為蘇聯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具有“擴張性”,將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與美國的生活方式。美國很清楚中國不是蘇聯,遏制戰略對中國不適用。因此,采取的是另一種戰略。
從尼克松訪華開始到2010年左右,美國對華戰略都是“兩面下注”,表現為既接觸又防范:期望中國對內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化”,對外融入現有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不會“另起爐灶”。2009年之前為“接觸為主、防范為輔”;2010—2015年調整為“防范為主、接觸為輔”;而在2016年之后,則轉為“全面防范”。以特朗普上臺后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志,美國不再寄希望于“改變中國”,而是把中國當作經濟上的競爭者(competitor)、安全與政治上的對手(rival)、一些問題上的潛在敵手(enemy),并為此制定相應的政策,具體表現為:聯手同盟國與伙伴國,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個方向對中國施壓。經濟上的關鍵詞是“對等(reciprocity)”;科技上防止中國留學生學習某些專業而動搖美國在相關產業上的優勢;文化上防止中國影響力在美國的擴大、防止中國動搖美國在這方面的產業優勢;安全上強化與盟國、伙伴國的合作,并構建新的安全機制(典型如美日印澳四國“同盟”以在“印太地區防范中國軍事勢力的擴張”),美國國會還通過《與臺灣交往法》,為強化對中國的制衡做好“法律準備”。
特朗普對于意識形態、人權等議題的興趣不大,對全球領導地位、軍事同盟的重視程度也是“二戰”后歷任總統中最低的。他的興趣主要在于美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相對獲益。美國并不想從經濟上把中國從世界體系中“隔離”出來,而是覺得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在與中國的“政府主導市場模式”博弈中“吃虧了”。特朗普想借助美國的整體實力優勢,一方面迫使中國“開放市場”,以利于美國的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等發揮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加大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難度。此外,為了確保美國的技術優勢,還采取多種措施:限制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與收購美國公司;限制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某些專業;要求中國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由政府出面打壓《中國制造2025》中確定的高科技產業。
從中國的角度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系,是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習近平主席甚至強調“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不過,隨著實力與自信心的提升,中國也展示了一些新動向: 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在對美關系中越來越多地“設置議程”;大力支持經濟全球化;為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總之,中國對美戰略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但美國對中國的整體定位是“對手”而非“敵人”,其對華戰略從“合作為主”調整為“競爭為主”,這是一個轉折,但未必是質變。它不同于冷戰時期美對蘇實施的“遏制戰略”,而是“保持接觸前提下的全面防范”。
(摘自《世界知識》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