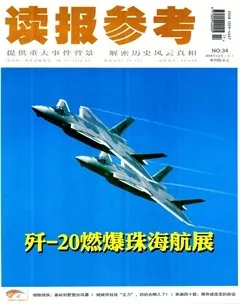歷史中國的“合”與“一”
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劃分了農耕與游牧的界線,自此,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中原農耕文化和北部游牧文化,成為一種廣泛的認知。但這種劃分是否能夠適用于歷史中國的各個時期,能否涵蓋歷史中國疆域內的各個地域?
閻崇年先生在其新著《森林帝國》中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華古代文明主要是由農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等五種文化形態構成的。而他更加著重探討了東北地域所屬的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孕育了滿一通古斯語族諸民族,造就了渤海、金朝、清朝等政權。
梳理東北地區的文化脈絡
森林文化,就我國的地域范圍而言,主要指的就是東北地區:就歷史上生活在這一地域的民眾而言,主要指的就是滿一通古斯語族諸族群。這些族群利用當地的森林資源,進行漁獵和采集,崇拜森林,所產生的文化就是森林文化。閻崇年指出,森林文化所具有的這些特點,從肅慎、勿吉、挹婁、靺鞨、渤海、女真直至滿洲,始終獲得繼承與發展,是一條貫穿3000年東北史的文化脈絡。
這條文化脈絡的存在回答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東北地區是否具有獨立的文化形態。以往,學界一般認為,東北地區并不具有獨立的文化形態,而與西北地區一樣都屬于草原文化的一部分。這種觀點的缺陷在于,既無法解釋東北地區文化與西北地區草原文化的顯著差異,也不符合東北地區的文化特征。但是,獨立的文化形態并不意味著文化形態的單一性與排他性。森林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善于吸收借鑒農耕、牧放等生產方式。明代漢人曾對女真諸部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行了比較描述,建州女真“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為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為生”。這是由森林文化所處地域的地緣政治決定的。
東北地區與以游牧為主的蒙古地區毗鄰,又與從事農耕的漢人、朝鮮半島居民長期接觸,故存在于森林文化中的生產方式包括農耕、牧放、漁獵、采集等多種。但漁獵、采集應是最初的生產方式,農耕、牧放是隨著與周邊文化的接觸而逐漸產生的,同時也是伴隨著森林文化族群逐漸南下的過程出現的。有學者已經指出,射獵、牧放和采集經濟,為女真社會經濟繁榮提供了有利條件。
重新審視滿族崛起的根源
赫圖阿拉位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赫圖阿拉村。閻崇年為了寫這本書。這些年曾無數次去往赫圖阿拉故城遺址。赫圖阿拉是滿語的漢語音譯,直譯作“橫崗”,也譯作“平頂山”,是一座地形古怪的小山城,三面環山,四面臨水,憑借天險,易守難攻。為什么是赫圖阿拉?因為赫圖阿拉可作為清朝的發源地:努爾哈赤以赫圖阿拉為基地,統一女真各部,創建滿文和八旗,奠定了清朝的基業。赫圖阿拉被清朝尊為“興京”,意思是清朝興起的京城。
《森林帝國》開篇便拋出一個歷史問題——“赫圖阿拉之問”,簡而言之,就是滿族如何以弱勝強地戰勝明朝,并建立起268年的統一王朝。作者通過多年的努力在書中對此問題進行了回答,可以用“文化”與“統合”兩個詞予以簡單概括。
清史專家曾指出:“滿族是17世紀初在遼東地區形成的一個新民族共同體。而構成其基本源流的那部分女真入主要來自東北北部和東北部的邊遠地帶。”
滿族先民的步步南下,在白山黑水之間形成了四個民族(女真、蒙古、漢族、朝鮮)、三種文化(漁獵、游牧、農耕)并存互動的格局。外部的多重文化對于滿族先民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這是滿族意識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清史專家提到了滿族先民在南下過程中不斷接觸其他族群、其他文化的歷史,也提到了多重文化對滿族形成所起的前提作用。
而所謂外部文化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促進了該地域的森林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文化史家認為,文化并不是在人類活動及其成果中被經驗確認的、作為技術方法及靜態特征的樣式,而是作用于人類一切活動及其成果中的“動態力量”。是促使樣式成立的“形成原理”。誠如上文所及,森林文化的重要特點就是善于吸收、借鑒其他文化,從而使得本文化與他文化互融互通。這應該是森林文化的一大優勢。借助這一優勢,滿洲依靠森林文化,統合其他文化,定鼎中原,實現了對全國的統治。
閻崇年認為。在中國兩千多年帝制史中。中華文明帝國曾表現為農耕帝國、草原帝國和森林帝國三種形態。其共同特征是以某一文化形態為紐帶,實現文化的多元一統。森林帝國是指以森林文化為紐帶,統合農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所建立多元一統的中華文明帝國。
白壽彝先生曾指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逐漸形成起來的,并在理論上提出了統一的四個類型,即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區域性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統一。歷史時期的全國統一則應該屬于白先生提到的前三種類型,而滿洲建立清朝統一全國的過程也屬于白先生這三種類型的范圍之內。滿洲實現了女真內部的統合,完成了東北森林文化的統合、同漠南蒙古(內蒙古)的統合,以及同漢軍、漢臣、漢儒的統合,形成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清定都北京后,原本是“以小制大”,經過“康乾之治”的文化統合,他們在滿、蒙、疆、藏、臺等地區,重俗尊教,因地制宜,逐漸與農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統合。
書中所述五個文化圈,占當時全國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滿洲從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占據主導或主流地位,取得了鞏固的地位。總之,清廷依靠“文化統合”而得以國祚綿延268年。后來外有列強入侵、內生文化分裂而逐漸走向衰亡。
重新看待中華民族的凝聚統一
閻崇年在《森林帝國》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統合的概念。他認為,從森林文化走出來的滿洲統治集團,善于利用政治、文化、宗教等政策,逐漸統合農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使得各種文化類型既能和而不同、各自得到發展,又能夠互通有無、促進多元文化共同發展,最終匯聚成為中華文明,各文化類型的族群最終凝聚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統。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指出中國有三大特征:廣土眾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歷史長久。翁獨健先生也認為。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是歷史上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的兩種不同方式。因此,民族同化、民族融合被長期認同為我國民族關系的主要存在形態。此外,“征服說”“漢化說”“涵化說”等說法也代表了學術界有關民族關系的認識。
閻崇年提出的森林文化善于吸收借鑒其他文化,具有包容性,而滿洲統治者則充分利用森林文化的優勢與特點,采用文化統合的政策。費孝通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指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體性,而不是其中某個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漢化,或者馬上實行‘民族融合’。”費先生的說法與滿洲統治者所采用的文化統合政策是相輔相成的。文化統合,在堅持統一的前提下,允許各個地域、各個族群在各自的文化系統內生產、生活。在對中國歷史的長時段觀察后。閻崇年指出了文化統合的優勢與不足:文化統合能夠促進政權的建立與鞏固;文化統合還需放眼世界,善于從其他文明、文化中汲取養分;中國歷代長期忽視海洋文化、森林文化是文化統合中的一塊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