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編印的語文選本教材
■龍美光
西南聯大是我國近代史上一所成就卓著的與抗戰相始終的著名戰時大學。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教授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在極端困苦中堅守學術精神,開創一代學術盛事。他們落腳昆明,以強烈的責任感,問學求知,傳道授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辦學成就。西南聯大教授們打破“部頒教材”一統天下的局面,自編自印語文教材,以此引領學術風氣,熏陶了一批成就卓著的英才。其中,聯大文學院編選的兩本旨在培養學生新文學氣質的語文讀本曾廣受聯大學子和學界稱贊。
《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試選新文學
二手書最受追捧的孔夫子舊書網上,一家舊書店以一萬元的高價懸售一本抗戰時期編印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其價甚昂,惜售之情躍然而來,又多少代表了后人對西南聯大的一種敬意。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維遹、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朱自清先生在一篇《論大學國文選目》的文章里,曾就大學國文選目問題詳作闡釋,其中就專門提到這本舊舊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他征引朱光潛先生的話:“大學國文不是中國學術思想,也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學,它主要的是一種語文訓練。”并指出,這句話代表了大部分人對于大一國文的意見。
抗戰前后,提供給大中學生閱讀的國文閱讀范本,以古典文學為主,有著“重古”的方向。而抗戰初起,開始有了“重今”的呼聲。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雖然重今的選本可以將文化訓練和語文訓練完全合為一事,這是最合乎理想的辦法,也是最能引起學生興趣的辦法,可是辦不到,一則和當時的中學國文教材沖突;二則和當時的大學國文教材也沖突。無論哪個大學都還不愿這樣標新立異。
由于西南聯大大部分文學教授對新文學有著特別的敏感,也就尤其注重大學國文課語文訓練與文化訓練并重的國文課程方略。于是,聯大開風氣之先,將語體文收在“國文選”里,也就形成了特色明顯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一書。
1939年6月16日,西南聯大文學院召開了大學國文選本會,確定聯大學生必修校本國文選本篇目,并由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余冠英、魏建功、王力、浦江清、羅常培等人進行編選。此書自1939年起編輯,連續幾年不斷編選和增刪,形成了至少三種版本。據聯大大一國文委員會主任楊振聲之子楊起、王榮禧夫婦回憶:“我父親在西南聯大的諸項工作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白話文引進大學課堂。這一舉措可謂開風氣之先,而且意義深遠。1938年西南聯大成立了大一國文委員會,我父親任主任委員。在他的主持下,開始編選《大一國文課本》的工作。這冊課本把反映新文學運動業績的現代文學作品——散文、小說、戲劇文學、文學理論引進大學國文教材,在中國現代教育史和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為編好這本課本,他頂著當時教育當局嚴重的復古傾向和壓力,發揚學術民主,發動全體任課教師推薦篇目,幾經斟酌、討論,并在使用中不斷總結、增刪,至1942年才最后定稿。國文成為全校一年級的共同必修課。以后,到了1944年,又從中挑選出語體文部分(即白話文),加上新編選出來的語體文,形成了《西南聯大語體文示范》,并交由重慶作家書屋出版。
對于這次國文選的編選,1942年7月1日,羅常培先生在昆明廣播電臺演講時指出:“一般大學生對于國文了解的程度和發表的能力,照理說,如果中等教育辦得好,應該都在水平線以上的。這時候在選材一方面,除去他們對于中國文學更有進一步的欣賞和了解以外,對于近二十年來的現代文學作品也不可以一筆抹煞。有人說,既然做了大學生,還看不懂白話文嗎?如果他喜歡新文藝,自己盡可以在課外去瀏覽,何必占授課的時間?況且這二十年來新文藝產量雖多,實質一方面卻是瑕瑜互見,未必都是成熟的作品。其實,照我看起來,白話文學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懂。就因為它是新興的文體,所以對于它的設計、結構、文字的運用、人物的刻畫等等,越發得詳詳細細地分析、解釋。你必得講過一回新文藝,你才知道它不容易講;你必得做過一篇新文藝,你才知道它不容易做!又因為它瑕瑜互見,不完全是成熟的作品,所以在選擇去取之間,格外得慎重,才不至于叫后進漫無準則。我們西南聯合大學所用的大一國文讀本經過3次改編,最后的一本包含15篇文言文、11篇語體文、44首詩、1篇附錄。這不過是一種試驗,當然有許多自覺或不自覺的缺陷。可是,當初選錄的時候,很小心地挑選這十幾篇語體文,無非想培養一點新文學運動里秀出的嫩芽,讓它慢慢兒地欣欣向榮,不至于因為缺乏灌溉就蔫萎下去。沒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國文讀本編訂委員會只選了50篇文言文、4首詩,其中固然經史子集色色俱備,可是把語體文刪得連影兒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正是新舊文學消長的樞機!”
筆者見到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并不是羅常培先生提到的第三版,但很能體現編選者的心思。其中共收錄詩文七十多篇,多注重于作品的思想之深和語言之美,且又不忘兼顧時代呼聲。從入選文章不難看出,其編選者以一片熾烈的家國情懷,與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校訓精神相呼應,真正將“語文訓練”與“文化訓練”相結合,開創出大學國文教學的新天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筆者閱讀的版本,除了上篇的古文,下篇的古詩,18篇語體文佳作不僅作為中篇入選此書(如前所述,少數幾篇也入選后來出版的“語體文示范”)且其文體既有散文、小說、演講,還有戲劇文本和文藝理論,免去了大學生閱讀現代文文范須自尋課外書的不便。因而,朱自清在《論大學國文選目》中說:“照作者的意見,青年人連新文言都不必學,只消寫通了語體文就成(西南聯大一年級生就限作語體文)。無論如何,重古的選本不可避免地使閱讀和寫作脫了節。多年來大學師生都感到這種困難;只有讓學生課外閱讀語體文的書來彌補這語文訓練的缺陷。——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收錄語體文,是比課外閱讀進了一步。”由此,這本古今結合的國文選,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中國現代大學校本教材的范本,成為同類課本的典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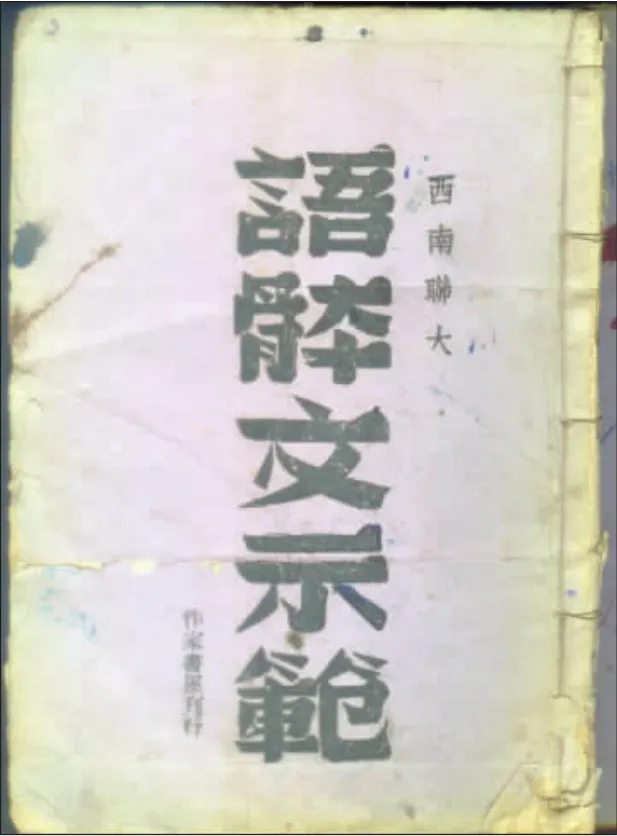
《西南聯大語體文示范》書影
多年前,汪曾祺先生在回憶西南聯大中文系時就曾這樣寫:“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么‘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只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后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系。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汪曾祺先生說得好,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這本書已經以《西南聯大國文課》的新面目示人,但愿讀者還能從中讀出這本書的趣味和精神氣,讀出一點新的“意思”來。尤其是語文訓練與文化訓練兩者趣味相成的編輯態度和語文理念,值得我們傾心效仿。
《西南聯大語體文示范》彰顯新文學
我在九年前第一次得見《西南聯大語體文示范》(書脊亦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語體文示范”)的廬山真面目,真有相見恨晚之感。無疑,這是抗戰時期由西南聯大的文學家們編選的一本倡導新文學寫作的老課本代表作。
經過四五年的醞釀之后,到了1944年10月,西南聯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為“能很適合的幫助學生習作”,為使大學生“能用本國文字恰當的表現他的思想與情感……養成他們中每一個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同時為培育大學生“以現代人的資格,用現代人的語言,寫現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學共同的立場上創造現代的文明”,以整冊篇幅“清一色”地編選出版了這本新文學色彩極為濃烈的“參考小書”。楊起、王榮禧回憶:“1944年,當時的教育部重申大一國文課必須采用部定教材。聯大沒有低頭,而是在使用部定教材的同時,大一國文委員會另編一冊《西南聯合大學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作為補充教材……這冊文選,后來改稱《語體文示范》。”
其由楊振聲先生撰寫但在書中并未署其名的“卷頭語”指出,這本小書“內容雖不完備——凡長篇及本校同人作品皆經割愛——卻都是能忠實于自己的思想與情感的作品;從這些作品發展開來,便是修辭立誠的門徑,便是創造中國文學的新途,便是中國文學走上世界文學的大路。”
這一選本的著作人有胡適、魯迅、徐志摩、宗白華、朱光潛、梁宗岱、謝冰心、林徽因、丁西林9人,完全打破了文學選本“生者不錄”的傳統。毫無疑問,“經割愛”的是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卞之琳、馮至、羅常培、李廣田、楊振聲等聯大文學家的作品(這些文學家的作品在西南聯大結束后則大多入編繼承了西南聯大文學院衣缽的昆明師范學院中文系1947年10月編印的《國立昆明師范學院語體文選》)。這一針對本校同人的自律,與其說是避嫌,還不如說是聯大學人對名和利的自覺看淡,從中更讓人感慨聯大學人為人學問的嚴謹。
此書收錄的各體作品計有13篇,收錄的各作者文章,則分別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節錄)》,魯迅的《狂人日記》及《示眾》,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節錄)》及《死城(節錄)》,宗白華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朱光潛的《文藝與道德》及《無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與李白》及《詩、詩人、批評家》,謝冰心的《往事(節錄)》,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以及丁西林的《壓迫》。這些按照“浸透作者思想和情感”為標準的入選文章,不少在今天仍是不朽的名篇。
從《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到《西南聯大語體文示范》,西南聯大的文學教授們將新文學的種子漸進式地、鄭重地播撒在聯大學子的語文訓練和文化訓練中,成為那一代大學生難以忘懷的記憶,這兩本書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珍貴文獻。
聯大新文學教學開花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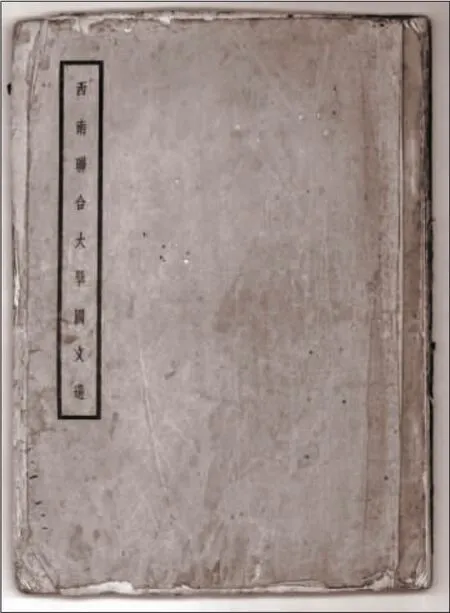
《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書影
當然,在新文學的倡導上,西南聯大并不是編兩本校本教材來突顯新文學的地位就了事,而是在編選教材的基礎上,將選本納入課程體系,并在實際的教學研究中,以課程建設全力滲透新文學思想,夯實新文學根基。聯大在昆明八年間,先后開設了大一國文(沈從文、吳曉鈴)、各體文習作(沈從文、余冠英、蕭滌非、李廣田、游國恩)、散文研究(朱自清)、現代中國文學(楊振聲)、中國小說(沈從文)等等諸多課程。其中以“各體文習作(一)”為例,其1945年度聯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學程說明書就指出,“本課程注重語體文之寫作訓練。在程序上,上承大一作文之基礎,并進一步作為文學創作之準備。至少于每兩周內在堂下作文一次。每周上課兩小時,除介紹中外作家之寫作理論及經驗外,并以作品為例,分析其寫作過程,批評其優劣得失,以引起學者自動寫作之興趣。”
在聯大文學教授們的影響下,聯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從詩界革命到新詩》(劉泮溪)、《抗戰后文藝發展情形》(林掄元)、《中國戰時文學》(王松聲)、《新詩的發展》(張燕傳)這樣的題目,涌現了聯大新詩社、高原文藝社、冬青文藝社、南荒文藝社、文聚社這樣的十多個新文學社團。并且,這些社團還是在聞一多、李廣田等文學家的指導下開展文學活動。在這樣的努力下,西南聯大產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新文學作家。聯大學生中,穆旦的《探險隊》(1945)和《穆旦詩集(1939-1945)》(1947)、鄭敏的《詩集(1942-1947)》(1949)、繆弘的《繆弘遺詩》(1945)等都已是新文學出版物中的珍品。由杜運燮和張同道編選的《西南聯大現代詩鈔》(1997)、李光榮編選的《西南聯大文學作品選》(2011)等選本集中呈現了聯大新文學教育的成果。可以說,聯大已成為新文學滋生的土壤和大西南重要的新文學陣地。
“話從哪里說起?等到你要說話,什么話都是那樣渺茫地找不到個源頭。此刻,就在我眼簾底下坐著是四個鄉下人的背影:一個頭上包著黯黑的白布,兩個褪色的藍布,又一個光頭。他們支起膝蓋,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墻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簡單的東西:一個是白木棒,一個籃子,那兩個在樹蔭底下我看不清楚。無疑地他們已經走了許多路,再過一刻,抽完一筒旱煙以后,是還要走許多路的。蘭花煙的香味頻頻隨著微風,襲到我官覺上來,模糊中還有幾段山西梆子的聲調,雖然他們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鐵紗窗以外。鐵紗窗以外,話可不就在這里了。永遠是窗子以外,不是鐵紗窗就是玻璃窗,總而言之,窗子以外!…………”(林徽因:《窗子以外》)
——七十多年前,西南聯大的同學們就讀著這樣美的文字進入大學生活了。汪曾祺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一文中深情地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文化熏陶下,才孕育出了汪曾祺、穆旦、鹿橋、杜運燮等一批成就卓著的西南聯大作家群。
七十多年時光轉瞬而逝,在新文學已廣泛影響于今天社會文化生活的時候,我愿以本文向編選這兩本小冊子的西南聯大文學院的教授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