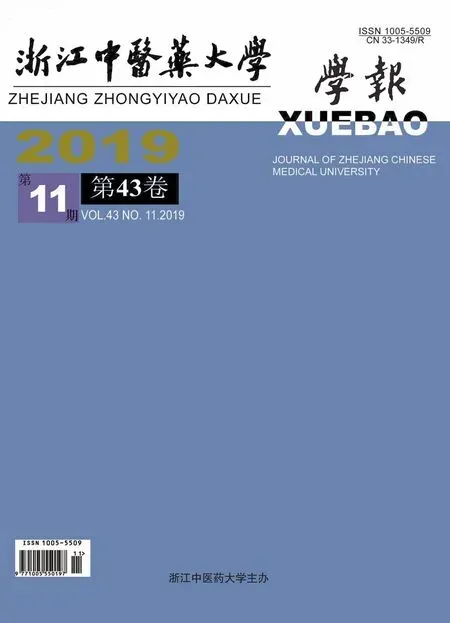《傷寒論》“方證辨證”思想探討
長春中醫藥大學 長春 130117
“方證辨證”思想是傷寒學術流派中的方證派的辨證思想,其在《傷寒論》的研究、學習和應用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和獨特優勢,是準確運用經方的一條捷徑。從“方證辨證”角度解讀《傷寒論》的思想古即有之,隨著近年來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方證派學術思想受到了中醫界的廣泛關注,不斷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涌現出來,但目前“方證辨證”仍存在諸多爭論。筆者對“方證辨證”的研究方法及內涵、歷史源流、現實意義等作一總結,并分析其發展趨勢以及存在問題,現論述于下。
1 歷史沿革
研究方證辨證思想歷史沿革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確定方證辨證思想古即有之,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二是探尋其形成的理論淵源、發展變化、歷史背景、各家學說等,有助于總結其研究思路與方法。
學界有人認為方證辨證思想源于神農時代,還有人認為其源于《五十二病方》,但中醫理論體系和辨證論治思想在這兩個時代尚未形成,這種說法過于牽強。方證辨證思想應源于張仲景,在《傷寒論》原文中多處以方名證,如“桂枝湯證”“柴胡證”“柴胡湯證”等共十一處。在原文中論到“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為“方證辨證”思想之源頭。
唐代孫思邈[1]精研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數十載,將其按“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方法重新編次并載于書中,為“方證辨證”思想打下了基礎,后世學者皆仿此“方證同條”之法。
南宋楊士瀛[2]在其書《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中采集《傷寒雜病論》中所述主要病癥,并加以總結、概括,后列每一病癥在六經中之因機證治,并附方藥,做到“對病識證,因證得藥”,此為“方證辨證”思想之體現。朱肱[3]也在書中提出“藥證說”,書中云:“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可作為“方證辨證”之詮釋。
金代成無己[4]所著《傷寒明理論》的“方藥論”中,選《傷寒論》中二十首方劑,以先論主治再論方劑的方法加以闡發,可視為發展“方證辨證”思想的一員。
到了清代,柯琴、尤怡、徐大椿均在著作中對“方證辨證”思想有所闡述。柯琴云[5],“見此癥便與此方,是仲景活法”。徐大椿[6]在書中論到,“不論從何經而來,從何經而去,而見癥施治,與仲景之意無不吻合,豈非至便之法乎”,此皆為對“方證辨證”思想的精辟論述。
近代醫家曹穎甫、陸淵雷、張錫純、惲鐵樵等人均認可“方證相應”,亦在著述中有所論及。現代醫家劉渡舟[7]曾論“認識疾病在于證,治療疾病則在于方,方與證乃是傷寒學的關鍵”,胡希恕[8]認為“臨證有無療效,決定于方證對應與否”,黃煌教授[9]則認為“臨床上重視抓主證,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去是藥”。
綜上所述,“方證辨證”思想在漫長的中醫歷史中早有根基,在《傷寒論》研究中亦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歷代名家均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思想進行了不同的分析和闡述。誠然,各家論述皆不全面,各有偏頗,亦少有對“方證辨證”思想直接、具體、全面的闡述,多在論述之中透露。雖然如此,但仍在思想中向后世傳遞著“方證辨證”思想的火種。現代之后學有以為“方證辨證”思想源自日本者,實在錯誤。亦有認為“方證辨證”思想自胡希恕、黃煌等醫家始者,大錯特錯。
2 方證內涵
明確方證辨證相關內涵,是研究方證辨證的前提。方證辨證的內涵,主要是“方”“證”兩個概念,學界尚未有被廣泛認可的關于“方證辨證”思想的定義,文獻中多稱之為“方證對應”“方證相對”等等,其中少部分文獻對上述詞匯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釋說明。
李賽美教授[10]及其弟子林士毅[11]等,對傷寒學術流派的形成及發展、基本狀況、傳承等進行了長期深入的研究,認為“方證對應派”之方證對應即“有是證用是方”,臨床證候只要與仲景的描述相契合,便可放膽使用而不必強求舌、脈、癥的面面俱備。其中“證”并非證候的概念,乃是癥狀、天時、地域、體質等所組成的辨識疾病的“證據”,并認為“方證對應”不強調病機,甚至忽視病機。
冷偉[12]、簡瑜真[13]等認為,方證辨證是指在對脈癥等臨床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比較、鑒別的基礎上,辨別臨床病證與方劑的對應和契合關系的方法,也稱為“方證對應”[14]。
武開放、楊幼新[15]認為,所謂方證,簡言之,就是方劑的適應證。
黃煌[16]64認為,“方不僅是指藥物的特定組合,而且指具有明確應用指征的藥物”,故還提出了“藥證”。
季之愷[17]認為方應從法和術的層面理解,方不僅就藥物的配伍而言,而且也是治則和治法的具體體現,有方法的意思。
胡小勤[18]認為方是指具有特定藥味、藥量、劑型、用法等內容的用藥形式。還有學者認為方僅指《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中所載方劑,或唐以前的經典方劑,等等。
方證辨證中“證”的概念更是眾說紛紜,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張文選[19]認為證指特征性癥狀,但未明確特征性的內涵,也沒有明確癥狀的概念是否包括體征。黃煌[16]65教授認為證指用方的指征和證據。此論涵蓋了前一點,但仍欠缺明確的定義,不利于研究工作的開展。主流觀點認為方證辨證之證是病機概念,或指疾病某一階段的理概括,如脾陽虛證、腎氣虛證。
方證辨證既然為辨證方法就應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義,不應僅限于仲景方或唐以前的經典方劑,其思想適用于經方也適用于時方。但是,時方多不似經方之療效確切、主治明確、配伍精當,不易形成確定的“方”“證”關系,故此思想多于經方中應用。葉超[20]等人所著“杏蘇散方證論析”及宋成城等人[21]所著“溫膽湯方證芻議”,都是基于“方證辨證”思想對時方的研究。方也不可歸結為特定的用藥形式,這種定義太過寬泛,因為任何方劑必然有其藥味、藥量、劑型、用法。方應指經過長期驗證、切實有效、配伍嚴謹且相對較為固定的方劑,其中《傷寒論》《金匱要略》所載方劑即為最典型代表。
“證”指“方”所治之主證,即與“方”具有確定的契合關系的一組癥狀或體征。“方證辨證”思想,即指辨“方”之病機,辨病機之主證,方-機-證相貫,見“證”知方,因“方”識證。“方”針對確定之病機,病機又體現為某些特定的癥狀(即主證)及某些非特定癥狀(即兼次證、或然證),如此“方”與“證”之間便可建立確定的關系。臨證時通過四診等手段搜集疾病資料并加以辨別,得出主證,因證施方,隨證加減。其中亦有某癥狀之特藥、特方之特例,另當別論。
“方證辨證”思想不應以“方證對應”來表述,也不應限制于對《傷寒論》的研究。“方”與“證”之間不是“對應”二字字面上透出的對號入座的關系,兩者中間有一個核心的“辨證”過程。若只是單純的對應關系,那將淪為不可復制的經驗積累,丟掉其思想內核。再者“方”“證”之間應是確定關系,否則必難有定見,難取定效。
3 研究方法
歷代醫家利用“方證辨證”思想研究經方時方法不一,各有優勢。其發展至今,總體來講方證辨證的研究方法可分為以下兩類。
3.1 傳統研究方法
3.1.1 以方類證,證以方名 以“方”為核心,歸納、總結、分析其相關原文,得出其針對之病機及主證,臨床根據病機或主證開具處方,稱為“以方類證”。此法易于掌握,便于經方脫離外感熱病束縛、擴大應用范圍,但是容易忽略病機,產生機械地對號入座的錯誤。
3.1.2 分經審證,方隨證變 根據六經的主證將疾病歸于各經,再將六經病進一步細分為“經證”“腑證”等,最后每一證對應處方,稱為“分經審證”。此法注重各證內在聯系,便于判斷傳變及預后,但是容易局限于外感熱病,難于準確判斷疾病歸經,必須經過長期系統學習。嚴格來講,不屬“方證辨證”范疇,應為六經辨證的一種。
唐慶[22]在其論文中提出:以方劑為綱歸納相關條文;著重抓方證的主證;注意類似方證的鑒別;注意精析原文,理清辨證思路;將變化了的證候與六經主癥作對照,反映病機的相應變化,從而知常達變[23]。此論為兩種方法有機結合提供了思路。
陜西中醫學院曾福海[24]認為找出每一個方證的病因病機,是方證辨析的重要內容之一。楊國棟[25]認為方證運用要注重區別病機異同。兩位前輩說出了方證辨證研究方法的關鍵,即病機。沒有病機,方證辨證及就會陷入對號入座、守株待兔的尷尬。
3.2 現代研究方法 現代研究方法中逐漸出現了大數據統計學、數學模型以及“熵”等方法,雖有其顯著優勢,但多數學者對此知之甚少,更沒有先進的硬件和軟件設備作為研究基礎,有條件使用此類研究方法的學者也微乎其微,無法廣泛使用。多年來此類研究方法的結果并未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可,目前來看,意義不大。
“方證辨證”研究方法應以“以方類證”為主,結合三陰三陽之六經,以病機為核心,以陰陽變化統領病機。將與“方”相關原文歸納總結,以原文為基,參考歷代名家注解及真實可靠的醫案,分析原文,得出各“方”之病機(如桂枝湯之病機為陽浮而陰弱)、主證、兼次證、或然證。亦可以方劑組成反推其病機和主證等,但須以與《傷寒雜病論》同時代之《神農本草經》及相關注解為依據。再將各方主證與六經主證對照,明確其中變化,做到突破六經而不離六經。主證即主要矛盾,兼次證屬從屬地位,為次要矛盾。臨證時主要矛盾解決,次要矛盾自然解決,或然證為加減依據。
4 應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4.1 不可對號入座 “方證辨證”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不知方之旨與方之用,實存有“刻舟求劍、按圖索驥”之弊,切記不可丟失病機及辨證過程的核心。
4.2 辨證要準確 “方證辨證”的特點就是強調“方”與“證”的緊密聯系,必須抓住“獨處藏奸”之主證,以病機貫穿,如此才能例不虛發[26]。如徐靈胎[27]所說:“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
4.3 遣方精當,加減有據 加減用藥必須有據,否則力不向一處,難以取效,經方之精,不可小視。加減用藥要對證,而不是對癥。經方的方證運用于臨床已有千年的歷史,不可隨便加減,多余的加味,往往造成畫蛇添足[28]。
4.4 針對病機,具體分析 主證實際上是病機的特異反映,在臨證時不僅要看主證,更要看病機。有時雖癥狀相似但病機不同,有時主證不明顯,但只要看準病機即可大膽應用。辨明每一主證背后的病機,方可擴大方劑所治病證的范圍。
4.5 注意理清與其他辨證方法的關系 方證辨證看似是以“證—方”的形式分析疾病,但實際上是“證-機-方”的形式。如無病機,方證辨證就如同守株待兔、刻舟求劍失去了生機。而要準確把握病機,就離不開各類辨證方法。辨方證是繼六經八綱辨證之后更具體、更詳細的辨證[29],沒有六經八綱理論指導為前提,就不能正確把握方證[30]。而六經辨證與其他辨證方法實際上是相通的。
5 現實意義
5.1 臨床 主證背后是病機,病機之后是針對性的“方”,臨床只要抓準主證,即可快速認清病機,遣方用藥,無需套用各種辨證方法的繁雜程序和運用多種辨證方法,避免了各種思想帶來的分歧和干擾,加快了辨證論治的準確性和速度。
5.2 教學 曾福海、何大群[31]、錢峻[32]等人將“方證辨證”應用于《傷寒論》的教學中,反復實踐體會,認為方證教學便于學生快速、系統掌握經方,更好地學習其辨證論治的精神本質,為臨床打下理論基礎,不失為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已得到推廣應用。
5.3 促進診斷與鑒別診斷的發展 《傷寒論》是有效而可操作的診斷“金標準”。經典方劑的構成是相對不變的,所以方證也是相對固定不變的,這有利于中醫診斷標準和鑒別診斷的發展。
6 結語
方證辨證做為傷寒學派的辨證方法,具有其自身的歷史源流、內涵、研究方法、現實意義等。發展至今,其已不僅僅是傷寒學派的辨證方法,更可延伸至后世經典時方,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認識病證、學習方劑的思想。“方證辨證”思想以其準確的診斷、精確的用方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近年來研究此思想的學者逐漸增多,推動了“方證辨證”思想的發展和廣泛傳播,其為中醫的臨床、教學、診斷及中醫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提供了思路。
“方證辨證”思想概括起來即是:每一首經典方劑都對應一個確定的病機,而此病機往往反映為一組特異性的癥狀和體征,即證,如此方、證便形成了較強的契合關系,臨床上見證知方,因方識證。這種思維方式就是“方證辨證”思想。
方證辨證發展至今,研究逐漸細化,如黃煌教授提出的“藥證”概念,又如方證治法分類研究及方證治法用藥規律。亦呈系統化理論化趨勢,如《傷寒論》方證要素對應研究。更有學者借用現代的統計學、數學模型等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如《傷寒論》方證對應規律的可視化研究、《傷寒論》方證對應規律的數學三維解析。
研究中發現文獻中多以某方所契合的某證的研究或單一病癥所涉諸方的分析,而幾乎沒有文獻對《傷寒論》所述諸癥及對各癥所涉諸方進行全面分析、整理和總結,當某證對應多方時就會面臨尷尬。另外,“方證辨證”思想缺乏系統全面的總結和認識,更缺乏準確的、被廣泛認可的定義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