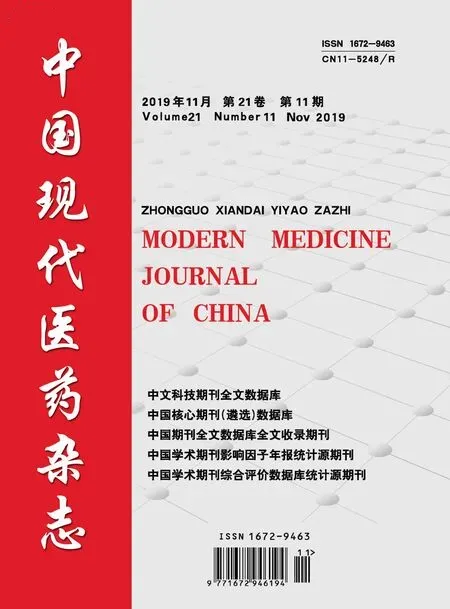抗甘氨酰tRNA合成酶抗體陽性的抗合成酶綜合征2例并文獻復習
朱雪梅 王占奎 劉愛維
1 病歷資料
患者,女,47歲,因“乏力7年,對稱性多關節腫痛2年,憋喘1年,加重3月”于2019-05-22入院。患者7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乏力,肩背片狀皮疹,外院查肌酸激酶(CK)大于6 000U/L,診斷為“皮肌炎”,服用“糖皮質激素”治療,病情穩定;2年前出現雙腕、雙肘、雙肩、雙膝、雙踝關節腫痛,自服激素治療后好轉;1年前間斷發熱,最高體溫39℃,伴咳嗽、咳痰、憋喘,乏力,CK 692U/L,C 反應蛋白(CRP)79.50mg/L,紅細胞沉降率(ESR)66mm/h,胸部 CT示:雙肺間質性改變,予抗生素、激素治療好轉后出院。3月前出現刺激性咳嗽,嚴重時語不成句,伴發熱,抗感染治療效果欠佳來診,查體:激素面容,雙肘關節伸面暗紅色斑疹,伴白色鱗屑,雙手雷諾現象,雙肺可聞及Velcro啰音,四肢肌力4~5級。輔助檢查:谷草轉氨酶(AST)40.5U/L,CK 1 466U/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57.76U/L,羥丁酸脫氫酶(HBDH)339U/L,CRP 32mg/L,ESR 53mm/h,B 型鈉尿肽(BNP)90pg/ml,鐵蛋白(SF)1 383.63ng/ml,血常規、余生化、類風濕因子、抗環瓜氨酸肽抗體、抗核抗體、抗可提取性核抗原抗體、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補體、肺癌系列、凝血、病毒、真菌、支原體、降鈣素原等指標均未見異常。血氣分析:酸堿度(pH)7.43,氧分壓(pO2)66mmHg,二氧化碳分壓(pCO2)41mmHg。胸部CT示:雙肺內多發片絮狀及網格狀密度增高影。肺功能:中度限制性通氣功能障礙合并小氣道功能障礙,CO彌散量重度減低,FVC 62%,FEV1 61%,DLCO 26%。肌電圖提示肌源性損害。心臟彩超:肺動脈收縮壓24mmHg,LVEF 72%,微量心包積液。入院第6天肌炎抗體譜結果回示:抗 EJ抗體 IgG+++,抗 Ro-52抗體 IgG+++。診斷:抗合成酶綜合征(抗EJ抗體陽性),予醋酸潑尼松20mg/d和環孢素150mg/d治療,治療1周后患者憋喘緩解,CK 1 142U/L,pO271mmHg。
患者,男,52歲,因“發熱、皮疹、乏力2年”于2017-10入院。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8℃,面部及前胸部及背部散在紅色斑疹,伴瘙癢灼熱感,乏力,肌無力、肌痛,無畏寒、寒戰,無流涕,無咳嗽、咳痰,無胸悶、憋喘,無活動后氣促,無口腔潰瘍及光過敏,既往體健,無用藥史。查體:面部、頸部V區、背部紅色斑疹,雙手近端指間關節、雙肘關節伸面斑丘疹,伴色素脫失,四肢近端肌力4級,四肢肌肉壓痛,肌張力可。心肺查體無明顯陽性體征。輔助檢查:ALT 56.90U/L,AST 157.20U/L,CK 4 902U/L,CK-MB 111.35U/L,HBDH 433U/L,LDH 614U/L,SF 827.69ng/ml,CRP 27.3mg/L,ESR 36mm/h,抗Ro-52抗體+++,抗SSA抗體+,血常規、余生化、類風濕因子、抗環瓜氨酸肽抗體、抗核抗體、抗可提取性核抗原抗體、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補體、肺癌系列、凝血、病毒、真菌、支原體、降鈣素原等指標均未見異常。肌電圖提示肌源性損害(活動期);心臟彩超未見異常;胸部CT示:雙肺紋理增多,雙肺可見磨玻璃影,以雙肺下葉為著。肺功能:肺通氣功能正常,CO彌散量輕度降低,FVC 130%,FEV1 118%,DLCO 73%。入院第6天肌炎抗體譜回示:抗EJ抗體+++。診斷為“抗合成酶綜合征(抗EJ抗體陽性)”,予甲強龍60mg/d和環磷酰胺每周0.4g治療,10天后復查ALT 51.60U/L,AST 48.10 U/L,LDH 314U/L,CK 1 281U/L,CK-MB 62.83U/L,SF 146.5ng/ml,出院規律服用醋酸潑尼松治療,期間穩定,1年后減至5mg維持。2年后再次出現面部、軀干部、雙側大腿后外側瘙癢伴紅色斑疹,伴瘙癢、燒灼感,乏力明顯,四肢肌力5級,無肌痛及肌肉壓痛,無明顯呼吸系統癥狀。CK 269U/L,LDH 247U/L,ESR 77mm/h,SF 465.79ng/ml,IgG 22.1g/L,CRP 7.75mg/L。皮膚病理:表皮未見明顯異常,真皮淺層水腫,血管擴張、充血,血管周圍較多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浸潤。予醋酸潑尼松5mg/d和硫唑嘌呤100mg/d繼續治療,10天后皮損消退,復查肌酸激酶183U/L。
2 討論
1991年Love等提出按照特異性抗體對多發性肌炎/皮肌炎進行分類,1992年Targoff首次將抗氨基酰 tRNA 合成酶(aminoacyl tRNA synthetase,ARS)抗體陽性,臨床以肌炎、間質性肺炎、關節炎、雷諾現象、發熱、技工手為特征的一類肌炎/皮肌炎命名為抗合成酶綜合征(antisynthetase syndrome,ASS)。基于國外近年來文獻報道,其年發病率約為0.6/10萬[1],男女發病比例約為1∶2[2],抗ARS抗體在PM/DM中的發生率為30%,目前已知的抗ARS抗體有11種,抗甘氨酰tRNA合成酶抗體(EJ)在PM/DM的發生率小于5%。抗EJ抗體在抗ARS抗體中的陽性率國內外報道有差異:2014年日本金沢大學一項165例抗ARS抗體陽性的PM/DM患者調查結果顯示:抗EJ抗體陽性者占抗ARS抗體陽性的23%,僅次于抗Jo-1抗體(36%);趙娜等[3]報道60例ASS患者,抗Jo-1抗體陽性率為70%,抗PL-7抗體陽性率為11.7%,抗PL-12抗體陽性率8.3%,抗EJ、OJ抗體陽性率僅為5%。
雖然抗合成酶綜合征有著共同的臨床表現,但進一步的觀察發現,不同類型抗ARS抗體的臨床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例如抗Jo-1/EJ/PL-7抗體臨床表現多與肌炎相關,被認為是肌炎相關性抗體,而抗KS/PL-12/OJ抗體被認為是非肌炎相關性抗體。本研究針對抗EJ抗體陽性患者臨床特征做一個概述。抗EJ抗體陽性患者與其它抗ARS抗體患者在發病年齡和性別上無差異。在臨床表現方面,80%以上抗EJ抗體陽性患者合并肺間質病變(ILD),表現大多呈慢性、隱匿性,但約有18%抗EJ抗體陽性患者臨床表現為無肌病性皮肌炎(CADM),這一部分人群可出現急性進展型的ILD,表現為1月內出現嚴重的低氧血癥和呼吸衰竭。肌無力的發生率較高(55%),在所有抗ARS抗體陽性患者中僅次于抗Jo-1(78%)、PL-7(76%)抗體陽性者。多關節炎、技工手、雷諾現象在抗EJ抗體陽性患者的發生率少于抗Jo-1、OJ、PL-7、PL-12抗體陽性患者。向陽疹、Gottron皮疹、Gottron征在抗EJ抗體陽性患者中常見,發生率與抗PL-7抗體陽性患者一致,并高于其它抗ARS抗體者。干燥癥狀在各抗ARS抗體的發生率報道不一,國外報道認為其在抗EJ抗體中陽性率高,國內報道多認為其在抗PL-12抗體中陽性率高。發熱癥狀與各抗ARS抗體的發生率無差異。抗EJ/抗PL-7抗體陽性患者的平均病程長于抗Jo-1/PL-12抗體陽性患者。抗EJ抗體還可出現在系統性硬化癥和重疊綜合征患者中[4~6]。Hamaguchi等[5]總結165例ASS患者臨床特征,其中抗EJ抗體陽性患者38例,表現為DM者37%,PM者13%,CADM者18%,僅有間質性肺病者26%,系統性硬皮病者3%,重疊綜合征者3%;38例患者中21例以ILD起病,6例(29%)在隨訪中出現肌炎;6例以肌炎起病,5例(83%)病程中出現ILD;11例肌炎和ILD同時發病。肌炎特異性抗體相對相互排斥,而肌炎相關抗體與肌炎特異性抗體共存[7]。Ro-52是最常見的與抗EJ抗體交叉存在的肌炎相關抗體,其次是SSA、SSB。抗EJ抗體陽性與抗Jo-1抗體陽性患者肌酶譜各項均值均較高,高于其他抗ARS抗體患者[4]。
上述2例患者均有肌無力、ILD、Gottron皮疹表現,血清肌酶譜、炎性指標升高,抗EJ、Ro-52抗體陽性,肌電圖提示肌源性損害,肺CT顯示肺間質纖維化,肺功能有彌散功能降低,治療為糖皮質激素聯合免疫抑制劑。第1例患者以肌炎為首發癥狀,病程中出現多關節炎和ILD,呼吸道癥狀明顯,反復發作,逐漸加重合并低氧血癥,予糖皮質激素和環孢素治療;第2例患者,肌炎和ILD同時出現,肌酶水平高,肌痛、肌無力嚴重,而且伴有罕見的皮膚血管炎表現,但無呼吸道癥狀,僅有影像學證據提示有肺受累,考慮到患者肌炎癥狀較重,皮膚血管炎反復發作,予糖皮質激素聯合硫唑嘌呤控制病情。總的來說,2例抗EJ抗體陽性的ASS患者病情輕,對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反應良好,但容易復發,2例患者2~7年病程中復發2~4次,早期聯用免疫抑制劑可以減少復發次數。
綜上所述,抗EJ抗體與肌炎、間質性肺病相關,皮損以向陽疹、Gottron皮疹、Gottron征為主,可表現為CADM,合并RPILD的可能。ILD是影響預后的主要因素,臨床要引起重視,監測ILD的活動指標,包括鐵蛋白(serum ferritsn,SF)、涎液化糖鏈抗原(Krebs von den Lungen-6,KL-6)、肺表面活性物質蛋白(SP-D)水平,有預測ILD發生、判斷病情活動度、評估預后的作用,SF、KL-6、SP-D值與DLCO、FVC呈負相關,KL-6、SP-D還能鑒別肺部的細菌感染和間質性肺病,細菌感染時,兩者值正常。Gono等[8]研究SF>500ng/ml時發生急性/亞急性肺間質病變的概率明顯增加,SF≥1 500ng/ml時患者生存率明顯下降,6 個月累積生存率僅為28.6%。Fathi等[9]回顧性分析30例PM/DM患者KL-6水平,結果表明KL-6為549U/ml時,診斷合并ILD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為83%、100%,中日友好醫院對DM/PM-ILD患者的血清標志物、肺功能、肺CT研究發現KL-6出現早于臨床癥狀、肺CT表現[10]。肺功能、肺部高分辨率CT、動脈血氣分析、6分鐘步行距離試驗能幫助評價肺的功能狀態,有助于及早調整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