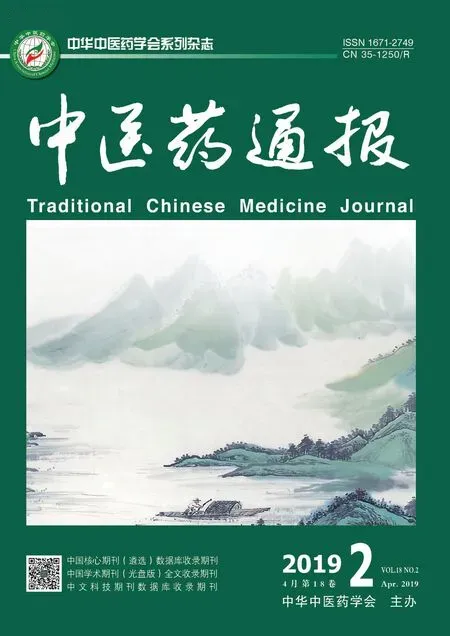從血府逐瘀湯“異病同治”看方劑辨證
● 張 歌 李恒謀
血府逐瘀湯是清代醫家王清任名方,《醫林改錯》曰:“立血府逐瘀湯,治胸中血府血瘀之癥。”[1]“所治之癥目”共有19條,即頭痛、胸痛、胸不任物、胸任重物、天亮出汗、食自胸右下、心里熱(名曰燈籠病)、暓悶、急躁、夜睡夢多、呃逆(俗名打咯忒)、飲水即嗆、不眠、小兒夜啼、心跳心忙、夜不安、俗言肝氣病、干嘔、晚發一陣熱。
此方以桃紅四物湯活血化瘀和四逆散疏肝理氣,除以上九味藥外加桔梗、牛膝組成,具有“活血化瘀而不傷正、疏肝理氣而不耗氣”的特點,病機以“肝郁氣滯、營血瘀阻”為特點,是為氣滯血瘀證而創。
現代對于血瘀證的認識,參考《血瘀證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2011年)血瘀證的診斷標準,血府逐瘀湯推薦用于氣滯血瘀證(臨床表現為:胸脅、脘腹脹悶或疼痛,乳房脹痛,小腹脹痛、刺痛,心煩易怒,舌黯,舌質黯紅,脈弦),體現了在八綱辨證、六經辨證及臟腑辨證指導下對血府逐瘀湯方證的理解,顯然現代血瘀證的認識較血府逐瘀湯所治癥目相去甚遠。《醫林改錯》曰:“血府即人胸下隔膜以上,低處如池,池中存血之處。”血府逐瘀湯所治癥目頗多,以“胸中血府血瘀”之病位病機難以全部解釋,更如“天亮出汗”,已超出了一般血瘀致病的范疇。然王氏又云:“古人立方之本,效與不效,原有兩途。其方效者,必是親治其癥,屢驗之方;其不效者,多半病由議論。方從揣度。”可知經王清任“親治其癥”,血府逐瘀湯才成為“屢驗之方”,所治癥目皆由實踐得來。“血府逐瘀湯所治癥目”即等同為血府逐瘀湯證,其指導臨床用方之意與方劑辨證相似相通。
認識疾病在于證,治療疾病在于方。受王氏之言啟發,分享運用血府逐瘀湯醫案兩則,均獲桴鼓之效,以管中窺豹,探析方劑辨證之一斑。
1 青光眼頭痛案
張某某,女,68歲,2017年8月10日初診。輪椅來診,閉目流淚,青光眼病史多年,因久視手機累目后出現頭痛,左側前額掣痛,雙目赤痛,左側嚴重,舌淡紅有瘀斑,苔白厚膩,脈細弱。查眼壓升高,確診為閉角型青光眼急性發作期,中醫診斷:綠風障目(氣滯血瘀)。方選血府逐瘀湯加減。藥用:當歸10g,生地30g,桃仁6g,紅花6g,枳殼10g,甘草6g,赤芍10g,柴胡10g,川芎15g,桔梗10g,牛膝15g,枸杞子10g,菊花10g,桑葉15g,夏枯草15g,7劑。
2017年8月17日二診:家屬攙扶行走來診,頭痛、目痛、流淚明顯好轉,仍有雙目異物感,稍覺咽干,舌淡紅有瘀斑,苔白,脈細弱。上方去枸杞子,加木賊10g,7劑。
2017年8月24日三診:癥狀進一步好轉,合杞菊地黃湯善后。隨訪1年未復發。
按患者雖為眼部疾患,但以前額頭痛為主要癥狀,“頭痛”為血府逐瘀湯所治之病第一條,“查患頭痛者,無表證,無里證,無氣虛、痰飲等癥,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劑而愈。”結合舌象瘀斑,血府逐瘀湯用之有據。青光眼為房水排出異常所致,肝開竅于目,“津血同源”,入脈為血,出脈為津;四逆散疏肝理氣,桃紅四物湯養肝活血,于此收效之理明。
2 肺癌術后發聲困難案
馬某某,男,49歲,2017年11月4日初診。3個月前體檢發現右肺1.8cm大小占位性病變,確診惡性腫瘤,行胸腔鏡手術治療,術后發聲困難,僅能逐字發音,考慮手術損傷喉返神經,經針灸治療后語言漸流暢,但仍聲音嘶啞,大便日行4~5次,成形,舌紫暗苔白厚,脈弦。中醫診斷:肺積(氣滯血瘀)。處方:柴胡6g,白芍15g,枳殼6g,炙甘草6g,熟地黃15g,當歸6g,川芎10g,桃仁6g,紅花6g,仙鶴草30g,葛根30g,炮姜10g,車前子30g。7劑。
2017年11月11日二診:聲音較前宏亮,大便次數減少,上方加山藥30g,蓮子30g,芡實30g以實大便。此方基礎調整服至2018年1月,發聲困難緩解,聲音恢復至術前狀態。隨訪1年未復發。
按患者聲音嘶啞,雖未在血府逐瘀湯所治之條目,然病起于術中損傷,傷處必有瘀血,此病機與“飲水嗆咳”會厭瘀血相似,“飲水即嗆,乃會厭有血滯,用此方極效”。本案使用血府逐瘀湯收效正如王氏之言。
3 總結
以上醫案兩則,非從一般辨證論治而治,乃受王清任“血府逐瘀湯所治之癥目”啟發而用,所謂“方證相對”,可收效桴鼓。
方證相對的精神內涵最早體現在《傷寒論》,“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都提到了病證與方劑相對應的關系。孫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九》“舊法方證,意義幽隱……今以方證同條,比類相附需有檢討,倉卒易知”提出“以方類證”的研究思路,更是豐富了“方證相對”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涵義。宋代孫奇等在校正《金匱要略》時,序中有“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言,清柯韻伯《傷寒來蘇集》中“合是證便是方”亦是此義。劉渡舟教授曾著述強調“方證相對”的重要性[2]。當代醫家朱邦賢[3]將方證辨證作如下定義:又稱方劑辨證,是以方劑的主治病癥范疇及該方組方之“理法”為基礎,通過對患者表現出來的主要病癥(或病機)與“方證”相符與否的分析,選擇合乎理法的方劑主治疾病的一種辨證施治方法。方劑辨證的原則是“有是證而用是方”,具有思維方式上“逆向辨證”的特征,正如徐靈胎言“此從流溯源之法,病無迭形矣。”
中醫辨證論治學術體系一直被認為是中醫學理論中最具特色的學術精髓,“方證相對”更被認為是中醫辨證論治法則之魂[4]。它歷來是中醫臨床不可或缺的一種辨證思維與技術方法。有醫家[5]認為方證辨證與辨證論治是《傷寒雜病論》提出的兩個獨立的辨證學術體系,既相互補充又互相滲透。此說不無道理。但用方劑辨證平行于六經辨證、八綱辨證、臟腑辨證、三焦辨證,均隸屬于辨證論治來形容兩者的關系則更為貼切[6]。
方證相對是臨床醫生對一個方劑深刻理解和長期應用經驗的積累總結,走了辨證論治的“捷徑”,也可以說方證相對是基于方劑組方理法上的“異病同治”法則的進一步拓展。將方證結合起來研究,有利于開闊臨床思路,豐富方劑涵義,有效指導治療,發現新的規律。方劑辨證論治方法自古有之,但自清代以后建樹寥寥,方證研究也大多局限于部分《傷寒論》經方,沒有形成系統的方法體系。喜于已有學者關注并潛心研究[7,8],也有新的具有可行性方法建議提出[9]。方證相對理論起于傷寒,方證相對研究重于經方,今謹遵其義臨證,可拓方劑之使用范圍,緩患者之病痛。正所謂起于傷寒,而不止于經方。方劑辨證在辨證論治中必不可少,方證相對研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