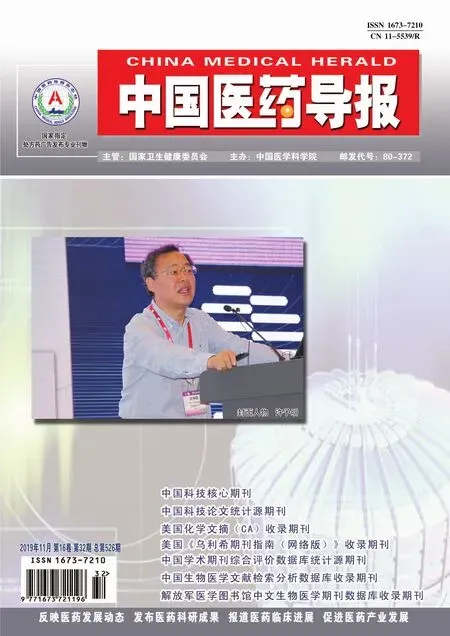肛周膿腫的診治進展
宋思惠 秦建平
1.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貴州遵義 563000;2.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中醫肛腸科,貴州遵義 563000
肛周膿腫是指直腸肛管周圍軟組織內或周圍間隙內發生急慢性化膿性感染形成的膿腫,為肛腸外科常見疾病。常見癥狀包括肛周疼痛、腫脹、發熱,并伴有異味,大部分均需手術治療,術后予以抗感染、坐浴換藥等綜合治療[1]。膿腫術后易反復發作,形成肛瘺,目前無一種特別有效的治療方法,現將近5 年的診治進展報道如下。
1 肛周膿腫發病率及特點
肛周膿腫發病率在我國較高,楊志鵬等[2]報道,肛周膿腫發病率約為2%,占肛腸疾病的8%~25%。這與國外的相關報道差別很大,瑞典一項研究報道其發病率為16.1/10 萬[3];Sahnan 等[4]統計出英國的年發病數估計在14 000~20 000 例,考慮可能與環境、氣候、飲食及生活習慣等不同息息相關,其主要發病人群集中在20~40 歲的中青年。
2 肛周膿腫病因病機
2.1 中醫病因病機
中醫學認為,肛癰陽證多因飲食辛辣、醇酒厚味,致濕熱內生,熱毒蘊結肛門所致;或因感染毒邪,氣血淤滯,經絡阻塞所致。孫林梅等[5]研究顯示,痰濕質、濕熱質和陰虛質體質是肛癰發病的危險因素。
2.2 西醫病因病理
西醫認為,肛周自身解剖結構復雜及細菌感染是肛周膿腫發生的主要病因。
2.2.1 發病機制 肛周膿腫的發病機制有多種假說,其中較為公認的是Parks 提倡的肛腺感染學說[6]。致病菌首先侵入肛竇致其感染,隨后肛腺導管分泌物淤堵引起肛腺炎,炎癥逐漸向肛門直腸周圍各間隙蔓延,最終形成肛周膿腫。國外已有研究證實,吸煙、肥胖、糖尿病、HIV 感染和炎性腸病均為肛周膿腫的風險因素[3,7]。
2.2.2 肛周膿腫的病原菌特點 肛周膿腫的感染多為厭氧菌與革蘭陰性菌的混合感染[2,8]。有研究[9-11]證實,膿液培養常見病原菌為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也有相關研究[12-13]報道,肛周膿腫常見病原菌是大腸埃希菌、鏈球菌屬、金黃色葡萄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且膿液標本中有66.7%培養出厭氧菌腸道菌群,可見大腸埃希菌為肛周膿腫最常見細菌,考慮可能與發病部位相關。
3 肛周膿腫常規治療方法及其并發癥
3.1 切開引流術及其并發癥
早在14 世紀初,英國直腸病學之父約翰·阿德納已強調早期開放膿腫并引流的治療原則。目前,肛周膿腫切開引流術仍為公認治療方式,但膿腫復發率和瘺管形成率高達40%[14]。
3.2 一期根治術及其并發癥
肛周膿腫一期根治是指在徹底切開膿腔及內口的基礎上,再擴大范圍切除內口及周圍感染組織的一種術式,具有肛瘺形成率低、膿腫復發率低等特點,但也產生術后肛周水腫、疼痛、創面滲液及創面延遲愈合等并發癥,且因增加肛門失禁風險受到一些術者的反對。
4 肛周膿腫的術后治療
4.1 中醫治療
隨著近年來病原菌對抗菌藥的耐藥性升級,肛周膿腫圍術期中醫藥的應用及抑菌研究逐漸增多。最常用的中醫藥治療方式包括外敷、熏洗、坐浴。
4.1.1 中藥清熱解毒抑菌作用 臨床上常用苦參湯為基礎方加用清熱解毒、活血止痛的中藥,中藥具有清熱解毒、消炎抗菌、活血止痛之效。現代藥理學顯示,中藥的抑菌機制多樣,有效抑菌成分多種,可在多部位、多階段發揮抑菌作用,甚至可逆轉細菌的耐藥性。主要抑菌機制包括以下三點[15-16]:①直接破壞菌體細胞膜、細胞壁等結構,同時干擾細菌的代謝。②促進機體免疫系統發育,激活其免疫功能。③抑制局部炎性介質的滲出,減輕炎性反應。中醫藥發揮抑菌作用的有效成分有多種,主要包括黃酮、醌類、多糖類、萜類、有機酸、生物堿、揮發油等。有研究表明,肛周膿腫術后使用的濕潤燒傷膏中含有的β-谷甾醇、小檗堿和黃芩等有效成分可使病原菌變異并抑制其生長,同時減輕病菌的毒性,從而起到較強的抗菌作用[17-18]。林正軍[19]報道,消炎生肌膏中的輕粉、爐甘石、朱砂、黃丹均有抑菌作用,其中爐甘石對銅綠假單胞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埃希菌等多種病原菌均具有較強的抑菌作用。此外,廣泛的研究證實冰片、蒲公英、苦參、虎杖、金銀花、赤芍、白芷、皂角刺也具備較好的抗菌效果。中醫藥不僅具有較明顯的抑菌效果,甚至可逆轉某些菌株的耐藥性。張傳美等[20]對慶大霉素耐藥型大腸埃希菌進行研究發現,小檗堿能直接抑制其產生,而黃芩、黃連和黃柏則可通過抑制β-內酰胺酶,間接消除耐藥株的耐藥性。另有實驗研究證實,中藥的抑菌性能與培養基的條件相關[21],故實際的抑菌性能還應考慮人體微環境的影響。
4.1.2 中藥的其他效應 中醫藥在消腫、緩解疼痛、促進創口愈合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趙瑞琴等[22]報道,康復新液用于肛周膿腫術后創面換藥,可明顯促進創面肉芽生長,加快創面愈合。陳月紅[23]對膿腫術后患者使用加味四黃散熏洗,研究表明其能降低術后血漿纖維蛋白原含量,有效減輕術后創面疼痛程度,減少術后創面分泌物的產生,縮短創面愈合時間。孫昱[24]研究表明,龍甘消炎膏在肛周膿腫術后的應用,極大地緩解肛周疼痛、創面滲液等并發癥,并促進傷口的愈合,由此減輕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質量。
此外,眾多的研究皆證實中藥對肛周膿腫的其他術后并發癥亦有良好效果。例如,張蕉等[25]應用三黃洗劑坐浴聯合辨證施護于肛周膿腫術后,發現能有效減少精神情緒改變、出血、便秘、尿潴留等并發癥。秦曉靜等[26]通過臨床觀察得出結論,術后創面換藥應用扶正生肌油紗不僅能起到保護創面促進愈合的作用,同時還能使術區創面與外界環境隔離減少創面感染。
4.2 西醫治療
西醫術后常規選用高錳酸鉀1∶5000 溫水坐浴及抗生素抗感染治療。抗生素在肛周膿腫術后的應用如下:
4.2.1 抗生素的耐藥現狀 肛周膿腫最常見的病原菌是腸道菌群——大腸埃希菌[27]。2017 年CHINET 中國細菌耐藥性監測[28]報道了大腸埃希菌對多數抗生素的耐藥率已接近或大于50%。大量肛周膿腫致病菌耐藥性檢測的相關文獻報道主要致病菌耐藥性呈上升趨勢。早在1986 年,日本學者品川長夫對肛周膿腫的病原菌行藥敏試驗結果示,致病菌對各類抗菌藥物均有較好敏感性。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致病菌的耐藥性便產生了極大改變,膿液中的病原菌對臨床常用抗菌藥物幾乎普遍耐藥[29-31],僅少數幾種抗菌藥物暫未發現耐藥菌株[11]。徐利等[32]對肛周膿腫膿液分離出的124 株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腸埃希菌進行耐藥性的檢測,結果僅亞胺培南、替加環素及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未發現耐藥菌株。導致近年來細菌耐藥性上升的主要原因為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s)細菌的產生增加。ESBLs 可水解青霉素類、頭孢菌素類以及單酰胺類抗菌藥物,導致細菌多重耐藥,并通過質粒在細菌中傳播引起ESBLs 細菌的流行,為抗感染治療造成較大的困擾。柴瑞琪等[33]研究發現,ESBLs 大腸埃希菌對青霉素類、喹諾酮類等各類抗生素的耐藥性較非ESBLS 大腸埃希菌的耐藥性呈成倍增長,其中對頭孢類的耐藥率增長最突出,最多可達12.739 倍。此外,多重耐藥菌數量增多亦是導致細菌耐藥性增加的原因之一,多重耐藥菌可以是ESBLs 細菌,也可以是非ESBLs 細菌。文剛[34]研究發現,肛周膿腫的致病菌中多重耐藥菌占比達50.94%之多,大腸埃希菌中多重耐藥菌株的比例高達55.26%。
4.2.2 抗生素應用的副作用 抗生素應用的副作用及相關問題近來也引起了臨床醫生及科研界學者的廣泛關注。抗生素的應用可因糖和膽汁酸代謝異常、腸道菌群失調及腸黏膜直接刺激作用而致腹瀉;也可因其刺激、損害腸壁結構導致大腸蠕動功能障礙,食物殘渣在大腸內停留時間過長,水分過度吸收引起大便干燥而致便秘。王勝文等[35]研究發現,抗生素治療組出現頭痛癥狀者遠較中藥內服聯合坐浴組多,部分還可能出現皮疹等變態反應。此外,抗生素還能誘導革蘭陰性桿菌菌體內大量內毒素的釋放,導致病情的進一步惡化。
4.2.3 抗生素使用現狀 目前臨床上多使用抗生素來解決術后并發癥,部分研究發現了對所有接受手術引流的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有益證據[36-37]。此外,Ghahramani 等[38]通過1 年時間的單盲隨機對照試驗,得出抗生素可以預防瘺管發展的結論。一篇最近的Meta 分析顯示,切開和引流肛門直腸膿腫后的抗生素治療與瘺管形成的可能性降低36%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4]。由于證據質量低,它們的使用仍存在爭議并且僅受當前指南的弱推薦。例如,美國結腸和直腸外科醫生協會(ASCRS)和意大利結腸直腸外科學會僅推薦術后抗生素用于全身感染,潛在的免疫抑制或伴有周圍蜂窩織炎的膿腫。但并非所有研究證據均支持術后抗生素的應用。一項多中心、雙盲隨機試驗[39]表明,膿腫引流后的抗生素治療無法防止隨后的瘺管形成。另一項前瞻性臨床試驗發現,在引流中加入抗生素治療不能提高愈合率或減少復發[40]。故英國肛腸協會和愛爾蘭肛腸協會(ACPGBI)暫未就使用術后抗生素達成共識。
5 小結與展望
肛周膿腫發病機制有多種假說,目前多數學者較為公認的是Parks 提出的肛腺感染學說。肛周膿腫的感染常見厭氧菌與革蘭陰性菌的混合感染,治療以膿腫切開引流術為較公認的治療方法。迄今,關于肛門直腸化膿性疾病的所有患者使用經驗性術后抗菌藥以預防并發癥尚無共識,再加上目前抗感染治療難度增加、抗菌藥副作用明顯,術后抗菌藥應用是否必要或可否被取代值得今后進一步探究。由此,避免或減少不必要抗生素及廣譜抗生素的使用,延緩細菌耐藥性的進展、阻斷多重耐藥菌的進一步流行已成為當前臨床用藥的首要目標。
中醫藥作為我國五千年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瑰寶,治病講究整體論、全局觀,通過調動全身免疫系統,持續高效地發揮藥效,其不僅證實抑菌效果明顯,且在術后創面的促愈、消腫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在肛周膿腫術后已有不少關于抑菌、改善并發癥等的研究,但在術后預防膿腫復發及肛瘺形成的中醫藥研究卻寥寥無幾,且在肛周膿腫術后應用的研究不及抗菌藥廣泛。中醫藥的研究缺乏高質量、多中心、大樣本量的臨床試驗,這將有待未來實驗研究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