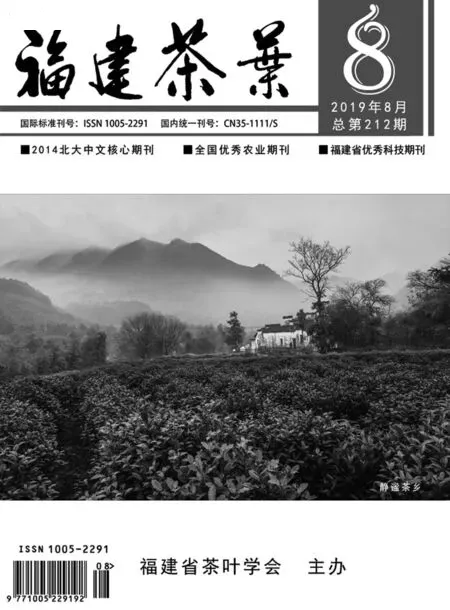日本茶道中的禪意
張 峰
(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河南鄭州 451191)
1 引言
作為茶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中國茶文化對日本茶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茶文化和禪宗思想的交融發展就是重要體現。當佛教傳入中國后,茶事活動就成為佛事活動的重要組成,禪宗思想也逐漸融入到茶文化之中,不斷豐富著茶文化的內涵,隨著中國茶文化傳入日本,尤其是日本留學僧對茶文化的推介和引進,這種“茶禪一味”的審美追求也逐漸固化在日本茶道乃至民族精神之中。“茶禪一味”不僅是日本茶事活動中普遍存在、耳熟能詳的用語,也是研究日本茶道,尤其是日本茶道中的禪意、禪思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詞,“茶禪一味”不僅體現了日本茶禪文化的發展歷程,還體現出了日本茶道中“禪”之境界和“禪”之追求。本文將在呈現“茶禪一味”緣起發展和精神內涵的基礎上,研究日本茶道中禪文化的發展歷程,從“和”“敬”“清”“寂”、“一期一會”、“獨坐”及茶具、茶室等方面,探討日本茶道中的禪意呈現和審美追求。
2 “茶禪一味”的緣起發展和精神內涵
“禪”是梵語“Dhyana”的音譯,本意為“靜慮”,最初傳入中國時也因其本意而被翻譯為“思惟修”,即開啟智慧、修至禪境的一種方法,簡而言之就是用靜思的方式體味尋常事物中所蘊含的哲思和智慧,從而“悟”出生活、生命的真諦,正如《永嘉大師證道歌》中所言,“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1]。其中的“靜”“思”“悟”與茶文化的意趣追求不謀而和,這也是“茶禪一味”能夠廣泛流傳的根本所在。
正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茶文化的重要發源地,“茶禪一味”也原起于中國。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就開始種植茶葉;到了唐代,飲茶的習慣已不再是皇族貴胄的專屬,在民間飲茶之風十分盛行。在唐代尤其是盛唐晚期,飲茶已成為禪宗寺院里重要的日常事務,不同于民間以茶會友的風氣,禪宗寺院的茶事活動具有嚴格的規范,許多禪宗寺院每年都會舉辦隆重的茶會,這在《釋門正統》、《禪苑清規》、《敕修百丈清規》等佛教經典中均有體現。在唐代,禪師們常常以茶說禪,這進一步促進了茶禪文化的發展,比如,叢諗禪師“吃茶去”的公案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面對參拜自己的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談話,而對于這些“不同”,叢諗禪師的回答都是“吃茶去”,這一令人疑惑的回答也成為了人們參悟的對象,而趙樸初居士的“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則解答了眾人的疑惑,再好的美酒也比不過一碗清茶,再多的高僧點撥也未必能夠令人參透一切,不如放下一切“吃茶去”[2]。從趙樸初居士的詩中,能夠看到千年之前“茶”與“禪”就已結下不解之緣。在唐宋時期,空海、最澄、一休、榮西等日本留學僧將中國的茶禪文化帶回日本,《吃茶養生記》等留學僧關于茶禪文化的論著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茶道的興起和發展,“茶禪一味”也在日本上流社會中流行開來。隨著日本茶道的不斷發展,“茶禪一味”的審美追求體現在日本茶事活動的方方面面,可以說,“禪”貫穿于日本茶道的發展歷程。總的來說,“茶禪一味”原起于中國,卻在日本發揚光大,近代以來直到改革開放后,“茶禪一味”又從日本傳回中國,現在“茶禪一味”已經得到了東方世界的廣泛認同。
“茶禪一味”廣泛流傳的根本原因在于“茶”和“禪”之間的緊密聯系和精神層面的互通,茶的韻味在于靜心品味中的先苦后甜,與禪宗的“靜修”“苦諦”相通,品一杯清茶,先苦后甜的感受猶如經歷繁雜瑣碎后的豁然開朗,人生所經歷的痛苦都是一種修行和磨礪,在磨礪后的峰回路轉猶如茶的回甘一樣,也猶如悟“禪”后的寧靜、平和、淡薄,所以品茶與修行具有相通之處,“茶”中的禪意也成為了茶禪文化的核心。
3 日本茶禪文化的發展
正如上文所述,“茶禪一味”源自中國,興盛于日本,公元七世紀時,大量的日本留學僧和遣唐使將中國飲茶的習俗和中的茶禪文化引入日本。此時日本茶葉種植規模較小,茶葉數量有限,制茶方法也僅被少數人掌握,飲茶習俗只在日本上流社會流行,在《日本書記》《與海公飲茶送歸山》等文獻中,都記載了日本皇室、貴族及寺院中的茶事活動。由此可見,日本茶道自產生之日起,就與“禪”結下了不解之緣。唐朝安史之亂爆發后,中國茶禪文化對日本茶道的影響日漸衰微,到了日本鐮倉時代,在榮西等高僧的倡導下,日本開啟了具有本土風貌的茶禪文化發展歷程,“茶禪一味”的思想理念和審美追求開始在日本發揚光大,可以說,從日本茶道獨立發展以來,“禪”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始終作為重要審美特征存續其中,禪宗思想對日本茶道的發展、成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隨著日本茶道的發展,在室町時代,日本茶葉種植規模不斷擴大,茶葉也在日本社會生活中逐漸普及,直接推動了日本本土關于制茶方法、茶室建設、茶具制作的研究,為更加規范、更為精細的茶事活動奠定了重要基礎。與此同時,日本的茶禪文化不斷發展,樸素雅致的茶事活動成為了禮儀、禪宗、日本文化的集成體現,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茶事活動的模仿和對中國茶禪文化的尊崇日益弱化,日本以“茶禪一味”為核心的茶禪文化發展也逐漸呈現出了日本民族文化特色[3]。到了江戶時代,日本茶道文化走向成熟,茶道流派百花齊放,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千家”成為日本茶道的中流砥柱,在弘揚“茶禪一味”的同時,將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書法藝術、繪畫藝術以及武士道精神融入到茶道文化中,使日本的“茶禪一味”綻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獨具特色的魅力。
4 日本茶道中的禪意追求
日本茶道中的禪意首先體現在“和”“敬”“清”“寂”上,早在鐮倉時代,“和”“敬”“清”“寂”就是日本社會所認可的茶道思想和茶人的精神追求。從“和”“敬”“清”“寂”這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四種境界中,能夠看到鮮明的禪宗思想,“和”體現的是心中有佛、佛我如一的修禪境界;“敬”體現的是眾生平等的思想;“清”則體現的是靜心修禪中的“清凈心”;“寂”則指向了涅槃,體現了萬物皆空的無我追求[4]。可以說,“和”“敬”“清”“寂”不僅是日本茶道一以貫之的精神追求,更是日本茶道的審美追求,體現日本茶禮儀、茶事活動的方方面面。
“一期一會”是日本茶道的專用語言,意為每一次茶事活動都是一生一次的相會,細觀之下也蘊含著“和”“敬”的茶道思想。“一期一會”所體現的是日本茶人在茶事活動中的心態,將茶事活動作為人生中難能可貴的一次相會,在相互尊敬、滿懷感恩的氛圍中飲茶交談,體現出了生活中友人之間的真摯情誼,同時也體現出了超越生活的人生哲思和禪意追求。如果說“一期一會”體現出了“和”“敬”的茶道思想,那么“獨坐”則體現出了“清”“寂”的精神追求,同樣是日本茶道中的重要組成。“獨坐”即為獨自品茶,在品茶的過程中靜思人生、反思生活,與禪宗的“坐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獨坐”時的靜思又與禪宗的“冥想”相似,品茶節奏緩慢、環境清靜,能夠讓品茶之人摒棄雜念,在清新的茶香和悠然的心境中達到自悟,感受一茶一世界的禪意,走進身在凡世又超然世俗的奇妙境遇之中。
日本茶道中的禪意不僅體現日本茶道思想、茶道觀念中,還體現在茶具和茶室建設上,樸素殘缺的茶具和講究不對稱之美的茶室建設呈現出了獨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禪一味”的審美追求。相比于中國茶禪文化中對對稱、完整、圓潤的審美追求而言,日本茶道文化更加偏愛殘美、不對稱之美,茶具常常是殘缺甚至是畸形的,在自然樸素的色彩中呈現出了個性化的追求。茶具樸素的材質和色彩體現出了對自然的尊崇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禪意,比如日本茶具中的重要代表“樂燒”就選胎土為材,經過素燒、上釉后入窯燒制,古樸的材質和色彩中蘊含著繁復的工序和細膩的做工,體現出了千錘百煉、精雕細琢后的自然之美,猶如經歷了修行后回歸本真的狀態。再如日本的“赤樂茶碗”和“黑樂茶碗”都是用手工進行塑性,殘缺或不對稱的形態反而體現出了個性之美、靈動之美和自然之美[5]。
日本的茶室有“不對稱之屋”“喜愛之屋”之稱,與茶具相似的是,日本的茶室也講究自然建造、個性建造。一般而言,日本的茶室面積為十平方英尺左右,源自十平方英尺迎八萬四千佛家弟子的經文,寓意茶室容納為數不多的真正悟禪之人[6]。日本茶室的整體風格簡單樸素、清新空靈,大有模仿禪院建造風格之意,同時又注重細節設計,不同的茶人根據自己的審美偏好建設茶室,體現了“先人后室”的建造理念,在尊崇自然的同時,尊重人的內心,強調人的感悟的重要性,也體現了禪宗關于避免對稱、避免重復的審美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美學追求。
日本茶道中的禪意體現在“和”“敬”“清”“寂”的精神追求中,體現在“一期一會”“獨坐”里,也體現在茶具、茶室上,“禪”已經融入到了日本茶事活動的方方面面,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占據著核心地位。“茶禪一味”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品茶如參禪的日本茶道,還體現了日本社會文化的審美追求,呈現出了超越“茶”與“禪”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