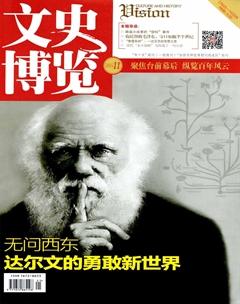公社衛生院拔牙,連拔兩顆都錯了
張正儀
“文革”時期,我插隊的公社距江蘇揚州城區很近,大約正因為近,公社駐地的鎮就特別的小,小到只有一條東西走向的街。小歸小,卻五臟俱全,供銷社、郵政代辦所、信用社、中小學、衛生院,一樣不缺。
公社衛生院在小街南側,與公社機關一路之隔,呈四方形,是一幢獨立的單層建筑。衛生院內分門別類地設有掛號、藥房,內科、外科、婦科等科室,后院還有幾間雙職工宿舍。
衛生院醫術不一的幾位醫生
公社衛生院一共有3名醫生,一位姓陳,一位姓朱,還有一位不知姓名,是大隊合作醫療調上來的“赤腳醫生”。
我插隊的大隊“赤腳醫生”只讀過兩年書,去縣醫院培訓了20天,大隊挪出一間辦公室,他就正式上崗了。記得有位知青患流感,高燒不退,他診斷為,退燒藥吃得不夠份量,藥盒上標注一次吃一顆的藥,應該一次吃8顆。他為了讓知青相信,以身試藥,當著知青面吞下8顆退燒藥,結果自己在床上暈暈乎乎地躺了3天。
公社衛生院的科室是輪流轉的,今天在內科診室就是內科醫生,明天進了外科診室就是外科醫生。所以熟悉衛生院的人從不看科室,只認醫生。
陳醫生很胖,走起路來有點費勁,但他和顏悅色,慢聲細語,對病號從不橫加指責。朱醫生恰恰相反,問診明確,診斷果斷,給人一種嚴肅的感覺。朱醫生十分注重形象,一件穿舊了的白大褂總是一絲不茍地扣好每一粒鈕扣,干部社員一致認為朱醫生的醫術“NO.1”。
那些年,交通工具以自行車為主,從公社騎車去揚州只有十多分鐘,干部社員們生病大都去揚州大醫院就診,所以來衛生院看病的人并不多。后來朱醫生自尋門路,調往一所礦校醫務室當校醫,來衛生院看病的人更加少了。
不幾年,一位姓李的揚州知青打破了衛生院的沉寂。他高高的個頭,白凈的臉龐。因為父親是位小有名氣的醫生,耳濡目染之下,他繼承父親衣缽,插隊不久便當上了大隊“赤腳醫生”。
大隊里有一位社員患了嚴重的白內障,李知青為了解決患者失明的痛苦,冒著風險,用針將白內障撥離晶狀體,讓這位社員重新看見了身邊的事物。
眼科專家說,這原本是一種民間的土方法,醫學上不宜采用。
“文革”年代從不顧及專家怎么說,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揚州日報》報道了一篇《知識青年讓盲人重見光明》的文章。這則新聞迅猛地膨脹,《人民日報》也緊跟著發表了專訪專文。
李知青一時人氣爆棚,名聲大振,被調往公社衛生院,成了一名真正的醫生。
社員們看病都理所當然地找李醫生,甚至有的女青年看婦科病也點名非李醫生不可。然而他只是公社衛生院蜻蜓點水的一位過客,很快被點名,作為工農兵學員,被保送至醫科大學深造。當然,這是后話。
再后來,衛生院來了一對真正的科班大夫,夫婦二人都姓王。二王是南京中醫學院(今南京中醫藥大學)66屆畢業生,因家庭出身不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來到衛生院工作。
從此衛生院有了診斷確切、醫技出眾、一男一女兩位王醫生。社員們不再舍近求遠,奔波揚州,喜歡將首診權交給王醫生。兩位王醫生也以此為家,不僅在衛生院開火做飯、縫洗漿裳,而且還在后院種上了草藥。
“文革”結束后,兩位王醫生落實政策,調回南京,一位成了南京中醫學院教授,一位當了江蘇出版社醫藥編輯。這也是后話。
朱醫生為我拔牙,“不是這一顆”
我在生產隊過了兩年“跟著太陽起,伴著月亮歸”的農耕生活后,調往公社中學任代課老師,接著又在公社農機廠任職,長年租住在公社小鎮上,常與衛生院的醫生打交道。
有一次,我患了口腔潰瘍去衛生院就診,恰值陳醫生當班。他拿了一根棉簽在紅藥水瓶里蘸了蘸,往我嘴里潰瘍點涂抹。我記得朱醫生說過,紅藥水有毒性,口腔內只能涂抹紫藥水,不能擦紅藥水。
陳醫生不屑一顧:“完全道聽途說,紅藥水與紫藥水一樣效果,只是顏色不同。”
離開衛生院不久,我感到嘴里麻木,愈演愈烈,喉嚨也跟著腫脹起來,吞咽困難,整整一天只能吃流食。
還有一次,我的腳跟被異物劃破,流膿滲血不見好轉,恰巧一連三次換藥都遇上陳醫生。大約因為腳臭,每次換藥,他都伸長手臂,讓頭部離得遠遠的。后來我跟隨宣傳隊在縣北演出,去了中心衛生院,一位從南京鼓樓醫院下放的護士為我換藥。她仔仔細細地為我檢查過后,說傷口內有異物,嫻熟地從我腳底鑷出一塊約1厘米左右的碎玻璃。
從此,我看病只找朱醫生,直至兩位王醫生加盟衛生院。兩位王醫生不僅醫術精湛,其醫德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一個秋雨綿綿的晚上,我時而篩糠似的顫抖,時而燒得滿臉潮紅,此前已一連吃了幾天的退燒藥,絲毫不見療效。不得已,我拖著幾乎無法站立的身體,去衛生院復診。兩位王醫生商量以后,決定送我去揚州蘇北人民醫院檢查。
公社沒有通往揚州的公交,男王醫生借來一輛自行車,帶上手電筒。我坐在車后座,躲在王醫生的雨衣里。出發前,細心的女王醫生將雨衣的邊角拉直,覆蓋至我的腳尖,并再三叮囑注意安全。到了蘇北人民醫院,男王醫生的前胸濕漉漉往下淌水。我的病因得到確診,是瘧疾。男王醫生卻因淋雨而病倒了。
還有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我同樣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有一年盛夏,我牙齦腫痛,腮幫也腫了起來。這一天傍晚,我終于按捺不住,一天之內第二次邁進衛生院大門。當時正值暑假時段,調往礦校的朱醫生一家人正在后院吃晚飯。我看見朱醫生,盡隋地訴說牙痛不愈之苦。
“想治標還是治本?”朱醫生問。
“當然治本。”我回答。
“治本,拔掉,一勞永逸。”
“拔掉?”
“你大概不知道吧,我來衛生院前就是牙醫,祖傳的。”
朱醫生當即丟下飯碗,回到宿舍,拿出一套白布包裹著的工具。
我有點擔憂,因為口腔醫院的醫生都頭戴反光鏡,不知是他技術嫻熟,覺得不需要,還是根本沒有。但我對朱醫生還是信任的,主要是“祖傳”二字征服了我。
開始朱醫生操作老到麻利,打麻藥、手術刀分離牙齦都很順利,正式拔牙的時候遇見了麻煩。大概牙根太堅固,一連重復了幾次都不見效,最終朱醫生一手按緊我的下巴,另一只手使勁搖晃著牙鉗,才將牙拔了下來。朱醫生沒有言語,對著牙凝視了好一會兒,脫口說道:“不是這一顆。”緊接著,他又脫口說了第二句:“我建議再拔一顆,不能猶豫,麻藥要過性了。”沒等我點頭或者搖頭,他的牙鉗已經伸進了我口腔,三下五除二拔下了第二顆牙。我清楚地看見牙根上粘著一塊肉。
我口腔里的血水不斷地往外涌,咬緊棉球也無濟于事。朱醫生往我嘴里滴了幾滴藥水。
“腎上腺素,止血的。”沉默良久,朱醫生說了第一句話。
朱醫生收拾起他的工具包,一聲不吭地走了,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懊惱,這顆牙也在不該拔除的范圍之內。
這不是講故事,都是我真實的切身經歷。
(責任編輯: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