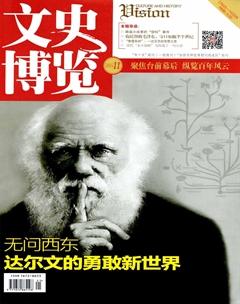張治中賞識的貼身秘書
朱文科

1939年5月20日,一直處于抗戰大后方的湖南耒陽縣城,打破了長久的寧靜與寂寞——湖南省政府從沅陵遷徙耒陽。眾多政府官員、社會各界名流帶著家眷寓居耒陽,這當中就有詩人、書法家洪漱崖。
洪漱崖,本名洪存恕,字漱崖(巖),安徽含山縣巨興鄉人,出生于光緒十七年(1891)。其父洪海榜系祖傳中醫,洪漱崖在少年時期隨父學醫,后考入安慶優級師范中文科讀書,曾在黃埔軍校六期學習,與愛國將領張治中是同鄉同學。張治中很賞識洪漱崖,聘其為隨從秘書長達十多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命其赴湖南省衡山縣就任縣長,洪漱崖懇辭未就,留在省政府秘書科。1939年5月省政府遷徙耒陽,洪漱崖帶了妻兒隨遷,在這座小城一住5年。
洪漱崖在繁忙公務之余,經常到耒水河畔漫步。他最愛去杜甫墓地徜徉。他推崇杜甫,同情杜甫晚年的悲慘遭遇。想到時局和個人命運,同樣有一種“國破山河在”的悲壯隋懷。
洪漱崖平時手不釋卷,酷愛寫詩習字。他在耒陽期間,正處于創作黃金期,先后有兩百多首格律詩詞問世。他的作品,抒發個人遭遇,感嘆家國之痛,陳述時政積弊。其中一首五言律詩《亂后復經耒陽》,詩曰:“斜日江城近,經年戰壘留。蒿深欲迷徑,葦白尚明洲。冷市魚蝦斷,空堂蝙蝠稠。舊奴何處至,骨立不勝秋。”
1940年春,蔣介石親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薛岳在衡山香爐峰征地30畝,種植日本黑松,欲送給蔣介石作為紀念。薛岳打算鑿字于崖壁之上,親授洪漱崖為黑松林題寫碑名。薛岳本身就是書法家,卻請洪漱崖題寫,可見他很欣賞洪漱崖的書法藝術。洪漱崖自然很看重,在耒陽縣城住處整整寫了一個星期,挑選出最滿意的一幅趕往梅橋薛公館交給薛岳。薛岳看了洪漱崖的字,贊不絕口,召集工匠準備在松林邊的崖壁鑿字,但因工程過大,只好改用碑刻代替。
洪漱崖為人正直,多次竭力保護進步人士。已故中央民革主席朱蘊山與其系同學故交,朱蘊山思想進步,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密令逮捕他,洪漱崖獲悉后立即轉告朱蘊山,并連夜雇一小船將朱蘊山送到蕪湖,使其得以逃脫險境。洪漱崖還受張治中之命,曾將蔣介石通緝的愛國人士陶行知安全護送到上海。
1941年,張治中調任重慶國民黨中央任職,電召洪漱崖去渝。他寫了一首七言律詩《將之蜀留別耒陽諸友》,向耒陽的友人告別:“嘉禾不敢緩程期,已戒征車辦短衣。亂世為儒猶此役,無家有弟尚誰依。功名附驥老何望,文字雕蟲古已譏。枉辱贐詩壯行色,饑驅萬里更難歸。”不過,他未能成行,原因是“時弟同客耒陽,不得隨行”。
抗戰勝利后,洪漱崖看不慣國民黨官場腐敗,毅然辭職回鄉任教。新中國成立之初,安徽省省長黃巖受張治中來信委托,邀請洪漱崖出外工作,但洪因年逾花甲,力不從心,選擇在家鄉醫院為鄉人健康奉獻余熱。黃巖寄給他的300元生活補助費,他亦如數退回。1956年和1964年,張治中先后兩次回巢縣均派車接其晤談,每次饋贈500元,他均婉言謝絕。1976年,洪漱崖病逝。
洪漱崖是民國時期的重要詩人,有《漱崖詩集》存世。學者徐晉如在《略談二十世紀詩詞研究的幾個問題》中說:“現代自由精神,從一開始就是與反極權、吁民主的政治訴求聯系在一起,是二十世紀詩詞的主旋律。這一主旋律,濫觴自清末詩界革命派,而經陳獨秀、魯迅、郁達夫、陳寅恪、洪漱崖等發揚光大,遂能成就近百年來的一代之文學。”徐晉如把洪漱崖與陳獨秀、魯迅、郁達夫、陳寅恪相提并論,可見他在民國詩壇的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