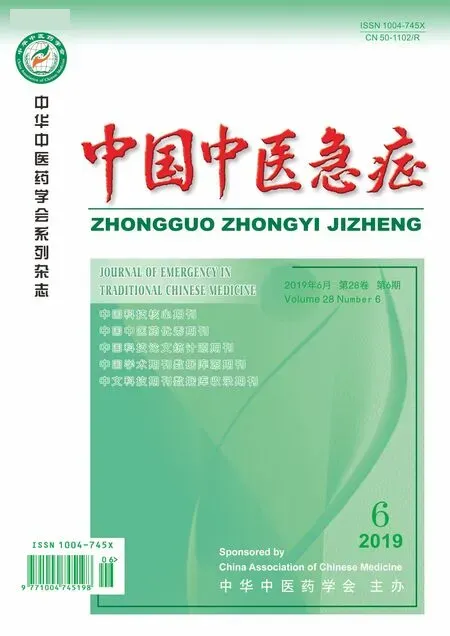基于溫病理論探討寒地小兒手足口病的病因病機*
劉麗麗 王有鵬 景偉超 關洋洋△
(1.哈爾濱理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手足口病是由腸道病毒(以柯薩奇A組、腸道病毒71型多見)引起的急性發疹性傳染病,臨床以手掌足趾、臀部及口腔皰疹,或伴發熱為特征。少數嚴重者可出現腦炎、腦膜炎、腦脊髓炎、神經源性肺水腫、循環障礙等。多發生于學齡前兒童,尤以嬰幼兒發病率最高。自1987年開始被報道以來,本病已波及我國大部分地區[1],并呈區域性流行特點。其中,北緯 45°以北的高緯地帶,每年至少2個月的時間日平均氣溫在0℃以下,冬季漫長、氣候嚴酷的城市,被稱為寒地城市[2]。臨床發現,寒地城市小兒手足口病臨床特點鮮明,與其氣候、地域特點密不可分。本研究參考《手足口病診斷指南 2010 版》[4],試運用溫病理論“一元化”地分析、闡明地域、氣候、體質、邪氣在手足口病發病機制中的作用,以形成寒地小兒手足口病的中醫辨治體系。現詳述如下。
1 中醫對手足口病的認識
本病為急性發熱、出疹性傳染病,大多醫家將其總歸于“溫病”范疇,因其具有傳染性,可稱為“溫疫”。因其發熱兼有局部紅腫、潰爛,有人稱之為“溫毒”。眾中醫醫家、學者對本病病因病機的認識尚存在分歧,可能與不同的地域氣候特點、人的體質特點及邪氣致病特點有關。
2 基于溫病理論對寒地小兒手足口病的認識
寒地城市小兒手足口病乃風溫毒邪所致,輕者傷脾、襲肺,三焦不暢,膀胱經氣不利,內濕與熱毒蘊阻于脾、肺、膀胱、心經絡局部;重者按衛氣營血傳變規律由衛入氣及營;危重者逆傳心包,邪陷厥陰。整個過程以風溫毒邪致病為核心,“三焦不暢”為風溫毒邪致病的進一步的演變結果,為伴隨的病理改變。此外,手足口病在兒童中廣泛流行,故病因病機的探討須結合小兒生理病理特點。
2.1 “風”邪為重要致病因素 國內很多學者研究表明,氣候因素與手足口病疫情存在相關性[3]。中醫認識、治療疾病注重“天人相應”。早在《素問·異法方宜論》就指出“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地域不同,五行主氣亦不同,故氣候特點、人的生活習慣及體質迥異,發病特點也差別很大。寒地多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全年多風;且寒地緯度高、海拔較高、遠離海洋,晝夜溫差大,中醫認為冷熱交替亦可為“風”。《素問·異法方宜論》云“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臟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北方寒地寒冷季節漫長,日照時間短,人們相對少動,代謝速度較慢,肥甘厚膩飲食相對較多,因此北方人形體敦厚,腠理致密而少開泄。至夏季濕熱之氣盛行,腠理開,加之風氣之開泄,易為風邪所襲。此外,肺為嬌臟,小兒肺常不足,衛表不固,更易感受風邪。風為陽邪,易襲陽位,葉天士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因此,感受手足口病邪氣初起表現為發熱、咳嗽、流涕、咽紅、舌紅苔薄黃、脈浮數等邪犯肺衛的癥狀。手足口病出現重證時可表現為抽搐、肢體抖動、肌陣攣、眼球震顫、共濟失調等,為邪陷厥陰、肝風內動所致。《黃帝內經》云“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熱淫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手足口病診斷指南2010版》[4](以下簡稱《指南》)在治療上,用辛涼輕劑銀翹散為主方疏散在外之風熱;用羚角鉤藤湯為主方清熱平肝以息內風,結合“涼開”之劑以醒神開竅。可見“風”邪因素已為專家們之共識。在寒地手足口病的治療上,我們更重視“辛涼輕解”“清熱息風”之法的合理運用。
2.2 手足口病的傳變規律和不同轉歸符合 “風溫”邪氣特點 中醫向來注重邪氣和正氣的辨證關系,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手足口病大都預后良好,在1周內痊愈。部分病例僅表現為皮疹或皰疹性咽峽炎[4]。部分病例表現為由衛及氣,再由氣及營的傳變規律。如寒地黑龍江地區小兒手足口病的證型包含了邪犯肺衛證、肺胃熱熾證、氣營兩燔證[5],此證型特點符合風溫病“衛-氣-營”而少入“血”的傳變規律。而濕溫病只要不化燥成溫,一般不入營分、血分,始終流連在氣分[6]。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未“逆傳”,說明感受的邪氣熱勢較微,不足以煎熬津液成痰,或患兒正氣充盛,心氣、心陰尚足,素體痰邪不盛,邪氣不陷,心絡不閉。現代醫學已經認識到了重型的手足口病是由腸道病毒71型引起的,此類邪氣熱勢較盛,可“逆傳心包,邪陷厥陰”,符合風溫病的傳變特點。病邪熱勢盛,正氣相對虛,年齡越小這種矛盾越突出,且年齡越小,肺、脾、腎越不足,越易生痰,外熱一陷,里絡就閉,與“手足口病重癥病例尤其是小于3歲者病情進展迅速”[4]的臨床特點相吻合。《黃帝內經》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溫病條辨·下焦篇》第36條“暑邪深入少陰消渴者,連梅湯主之;入厥陰麻痹者,連梅湯主之”[7]。痰熱蒙蔽心包,即心營痰蒙熱擾,表現為神昏譫語或昏聵不語,而邪陷足厥陰肝經可表現為肝風內動的四肢抽搐,均類似手足口病高熱、嗜睡、易驚、譫妄、肢體抖動、肌陣攣等臨床癥狀。此時熱勢較盛,似有暑邪之性,灼傷肝陰,筋脈失養,表現為肢體麻痹、腱反射減弱或消失等后遺癥。這些癥狀與濕溫病“濕熱釀痰,蒙蔽心包”之“身熱不揚、時昏時醒、呼之能應”有本質的不同。而《指南》[4]在治療重型病例時選用清肝息風、清心涼營、豁痰開竅的羚角鉤藤湯加減和“涼開之劑”安宮牛黃丸、紫雪丹,而非化濕清熱、芳香開竅之劑如蘇合香丸或至寶丹,印證了重型病例的病機為風溫病的痰熱蒙蔽心包及邪陷厥陰、肝風內動,而非濕溫病的“濕熱釀痰,蒙蔽心包”。
2.3 “濕”為繼發病理產物,非病邪特點 臨床上,濕溫病可從陽化燥成溫熱病,進而演變成溫熱病的傳變過程。但需滿足 “熱邪偏盛”“陽盛體質”“過用溫燥之品”3個條件,濕與熱結的濕溫病,濕與熱的消長轉變是較漫長的,與臨床上手足口病癥狀表現輕微而迅速出現肺水腫、肺出血等危重癥不相符合[8]。小兒雖“陽常有余”,但陽總歸“稚陽”,無法達到“陽盛”;而“過用溫燥”的誤治因素在現代臨床上基本不存在。因此,“濕溫病‘從陽化熱’轉歸成溫熱病”假說不成立,那么濕溫病的假設也就不成立。濕邪從何而來?《素問·經脈別論》說“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因此,濕乃三焦不暢化生而來,即邪氣侵犯肺、脾,脾失運化,肺失通調,三焦水道不通,膀胱失于氣化,加重三焦氣機壅滯,內濕形成。臨床表現為嘔吐、腹瀉、神情倦怠,甚或精神萎頓、苔膩或黃膩等。
日本學者的一項研究表明:手足口病的流行和當地前0~3周的濕度和溫度呈正相關[9]。寒地黑龍江手足口病高發于夏秋季節7~9月[5],為自然界濕熱之氣主令,此季節濕熱氤氳蒸騰,易致三焦氣機不暢,內濕與外濕相合,加速發病進程,此“濕”為六氣之濕,而非邪氣特點。此外,“濕邪重濁黏滯”“濕熱相合如油裹面”,臨床上手足口病患兒多為高熱,病程較短,多在10 d以內[5],部分病例進展較快,與濕溫病“傳變較慢、病勢纏綿”迥異,印證了手足口病的病邪特點以“溫熱”為主而不以“濕”為主。眾醫家在闡述手足口病的病因時,對于“濕”的存在并無太大分歧。 《指南》[4]在列舉治法時,雖提出“化濕”,但并未將“化濕”置于語首;在列舉方藥時,盡管未標明使用劑量或比例,但從藥性和藥味數量分析,化濕藥多作臣藥或佐藥,有芳香化濕的青蒿、藿香、佩蘭,淡滲利濕的通草、滑石、川萆薢、生薏苡仁,藥性偏于柔和,熱象明顯時才考慮用苦寒的梔子、黃芩、黃連。 因此,可以推斷《指南》[4]承認有“濕”的因素,但并未將“濕”作為主要的致病因素。從臨床來看,越來越多的手足口病病例發生于夏秋以外的季節,如春季、初冬,非典型濕溫病所能解釋[10]。
2.4 “毒”蘊阻部位反映了病變臟腑 手足口病主要表現為口腔、手足、臀部的丘疹、皰疹,乃內濕與熱毒蘊阻于經絡局部,因皮疹不甚疼痛,故為“蘊阻”而非“結”于血絡。《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唇口病論》述“風毒濕熱,隨其虛處所著,搏于血氣,則生瘡瘍”[11]。風毒濕熱于“虛處”與“血氣”相搏,可理解為手足口病的皮疹多在四末,或遠心的口唇,或常因坐擠壓的臀部,氣血運行較緩,濕邪、熱毒易阻滯。這種理論同樣可在臨床實踐中得到驗證。如《指南》[4]在治療的濕熱郁蒸證時用到了牡丹皮、赤芍,即為濕邪、熱毒蘊阻于局部,氣滯血瘀的病機而設。邪氣蘊阻的部位反映病變的經絡及對應的臟腑。《痘疹心法要訣》云“水泡濕淫克脾經,手足稠密身面輕”[12],《幼幼集成》曰“如舌上生瘡,赤者謂之赤口瘡,此熱在心脾二經”,又曰“但云六經加味,而不指明處所,未免闕略。今分晰之,以便治療。太陽經所屬:項、背、腰、臀、足外臁、足腨……太陰經所屬:中脘、四肢、兩足胕;少陰經所屬:臍腹、手足心、手足內臁、足跟”[13]。 風溫毒邪內乘心、脾二經,心脾熱盛,心氣通于舌,脾氣通于口,且脾主四肢,故手足部、口舌可見丘疹、皰疹。脾失運化,肺失通調,三焦水道不通,膀胱失于氣化,膀胱經氣不利,內濕與熱毒蘊阻于膀胱經絡,故臀部可見丘疹、皰疹。《御纂醫宗金鑒·編輯痘疹心法要訣·痘形并證治門》中“鱗坐”注解認為“臀”為至陰之地,乃“毒火太甚”所致[14];又膀胱屬下焦,邪傳至下焦提示病深邪重。因此,皮疹見于臀部提示毒熱較甚,病情較重。丘疹、皰疹現于臀部的病機及臨床意義,鮮有學者提及,結合經絡辨證、臟腑辨證、三焦辨證加以解釋,看似自圓其說,而非憑空捏造。《指南》[4]用歸膀胱經的滑石、白茅根、萆薢等疏利膀胱經氣,已助氣血暢通,濕、毒無所依附,促進康復,是為有力佐證。
2.5 “三焦不暢”為伴隨的病理改變 “三焦不暢”主要由外邪侵襲肺、脾所致,可因內傷積滯誘發或加重;而內濕由“三焦不暢”所生,且兩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惡性循環。良好的生活條件,長輩的嬌寵,肥甘厚膩的地域飲食特點及飲食不能自節等因素使小兒易生積滯,日久損傷脾胃,生濕可誘發或加重“三焦不暢”。若化熱則可出現心脾積熱證或胃熱熾盛證,表現為心煩、口舌疼痛拒食、溲赤便結、舌紅、脈數有力等。若蘊濕生熱傷陰,則小兒更易感風溫邪氣,感邪后兩熱相搏,充斥內外,表現為一派陽、熱、實之象,甚至發生入營、動風之傳變。這符合普通病例和重型病例手足口病病機的一般演變規律。在手足口病危重型病例的發展過程中,可出現咯吐粉紅色或血性泡沫痰,相當于現代醫學神經性肺水腫,可能是腸道病毒71型引起腦干損傷,致交感神經興奮,釋放大量腎上腺素能遞質,引起廣泛周圍血管收縮,體循環血液大量進入到肺循環引起的肺水腫[15]。 中醫認為此乃熱毒熾盛,重傷肺、脾、心,三焦閉塞,水飲內聚,凌心迫肺,傷及心陽,心血瘀滯,津不化加重飲停,飲瘀互結,宗氣虛陷。此病機早期的關鍵在于飲邪,與心源性肺水腫早期以心陽虛衰為主的病機不同,故治療時考慮以瀉肺逐水為主,方用己椒藶黃丸合參附湯加減[16]。總之,“三焦”病變在整個病理發展過程中居于重要地位。
3 結 語
中醫的精髓是辨證論治,而病因病機是連接“證”與“治”的橋梁。臨床療效和對臨床的指導意義是檢驗病因病機是否科學、嚴謹的重要標準,因此,病因病機的提出除了符合中醫理論中相關病證特有的發展演變規律,還應當對臨床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及指導下的良好的療效。中醫藥防治手足口病在疫情防控中起著重要作用,越來越被社會所認可,未來應具有更為廣闊的前景。雖本病可查閱的古籍文獻有限,但在各醫家不懈鉆研下,大都取得了滿意的臨床療效。目前,中醫對手足口病病因病機的認識還相對模糊,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再加上不同地域氣候不同、人的體質不同,眾醫家在認識上很難達成共識。筆者通過觀察寒地小兒手足口病的臨床特點,結合專家們的共識,分析、總結、歸納出適合寒地小兒手足口病的病因病機,為寒地小兒手足口病形成較為系統的中醫辨治體系及手足口病的防控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