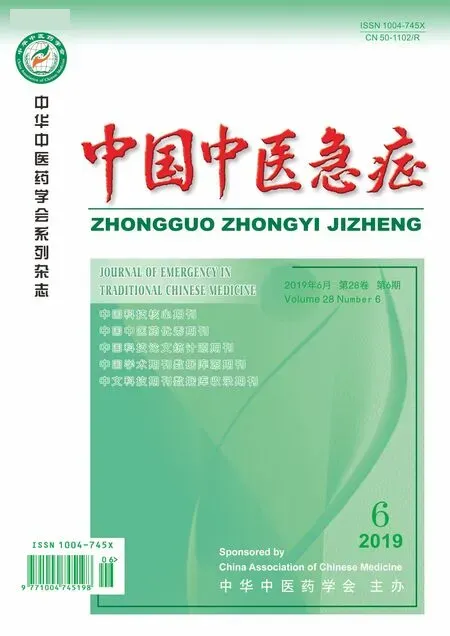六經辨證論治重癥肺炎
劉曉芳 劉 瓊 潘家文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405;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東 廣州510405)
重癥肺炎是由肺組織(細支氣管、肺泡、間質)炎癥發展到一定疾病階段,惡化加重形成,引起器官功能障礙甚至危及生命。本病的病死率高達30%~50%,可導致嚴重的并發癥[1],盡管目前臨床檢驗手段不斷發展、生命支持技術不斷完善、抗菌藥物的治療效果不斷優化,但發病率、病死率仍然很高[2]。 多個臨床研究[3-4]發現采用 《傷寒論》中的經方聯合西醫結合治療重癥肺炎,對調節炎癥因子水平,促進免疫平衡,改善患者癥狀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目前尚無采用六經辨證思路指導經方應用的報道。
在中醫學中無“重癥肺炎”病名,類似的癥狀及病情發展的描述在許多中醫古籍中都能窺見。現代醫家多參照 “暴喘病”“喘脫”等病進行辨證施治[5]。 筆者認為從六經傳變的角度闡釋重癥肺炎的發生發展過程,可以更好地去闡釋病情及指導治療,臨床上也頗有療效。
1 重癥肺炎與六經辨證
六經辨證的實質歷來有諸多學說,如六經經絡論、六經臟腑論等,筆者認為單從臟腑或是經絡解說六經辨證相對單薄,比較認同的是時振聲的觀點——六經辨證的全過程是急性熱病正邪消長的反映[6]。六經傳變融合了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正邪等理論,考慮到了病因、體質、病性、病勢、病位的特點,體現整體觀念,反映疾病發展的陰陽變化,邪正盛衰及病位深淺,從太陽到厥陰,病邪逐步深入,正氣逐漸衰微,十分類似重癥肺炎從外感初期逐漸發展到多器官功能障礙的疾病發展過程。治療上應觀其脈診,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1.1 重癥肺炎之太陽病 太陽病的總綱——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肺臟之病應當先考慮太陽病,《傷寒指掌》云“肺主衛,主氣,主皮毛。風寒先從皮毛,內應乎肺,又太陽一身之表。故肺家之邪,即可以候太陽之表”[7],重癥肺炎初起有惡寒發熱,鼻塞流涕,咳嗽咳痰等癥狀,初起時正氣充盛,邪氣暫未傳經入里,如果此時早期干預,驅邪達表,便不會形成重癥,治療上多以桂枝湯或麻黃湯之類,如誤治或素體不足,太陽經氣氣機失調,便容易形成太陽變證,或兼證,病理上炎癥逐漸波及肺實質,出現喘促癥狀,如“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的麻杏甘石湯證,“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咳……或喘,小青龍湯主之”,此時應當在解表的基礎上加以化痰平喘。張高峰等臨床研究發現老年重癥肺炎患者實施加減小青龍湯聯合莫西沙星治療臨床療效顯著,可明顯改善患者臨床癥狀,有效提高患者免疫功能,并下調血清 IFN-γ、IL-1β、PCT 水平[8]。
太陽病多在重癥肺炎病情早期,應該及早扶正氣,驅邪外出,莫以為太陽病病位淺表,病情輕微,卻不予重視,治病應該先安未受邪之地,莫待傳變。《金匱要略》云“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睥,當先實睥,余臟準此”。臨床醫生在流感高發季節應該多加警惕,但一旦失治誤治便容易病邪內陷,形成重癥,臨床上會發現患者陳述病情多雜而難辨,但是根據六經辨證則相對簡單,諸多癥狀都應當歸于表證的范疇,治療上以解表為首發,可以達以簡馭繁之效。
1.2重癥肺炎之陽明病 陽明病的總綱——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又有言——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黃帝內經》曰“大腸小腸皆屬于胃”“邪氣盛則實”,揭示陽明病為邪氣漸熾盛,病邪進一步入里,病位在胃腸,病變以里熱實,無表癥為特點,又可就里熱是否與腸中積滯相結合,分為陽明氣分熱證及陽明腑實證。重癥肺炎是陽明氣分熱證,在臨床上可見大渴,大熱,脈洪大,甚至可能出現躁狂、昏迷等邪熱熾盛的表現,此階段為感染進一步加重的表現,治療上應辛涼清熱,或兼以養陰,臨床上可與白虎湯加減。唐燕等應用白虎湯加減聯合胸腺素治療老年重癥肺炎患者也確有實效[9]。而陽明腑實階段,患者多見腸道功能障礙,肺與大腸相表里,燥屎積聚,腑氣不通,肺氣不宣,邪熱難清。現代醫學認為,腸道是機體最大的細菌及內毒素儲存庫,而重癥肺炎患者長期臥床,胃腸蠕動較常人減弱,且嚴重感染會引起應激性胃腸功能紊亂,致腸道菌群失調,內毒素移至血液或免疫系統[10],此時應用通便法,有利于調節腸道功能,有利于內毒素的排出,對改善機體的內環境有一定好處。治療上可根據患者“痞、滿、燥、實”輕重情況選擇相應的承氣湯運用。臨床研究發現應用承氣湯應用不局限于內服,更可外用。劉克琴等采用大承氣湯灌腸治療重癥肺炎患者較單純西藥相比,能明顯改善患者中醫證候評分,縮短機械通氣時間和抗生素療程[11]。
1.3 重癥肺炎之少陽病 《傷寒論》97條有言“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于脅下”,提示少陽病為正氣虛弱,邪氣進一步入里,或是素體虛弱,抗邪無力,少陽本經受邪,此時正邪交爭,各有勝負,少陽為三陽三陰樞紐,如此時治療得法,當表解里和而愈。少陽病的總綱為“口苦,咽干,目眩”,還可以參見96條所說“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胃熱,或咳者”。因邪犯少陽,樞機不利,致病變影響表里內外,出現多種或然證,此時因重癥肺炎患者中期多為藥物鎮靜狀態接呼吸機輔助通氣,許多癥狀或許不顯,臨床多見反復發熱,熱邪難退的情況。或是重癥肺炎后期,邪氣由里外出,患者正氣漸復,反復低熱、咳嗽咯痰、納差、精神疲倦等癥狀[12],治療上予和解表為大法,方選小柴胡湯加減。
1.4 重癥肺炎之太陰病 太陰病起,病邪由陽入陰,代表正氣弱于邪氣,“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太陰病與太陽病皆有胃腸功能障礙,但所謂“實則陽明,虛則太陰”,太陰病時正氣虛弱,此時不宜攻伐太過,《傷寒論》中亦有“存胃氣”之訓。重癥肺炎患者在此階段常已無發熱癥狀,主要表現為吐、泄,或是胃潴留的情況,臨床上多認為重癥感染的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多始于胃腸功能紊亂[13],如果能及早改善腸道功能,可以改善預后[14]。該情況也可見于長期應用廣譜抗生素后出現的腸道菌群紊亂,另“脾為生痰之源,肺為儲痰之器”。太陰脾虛,水濕失運,痰濁內生,患者多有咳嗽咯痰,痰多色白,又因體虛,咯痰不利,容易加重感染,此時應治療可選用理中丸、四君子湯、參苓白術散等,強健脾胃,運化水濕。此培土生金法,爭取保胃氣,存生機。
1.5 重癥肺炎之少陰病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此時病邪更深入,正氣虛弱,或是本身正氣衰微,病邪直接從太陽,直接入里,老年性重癥肺炎多見。臨床上主要表現為休克早期表現,意識水平下降,或呈嗜睡狀態,或是休克血壓,少陰主責在腎,此時腎陽衰微,病情危重,有一定死亡的風險,應急予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以回陽救逆。附子被稱為“回陽救逆第一品”。現代藥理發現,附子及其成分可通過影響β腎上腺素能受體和 NF-κB、AMPK、PI3K/Akt、BDNF 等信號轉導通路發揮強心、保護心肌細胞、抗心律失常等藥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升壓效果[15]。此時對于患者而言最基礎的生命支持及抗感染應放在首要地位,搶救生命于危急中,中藥起一定的輔助作用。
1.6 重癥肺炎之厥陰病 《傷寒論》云“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厥陰多死證,此時病多在終末階段,病情復雜,正氣殆,邪氣盛。《傷寒論》云“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陰陽氣機失調,臟腑功能紊亂,多為寒熱錯雜之象,重癥肺炎患者在此階段多出現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患者可表現為休克征象——意識障礙、血壓低、膚溫低、少尿或無尿、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等。疾病發展進入此階段,為搶救的關鍵時期,此時為陰盡陽生,不僅需救陰還需扶陽,用藥上多寒熱錯雜,如烏梅丸、麻黃升麻湯等。
1.7 重癥肺炎之六經合病 六經傳變可以很好地解釋重癥肺炎的發生發展過程,但是臨床上更多見的是六經并不一定會單獨出現,會出現錯綜復雜的證候。六經傳變的過渡狀態,各病之間可相兼出現,臨床重點在于——觀其脈癥、知犯何逆、隨癥治之、兩經合病。兼見兩經的證候,如太陽陽明合病,便可同時見外感癥狀合并燥屎結滯腸中。重點在于對于基礎六經證候的把握和對《傷寒論》條文的熟悉,在臨床可以有以簡馭繁之效。
2 驗案舉隅
患某,男性,25歲,酒店工作人員,自訴既往史、接觸史無特殊,因“發熱伴咳嗽7 d”2018年10月9日入院。患者于10月3日無明顯誘因出現惡寒發熱,體溫達38.1℃,偶有咳嗽、無痰,伴左側胸痛,無胸悶、氣促、咯血,無腹瀉、腹痛、惡心、嘔吐等癥狀,在當地醫院就診,胸部CT示左肺下葉團片影,性質待定:肺栓塞?肺部感染?予莫西沙星聯合多西環素治療3 d后,仍反復發熱,10月7日復查胸部CT提示:左肺病灶較前增多。予比阿培南聯合奧硝唑治療3 d,患者體溫仍波動在38~40℃,咳嗽癥狀逐漸加重,咯少量黃黏痰,稍氣促,為進一步治療收入我院,癥見:患者神清,精神疲倦,口苦,發熱,自汗,微惡寒,發熱時頭痛,稍氣促,咳嗽,咯少量黃黏痰,無鼻塞流涕,無皮疹,無關節疼痛,無頭暈,無腹痛腹瀉,納差,眠差,二便調,舌紅,苔厚黃,脈移。查體:血壓119/78 mmHg,呼吸頻率30次/min,心率 110次/min,體溫 38.5℃,SpO290%,左下肺叩診濁音,聽診左下肺呼吸音減弱。血氣分析:pH 7.482,pCO228.3、pO265.9 mmHg, 吸氧濃度 25%,Lac 2.7 mmol/L。肺動脈螺旋CT:考慮雙肺感染,病灶較前增多,左側少量胸腔積液(葉間裂局部包裹),雙肺CTPA未見明顯異常。中醫診斷:風溫肺熱病。西醫診斷:重癥肺炎。予亞胺培南西司他丁鈉、莫西沙星抗感染聯合磷酸奧司他韋膠囊抗病毒治療。結合舌脈屬太陽與少陽合病,六經辨證考慮為太陽與少陽合病,方用柴胡加桂枝湯加減:柴胡10 g,桂枝 10 g,黃芩 10 g,法半夏10 g,甘草片6 g,厚樸15 g,苦杏仁10 g,白芷10 g,防風 10 g,龍骨 30 g(先煎),牡蠣 30 g(先煎),青蒿 10 g(后下),連翹 10 g,石菖蒲 10 g,蘆根 20 g。 每日1劑,水煎至250 mL,溫服,服藥3 d后熱退,咯痰同前,氣促則較前減輕,其效可期。治療2周后,患者一般情況較前明顯改善,活動耐量可,予辦理帶藥出院。囑按時服用(阿昔洛韋、氟康唑膠囊、頭孢丙烯),7 d后門診復診,復查胸片示:左側胸腔少許積液,左肺感染明顯好轉。
按:《傷寒論》少陽病篇第225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患者傷寒已過7 d,仍微惡寒,表證未解,逐漸見于少陽里也,外邪襲肺,肺失宣降,發為咳嗽,結合舌脈屬太陽與少陽合病,六經辨證考慮為太陽與少陽合病,方用柴胡加桂枝湯加減。本方以柴胡冠桂枝之上,意在解少陽為主,散太陽為兼也。方用柴胡透泄少陽之邪從外而散,疏泄氣機之郁滯,黃芩助柴胡以清少陽邪熱,柴胡升散,得黃芩降泄,則無升陽劫陰之弊;半夏降逆和胃,桂枝解肌發表,青蒿、連翹[16]退熱解表,還有抗流感病毒作用,杏仁宣肺枳殼,厚樸行氣化滯,白芷、防風祛風濕,止頭痛,蘆根養陰生津,化濕開胃,石菖蒲開竅豁痰,龍骨、牡蠣重鎮安神,生甘草瀉火和中,調和諸藥,其效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