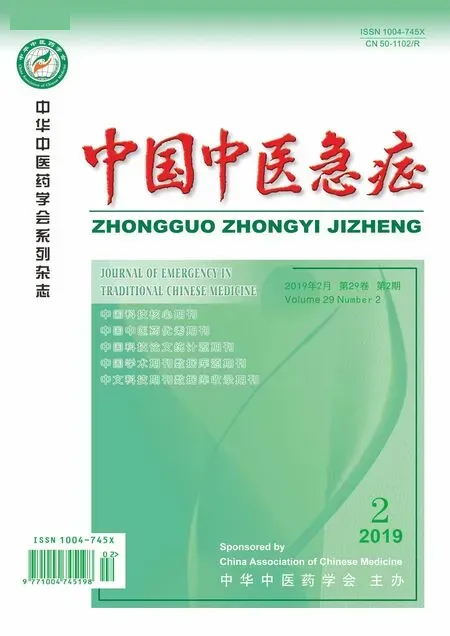張雄教授治療鼻竇炎的臨床經驗*
高 莉 李 菁 侯 薇 徐 璐 蘇 濤 徐俊艷 徐 芳 指導 張 雄
(陜西中醫藥大學,陜西 咸陽 712000)
鼻竇炎是臨床常見病、多發病,臨床發病率達10%,在鼻病中達23.5%。西醫治療鼻竇炎主要以抗過敏、抗感染、減充血、促排黏液、手術等方式治療。雖然短期療效顯著,但有易反復發作、產生耐藥性、手術費用高甚至術后復發率高等弊端[1]。張雄教授是陜西省名中醫,從事中醫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療與研究30余年,臨床經驗豐富,治療耳鼻喉科各種疾病有自己的獨特方法,療效顯著。筆者有幸侍診左右,得到啟發,闡述老師治療鼻竇炎的臨床經驗與臨證思路,加深自己對中醫治療鼻竇炎的理解,還望同行斧正。
1 抓主癥,用經方,強調辨證論治
臨床上常見的鼻竇炎一般分為急性期和慢性期,大致包含中醫的“傷風鼻塞”和“鼻淵”。張師認為,其病因從中醫講不外虛實兩端,其發病多由于正氣虛損,外感風寒濕熱邪氣或飲食不節,損傷脾胃,濕熱內生蘊結,化生痰濁瘀滯。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若脾肺虛損則清陽無升難濡頭面官竅,同時濕熱濁陰不降而蘊于頭面官竅,則鼻竅失養又受邪堵塞,終致鼻竇炎。張師認為,鼻竇炎的外感因素風、寒、濕、熱邪氣中,又尤以熱邪為重,劉完素曰“凡痰涎稠濁者,火熱極甚,銷濁致之然也”。《醫學入門》亦曰“鼻淵者,鼻流濁涕,熱甚”。張景岳則言“鼻淵總由太陽督脈之火,甚者上連于腦而津津不止,故又名腦漏。此證多因酒醴肥甘或久用熱物,或火由寒郁,以致濕熱上蒸,津液溶溢而下,離經腐敗”,亦指明鼻淵的重要發病因素為熱。王士貞教授認為鼻淵一病,始于邪,成于熱,釀膿涕,久致虛,兼痰瘀[2],劉德榮教授認為濕熱痰邪為鼻淵發病之標,故清熱在治療過程中獨樹一幟[3]。《辨證錄》中治療鼻淵的經典方劑取淵湯亦是從清熱利濕角度下手,為后世醫家所推崇,國醫大師干祖望認為治療鼻竇炎當以清泄膽熱為主[4]。
臨床上鼻竇炎的診斷[5]主要依據為四大主癥:鼻塞、流涕、頭痛頭昏、嗅覺減退,專科檢查則見鼻黏膜淡紅或充血腫脹、呈息肉樣變或鼻甲肥大、鼻腔分泌物量多而清稀或呈黏膿性、面頜顱枕不同部位壓痛叩痛。張師認為,中醫治療鼻竇炎應當辨證論治,在明確疾病的診斷基礎上結合主癥偏重及兼證特點,臨床上一般多可分為四大證型[6]。1)肺虛寒犯證:以鼻塞甚噴嚏頻、涕量多而清稀或白黏、頭昏頭脹痛為主,兼有肺氣虛或風寒外襲的全身癥狀;治宜益肺散寒、通竅止痛,方用蒼耳子散(《濟生方》)加減,若鼻涕黏多,酌加陳皮、半夏、枳殼等燥濕理氣。2)肺經風熱證:以鼻塞、涕量多而白黏或黃稠、嗅覺減退為主,兼有外感風熱的全身癥狀;治宜疏風清熱、宣肺通竅,方用銀翹散(《溫病條辨》)加減。如涕量多而稠黃,酌加蒲公英、魚腥草、土茯苓等燥濕排膿;如頭痛甚,可酌加蔓荊子、羌活、防風等祛風止痛。3)膽腑郁熱證:以鼻涕濃濁量多黃或黃綠伴腥臭味、頭痛劇、鼻塞甚而嗅覺減退嚴重為主,兼有肝膽濕熱證的全身癥狀;治宜清泄膽熱、利濕通竅,方用龍膽瀉肝湯(《醫方集解》)加減。若涕濃濁黃綠甚,酌加茵陳、木通清熱利濕;頭痛劇烈酌加白芷、石膏清熱止痛。4)脾胃失運證:以鼻塞重而持續、鼻涕量多或白黏或黃稠為主,兼有脾虛不化或濕熱蘊結的全身癥狀;治宜健脾利濕、化濁通竅,方用參苓白術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加減。如鼻涕帶血,酌加仙鶴草、槐花、白茅根、黃芩等涼血止血;如嚏頻涕清,加重黃芪、白術、防風用量。
故張師強調,在鼻竇炎的診療過程中,我們應當時刻記住兩點:抓主癥與辨證論治。根據患者顯著癥狀,鼻塞、流涕、頭痛頭昏、嗅覺減退中的部分或全部癥狀和鼻部專科檢查、結合輔助檢查足以明確診斷,再根據主癥之偏重及兼證之表現確定證型,處以相應治則治法與方藥。張師所選方藥皆為前賢之經方,臨證運用視病情之偏重加減化裁,靈活運用,循古不泥古。如選蒼耳子散為治療五官科諸病諸多證型之方,銀翹散為治療諸病外感風熱證之方,龍膽瀉肝湯為治療諸病肝膽濕熱證之方,參苓白術散為治療諸病脾虛濕盛證之方,均在診斷明確、辨證論治的基礎上辨證應用。
張師在臨床上發現,在鼻竇炎的疾病發展與診療過程中,實證各證型皆離不開“熱”,《名醫雜著》亦曰“鼻塞……殊不知此是肺經有火,邪火甚則喜得熱而惡見寒,故遇寒便塞,遇感便發也”。在虛證中,肺脾氣虛,易受外邪侵襲,致寒氣郁而化熱,脾虛生濕化熱,故本著辨證論治、對癥治療的原則,清熱思想應貫穿治療全程,時刻注意癥狀的熱證程度與熱勢發展趨勢而給予相應藥物。如肺經風熱證注意清熱散熱,主方基礎上酌加菊花、桑葉、蔓荊子。膽腑郁熱注意清熱排膿,主方基礎上酌加蒲公英、魚腥草、桔梗。脾胃濕熱證注意清熱利濕化濁,主方基礎上酌加薏苡仁、澤瀉、茯苓。肺虛寒犯證注意防止治療時發散外邪太過以致生熱化燥損傷肺陰,因肺為嬌臟、體清虛喜濡潤的生理特性,可酌加白薇、玉竹解表滋陰,生地黃清熱生津,以適肺性。張師視疾病癥狀之偏重和不同階段而酌加不同藥物對癥清熱,體現了既抓“熱”之突出癥狀的整體辨證思想,又體現了清不同“熱”的辨證論治的思想,亦是循古不泥古。
2 活用中藥與針灸,強調經絡辨證
張師多年臨床經驗認為,頭頜部疼痛為鼻竇炎患者最為苦惱之癥狀,尤其影響青少年記憶力與學習,故就對癥治療而言,解決患者頭痛為治療之當要。就治療全程而言,解決患者頭痛有利于取得患者的信任而為有效治療創造機會。中醫經絡理論認為經絡因其運行氣血、聯絡官竅的生理作用,一旦氣血不通、臟腑功能失常則表現出局部或循行部位的疼痛的病理狀態,此為中醫的“循經診斷”“分經診斷”理論,據此可根據鼻竇炎導致的頭痛部位判斷受邪經絡,有利于辨證準確及對癥治療。外邪侵犯機體后阻滯于清竅而致鼻塞及鼻腔分泌物增多無以排暢,蘊結堵塞,加上經絡不通、經氣不利,合而導致與加重頭頜部疼痛。中醫經絡辨證論治頭痛淵源已久,臨床應用療效顯著,耳鼻喉科可以借鑒用于治療鼻竇炎導致的頭頜部疼痛。西醫鼻竇炎的分期分型不同則疼痛部位與特點不同,有利于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此為局部診療思想,體現了西醫的“精確診斷”與“治病”的理論。現代醫家研究也認為鼻源性頭痛與原發性頭痛的診療應當嚴格區分,鑒別診斷很有必要[7]。臨證中,張師指出中醫講對癥治療、異病同治,可以借鑒分經論治頭痛的思想,活用引經藥治療鼻-鼻竇炎之頭頜部疼痛。西醫的分期分型診療鼻竇炎的觀點與中醫的“辨證論治”“分經論治”等治療鼻竇炎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臨床診療上遙相呼應。故在鼻竇炎的中醫治療中,本著經絡辨證的原則,發揮兩大中醫特色:中藥之引經藥的引藥直達病所的特殊作用及藥對的相須相使的特殊作用和針灸之穴位的近治、遠治作用。
引經藥在治療頭痛中的應用首推古醫家王好古的《此事難知·鼻淵》中的總結性論述,其淵源為《湯液本草》的“太陽則羌活,少陰則細辛,陽明則白芷,厥陰則川芎、吳茱萸,少陽則柴胡”。對于治療鼻竇炎導致頭痛的引經藥的應用,中醫界提出了川芎、柴胡等[8-9]。在此,張師認為,雖然鼻竇炎的西醫頭痛部位與中醫的頭痛分經論治在思想上可類比,中藥的“引經報使”思想可類比于西醫的“靶向治療”觀點,但在治療上臨床醫師切勿生搬硬套,比如,西醫的慢性蝶篩竇炎疼痛若發生在頭巔頂及顳部就胡亂堆砌吳茱萸、藁本、柴胡、黃芩,而應全程貫徹中醫辨證論治與分經論治的思想。同時還可根據證型適當添加引經藥,發揮中藥的相須相使的作用。如,肺虛寒犯證,可加辛夷、桔梗,取辛夷與蒼耳子合而為通竅藥對、桔梗引藥上達頭部之意,又取辛夷祛風散寒、桔梗宣肺祛痰功效皆恰適此證型鼻竇炎惡寒、涕多癥狀之意;脾胃失運證,可加蒼術、升麻,取分別具止陽明頭痛、引藥上行之意,還取蒼術健脾燥濕從而減少痰濁鼻涕生成、升麻發散郁熱而防脾胃失運之濕熱蘊結諸癥之意。張炳厚教授[10]認為,單味引經藥可分為臟腑經絡引經藥、疼痛引經藥、清熱引經藥、藥力走向引經藥,并受《傷寒論》經方類方的啟迪,創造性地提出并闡述“引經方”的概念與應用,為我們運用引經藥引經方提供了明確的方向與清晰的思路。
張師認為,耳鼻喉科疾病因其發病為頭面,是清陽之會的特殊部位,又耳鼻咽喉諸竅為五臟六腑之外竅,故鼻病的治療法則皆為宣肺、通竅的治療大法服務。故臨床醫師在隨證加減中應時刻注意重用或添加宣肺通竅之品,加上鼻塞為鼻竇炎最重要的癥狀之一,通竅亦為對癥治療。無論鼻竇炎是何證型,酌加具有直接或間接治療鼻病功效的藥對,多能顯效。張師總結臨床經驗,獨創鼻病藥對。對于鼻淵,鼻塞甚則加重蒼耳子、辛夷花祛風通竅藥對;鼻涕黃稠黏濁則加蒲公英、魚腥草祛瘀排膿藥對;鼻涕清而量多則加烏梅、訶子收斂止涕藥對;頭痛甚則加川芎、羌活祛風止痛藥對,皆可取得“四兩撥千斤”之效。張師總結,諸多經典方劑為藥對,如二至丸、左金丸、當歸補血湯,藥簡力專,體現中醫中藥的精而不繁的思想。這與其他醫家的經驗不謀而合[11-13]。
針灸治療各科疾病的某些病種有其獨特優勢[14-15]。張師指出,頭面部為三陽經直接循行的特殊部位,耳鼻喉科治療更應當充分發揮針灸治療特色,靈活、創新地將針灸為己所用。針灸治療鼻竇炎的基本原則是清熱宣肺通竅,主穴以局部之印堂、迎香、風池和鼻竅所屬臟腑之經絡穴位列缺、合谷,隨證加減配穴,理同方藥之辨證論治,常規針刺穴位,少商點刺出血。穴位注射法的操作方法為取穴合谷、迎香,每次每穴注射復合維生素B注射液0.2~0.5 mL,隔日1次;耳針法為取穴內耳、下屏間、額、肺,毫針刺,間歇捻轉或埋針1周。
3 重視肺脾,強調幼童防護
臨床上觀察到,兒童鼻竇炎的發病率居高不下,因年齡小耐受力弱的原因,家長與醫師皆傾向于非手術治療,故中醫特色治療受到青睞。《萬氏家藏育嬰秘訣·五臟論治總論》的“三有余、四不足”理論指出,小兒陰氣、肺脾腎常不足,陽氣、心肝常有余,同時小兒的生理特點為臟腑嬌嫩,稚陰稚陽、血氣未充,且小兒易隨氣候變化等因素而發病,傳變迅速,故臨床上小兒鼻竇炎發病就診時多表現為肺虛寒犯證。但是感受寒邪后,稚陽之體質加上小兒飲食不知節制,多食且好肥甘損傷脾胃,水濕不化易蘊熱,容易導致病情加重而纏綿難愈。
張師提出,小兒鼻竇炎的治療注意兩大要點:病初防發展,時刻顧肺脾。小兒鼻竇炎就診時外邪多處于皮膚經絡間,未深入臟腑骨髓,病情多處于輕淺階段,醫者應當抓住病情輕淺的時機及小兒臟氣清靈易趨康復的病理特點,有必要且容易阻斷病情發展。《赤水玄珠》言“此必治之早也,當以保肺為君,開郁順氣為臣……清竅無塞”,可見治療中解表的重要性。這一過程多使用質輕之中藥,如防風、蒼耳子、薄荷、蔓荊子等,以祛除邪氣,質輕力弱又恰適小兒臟腑嬌嫩的特性,避免藥重而傷害稚體。西醫解剖學理論認為,鼻竇、鼻腔相通,各個竇口位置偏近,一腔出現炎癥可引起交叉感染,然后迅速傳播,后果嚴重,同樣認為鼻竇炎應及早治療[16]。
同時,應注意小兒是否有肺脾氣虛的表現與癥狀,視病情程度可酌加白術、黃芪等健脾益肺、甘淡而不壅塞的藥物。病情日久,容易生濕化熱而表現為頭痛劇烈、黏膿黃涕等實證,亦因肺脾氣虛之根本,可在中藥的配伍原則的指導下適當添加健脾消導的藥物,如焦山楂、炒神曲、炒麥芽等,既顧護脾胃,又兼化濁涕散痰結之意,此淵源可追溯于李東垣的“脾虛則九竅不通”觀點及創升清降濁法用補中益氣湯治療鼻淵的思想。同時肺脾二臟在五行理論中為母子相生關系,脾土母虛則肺金子弱,故治療上采用培土生金法,健脾也即益肺,肺氣通暢又助脾胃升清降濁,肺之外竅鼻竅亦安然,正如經曰“肺和則鼻能知香嗅矣”。這與其他國醫大家的經驗有相似之處[17-18]。
4 病案舉例
患某,男性,11歲。2016年9月22日因“間斷鼻塞、流黃膿涕伴頭痛1年余,再發加重半月”于筆者所在科室就診。患者1年前感冒后鼻塞、流清涕伴頭昏頭痛,于某醫院兒科以“感冒”對癥治療,病情痊愈后停止治療。近1年常因天氣變化甚無明顯誘因則出現鼻塞伴頭痛,流黃膿涕,嗅覺時有減退,于某西醫醫院就診,行鼻竇CT(冠位平掃)確診為慢性鼻炎、慢性鼻竇炎,醫生建議住院手術治療,家長考慮患兒年齡而拒絕手術,要求西藥保守治療,癥狀可緩解但易反復發作,影響患兒學習與生活質量,家長遂來我院要求中醫藥保守治療。門診訴:鼻塞,流黃膿涕,量多,伴頭痛,主要位于眉棱骨、雙顳部,無明顯時間規律,影響睡眠,嗅覺減退,納食差,大便稍結,小便黃,舌紅,苔黃厚膩。專科檢查:鼻腔黏膜充血腫脹,見黃色膿性分泌物,雙側下鼻甲腫大,鼻中隔尚正,頭頜、眉棱骨壓痛。診斷為鼻窒、鼻淵,屬肺經蘊熱證,治宜清熱化濁,通竅止痛,方用蒼耳子散化裁:蒼耳子6 g,辛夷花6 g,白芷6 g,蔓荊子6 g,藁本 6 g,川芎 6 g,石膏 15 g,桑白皮 6 g,魚腥草10 g,蒲公英 10 g,桔梗 6 g,澤瀉 6 g,車前子 3 g,焦山楂10 g,神曲6 g,甘草3 g。7劑,每日1劑,分2次水煎服,特別囑咐少食辛辣刺激、肥甘厚味之品,且應多食水果以適初秋溫燥之性。1周后復診癥狀明顯好轉,頭痛鼻塞減輕,有白黏涕,嗅覺無明顯異常,視涕量與質酌減魚腥草、蒲公英、石膏、車前子,加陳皮6 g,枳殼6 g。經1月余42劑中藥治療,病情控制可,3月后隨訪,膿涕、鼻塞、頭痛及嗅覺減退未有復發。
按語:患兒為年幼體弱受涼,素有鼻-鼻竇炎潛在疾病,感冒誘發未予重視,延誤病情,遷延日久,平素不知節制飲食,恰逢夏季炎熱天氣,終致慢性鼻-鼻竇炎反復發作,證屬肺經蘊熱,治宜清熱化濁,通竅止痛,方用蒼耳子散加減。方中蒼耳子、辛夷宣肺通竅,為鼻部疾病之經典藥對;白芷、蔓荊子、藁本、川芎分別止陽明經、少陽經頭痛,又川芎引藥上行,多管齊下以止頭痛;肺經蘊熱日久,鼻涕黃濁黏稠,非石膏、桑白皮之寒涼入肺經不能下熱,非蒲公英、魚腥草、桔梗祛瘀排膿不能消涕;澤瀉、車前子清熱利濕,以消小便之黃濁、鼻涕之黃稠;焦山楂、神曲既健脾消食,又兼散結消濁涕之意。復診效不更方,黃膿涕漸消為白黏涕,則漸去祛瘀排膿之魚腥草、蒲公英及大辛大寒之石膏,加理氣健脾之陳皮、枳殼,以適病情發展,及飲食之囑托,皆為適小兒之體質、顧小兒之脾胃,1月余而愈,隨訪未復發亦是情理之中。
5 小 結
張師認為,鼻竇炎的中醫治療萬變亦有宗,即離不開中醫基礎理論思想如辨證論治、經絡辨證、從火論治、分期論治、從臟腑論治等思想的指導,離不開中醫特色療法,如辨證論治基礎上中藥的加減、引經藥的運用與針灸方式的多樣性和創新性運用。醫師臨床時當多總結前人經驗,尋找創新突破口,從而發揚繼承中醫治療鼻竇炎的特色與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