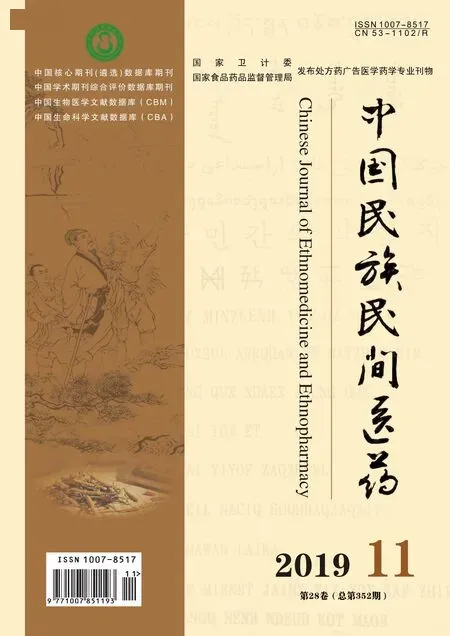從肝陽虛論治功能性消化不良
楊 陽1 顧 勤2
1.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2.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 指包括由胃、十二指腸功能紊亂引起的一系列功能性胃病,癥狀主要包括早飽感、上腹飽脹、上腹灼熱感及上腹痛等,經檢查排除引起這些癥狀的器質性疾病的一組臨床綜合征。臨床根據其側重不同,又分為餐后不適綜合癥和上腹痛綜合癥兩型[1-2]。我國流行病學調查發現,FD患者占消化科門診患者50%左右,具有病程長、易反復的特點[3]。祖國傳統醫學里并沒有關于FD的病名記載,但根據其臨床表現,可將其歸為中醫“胃痞”、“胃痛”等范疇。目前FD在中醫范疇內的的病名、證型尚不統一,《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2017)》將FD分為:脾虛氣滯型、肝胃不和型、脾胃濕熱型、脾胃虛寒型、寒熱錯雜型等5型[4]。病機上認為FD發病以脾胃功能失調,升降失司,胃氣壅塞所致[5]。治療上,結合中醫辨證分型選方,療效肯定。但臨床上仍有少數患者病程較長,經上述方法治療后,效果不顯著。此時從肝陽虛著手辨治功能性消化不良可取得較好臨床療效,現將筆者跟隨顧勤教授學習期間所得相關臨床經驗總結如下。
1 肝陽虛之理論探析
肝陽虛在現代中醫學教材中少有提及,缺少對其詳細論述。但查閱歷代文獻不難發現有關肝陽虛的相關記載,如華佗在《中藏經》提出:“肝虛冷,則脅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熱如瘧狀,不欲食。婦人則月水不來而氣急,其脈左關上沉而弱者是也。”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藥方》中說:“左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厥陰經也,病苦脅下堅、寒熱,腹滿、不欲飲食,腹脹悒悒不樂,婦人月經不利,腰腹痛,名曰肝虛寒也。”提出肝虛寒及其臨床癥狀。張景岳亦云:“或拘攣痛痹者,以木臟之陽虛,不能營筋也”,指出肝陽虛之象。近代名醫秦伯未在其《謙齋醫學講稿》中說:“懈怠、憂郁、膽怯、頭痛、麻木、四肢不溫等,便是肝陽虛的證候。”側面論述了肝陽虛及其癥狀。《蒲輔周醫案》中亦曾提過“筋無力,惡風,善驚惕,囊冷,陰濕,不欲食”等肝陽虛的表現,可見近現代醫家亦開始重視到肝陽虛這一病機。而從臟象及陰陽學說來看,“萬物抱陰負陽”、“無陰則陽無以化,無陽則陰無以生。”五臟皆有氣血陰陽,肝臟亦不例外。無論是從醫家古籍或是中醫基礎上來說,肝陽虛都是不可否認的。雖然在臨床上較少見,但仍不可忽視。而在肝陽虛的病因病機方面,顧勤教授在多年的臨床實踐中,歸納總結了以下三點:情志傷陽,平素多憂思謀慮,或性情急躁等,致氣機不暢[6],肝陽不展,日久而成陽虛之象;陰損及陽,肝陰虛日久,無以化生肝陽;五臟之陽氣皆來源于腎,腎陽虛的患者,日久不愈,累及肝陽。
2 肝陽虛是FD不可或缺的病機
肝主疏泄,調暢情志;脾主運化,主升清;胃主受納,主降濁。肝之疏泄有度,則氣機調暢,助脾胃發揮升降樞紐的作用[7]。如《醫碥·五臟生克說》云:“木能疏土而脾滯以行”。
現代的中醫教材大都認為肝之陰血充足,濡養肝體,肝性條達,則肝臟發揮正常的升發、疏泄功能。卻因對肝陽的不重視,而忽視了肝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顧勤教授認為,如果把肝比作樹木,則土壤及雨水為“體陰”,而樹木的生長、升發則是“用陽”。雨水充足樹木才能茁壯成長,但是卻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認識,即陽光所發揮的作用。如果缺少陽光,缺少溫暖,即使有雨水土壤,樹木也不可能成長的,而這個陽光就是“肝陽”。肝木的升發、條達、舒暢之性有賴于肝之陽氣的主導。正如宋鷺冰教授所言: “肝主疏泄,亦有賴陽氣之溫煦。”肝陰得肝陽的溫煦才不會損傷,肝臟只有得到肝陽的溫養,才能正常的疏泄,肝的功能才能正常[8]。可見在肝的正常生理功能中,肝陽是必不可少的。
若各種病因引起肝陽虛,均可導致肝失條達,疏泄失常,脾胃升降失調,發為痞證。正如清代名醫唐容川在《血證論》中所云:“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之證在所不免。”如素體陽虛,或大病傷陽,或過用寒冷之品等,均會出現陽虛的病理改變。肝陽虧虛,溫煦無力,虛寒內生,陰血不能濡養肝體,引起肝失條達,疏泄失常,氣機不利,影響胃之和降,從而引起病變。
3 肝陽虛型FD的臨床表現
肝陽虛型FD臨床表現包含肝陽虛和痞滿兩方面,其中痞滿以胃脘痞塞滿悶不舒為主。而肝陽虛則包含陽虛及由此所引起的肝失疏泄等兩方面表現,如神倦懶言、乏力、肢冷畏寒、小便清長等陽虛的表現;情志抑郁,太息,兩脅脹滿不舒,或伴脹痛、刺痛,胸腹痞悶不適,嘔惡等肝失疏泄表現。臨床上結合患者以胃脘滿悶不舒為主要癥狀者,不難診斷FD。但深究其病機時,往往難以明確病機。如無論是肝陽虛亦或肝陰虛,均會出現一系列肝失疏泄的癥狀,兩者難以區別,可以說是“本異標同”。陽虛癥狀有時又難以與痞滿伴腎陽虛者鑒別[9]。
總而言之,肝陽虛型FD的臨床表現,目前尚無醫家對其進行詳盡的論述,無統一的診斷標準。顧勤教授結合臨床總結其相關癥狀,如胃脘部痞塞不舒、不思飲食、嘔惡、納呆、或伴兩脅不適、優柔寡斷、精神疲憊、抑郁、善悲易恐、少氣懶言、畏寒肢冷、舌淡、苔薄白、脈沉弱無力等。
在辨證肝陽虛型FD時,對于陽虛較甚的患者,易與痞滿伴有腰膝酸軟、小便清長、畏寒等腎陽虛表現者相混淆。而對于以痞滿不舒為主的患者,伴有兩脅不適、或脹或痛、嘔惡納呆等,容易誤認為肝氣郁結證。顧勤教授在辨證中,尤其重視肝陽虛時的情志方面獨特表現,如情緒低沉、郁郁寡歡、少言寡語、表情淡漠等,認為其對于肝陽虛型FD的診斷有很大的幫助。同時結合經脈辨證,認為肝陽虛型FD,除了有胃脘痞滿不舒外,尚有頭部昏沉,或小腹拘急疼痛、疝氣痛,或少腹及大腿內側、陰部等冷痛,睪丸冷痛等厥陰虛寒之象。
4 從肝陽虛論治FD的臨床經驗
對于肝陽虛型FD,治療原則總以溫陽暖肝為主,輔以理氣消痞,同時兼顧陰陽,標本同治。在補肝陽時,顧勤教授針對肝陽虛的病機特點,提出了以下三點:①結合肝體陰用陽的特點,在運用溫藥時,兼顧肝陰易損易虛,肝陽易動易亢的特性。用藥多選肉桂、巴戟天、仙靈脾、小茴香、烏藥等性溫潤之品;②腎主一身之陽,腎陽虛者,常累及肝陽;肝腎同源,肝陽虛日久,亦會導致腎陽虛,認為肝腎陽虛多并見,故選用溫補之藥時,多主入肝腎二經,以期肝腎并補;正如《醫宗必讀·乙癸同源論》所謂“補腎即所以補肝”,藥用如溫補藥中之淫羊藿、巴戟天、肉蓯蓉、杜仲等;③溫陽同時不忘護陰,張景岳認為“陰根于陽,陽根于陰”,指出“善補陽者,必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10]故而在溫陽時,常輔以酸甘滋陰之品,陰中求陽,陰陽并補。尚能防辛溫傷陰之弊,起到柔肝的作用,以顧肝體,藥用熟地、當歸、白芍、烏梅、枸杞子、沙苑子、山萸肉等。
氣虛是陽虛之始,陽虛為氣虛之漸,故而在補肝陽時,應酌情配伍補肝氣之品,以舒暢氣機。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提出:“肝屬木而應春令,其氣溫而性喜條達,黃芪之性溫而上升,以之補肝,原有同氣相求之妙用。”[11]朱良春在《朱良春用藥經驗集》中說: “肝陽肝氣為用,肝陰肝血雖多不足之證,肝陽,肝氣亦有用怯之時……肝陽虛可用附子合桂枝、黃芪。”[12]顧勤教授亦認為,臨床無論是補肝陽或是滋肝陰等,旨在于復肝之升發條達。陽虛患者,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氣虛。應用黃芪可補肝升發之氣,以助肝陽。顧勤教授臨床每遇肝陽虛者,皆投以炙黃芪,取效甚佳。
FD的病機總以脾胃功能失調,升降失司,胃氣壅塞所致。故在溫陽暖肝同時,不忘理氣消痞,標本同治,考慮肝陽虛因素的存在。故所用理氣之品性多平和,常用有香附、蘇梗、佛手、香櫞、綠梅花、枳殼等。
5 典型病案
張某,男,42歲,2018年1日16號就診,主訴:胃脘脹滿5年余。患者5年前因飲食不節,出現胃脘部脹滿不適,每于飲食后加重,平素自服健胃消食片及嗎丁啉等,癥狀時有反復。后漸至納呆、食欲差,為之所苦惱,情緒不寧。情志波動時,諸癥加重。本次入冬后,癥狀加重,痞滿較甚,稍食則脹,納呆,四肢冷且畏寒,兩脅不適,少腹怕冷,倦怠乏力,神情憂郁,情緒低落,面色微青,胸悶嘆息等,舌淡,苔薄白,脈弦弱。曾予溫補脾胃、疏肝理氣等法,效果不甚。胃鏡示未見明顯異常;肝膽胰脾彩超未見異常。西醫診斷: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診斷:痞滿(肝陽虧虛型)。擬溫補肝陽、和胃消痞之法,方用溫肝湯加減。藥用:黃芪30 g,肉桂6 g,淫羊藿10 g,巴戟天10 g,山茱萸10 g,當歸10 g,香附10 g,白芍10 g,陳皮6 g,白術15 g,枳殼 10 g,合歡花10 g,炮姜6 g,茯苓15 g,黨參15 g,甘草3 g。
二診:諸癥較前緩解,胃納漸復,面色紅潤,情緒好轉,但覺腰膝酸冷,兩脅不適,繼守原方,并予腎氣丸口服。后隨訪患者,胃痞漸消,食欲可,情志暢達,四肢溫,語氣有力,囑原方續服。
按語:患者為胃脘痞滿所苦,相關輔助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西醫診斷為功能性消化不良,可歸屬于中醫“痞滿”范疇。四診合參,一派陽虛之象,且情志波動時,癥狀亦有加重,故考慮為肝氣郁結之象。然前醫投以疏肝理氣,溫補中焦之品,未見效果。故此例并非單純脾胃陽虛、肝氣郁結之證。細究其癥,除胃脘痞滿外,尚有神情憂郁、情緒低落、面色青等表現,故考慮其可能因肝陽不足所致。肝陽虛衰,肝失條達,疏泄失常,導致脾胃升降失調,發為FD。故試投以溫補肝陽之品,方中重用黃芪以復肝條達升發之氣。肉桂、淫羊藿、巴戟天等性較平和之品,補肝陽之虛。配以當歸、山茱萸、白芍等顧護肝體,以求陰陽并補。以香附、枳殼、合歡花等疏理肝氣,條暢氣機。木不疏土,脾失健運,故入白術、茯苓、黨參等健脾益氣。同時服用腎氣丸,以求肝腎并補。全方共奏,溫補肝陽,理氣消痞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