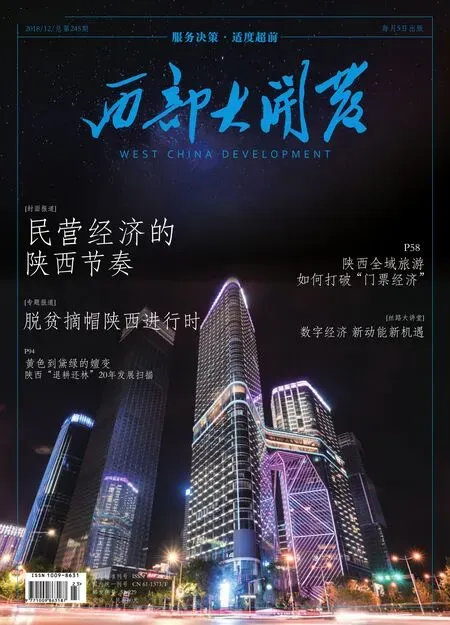翰墨猶在 風骨猶存
——陜西書法家王定成應邀王義之、柳公權故里題字紀略
文 / 張念貽
書畫
作為書家題碑題牌題匾,并不算作新鮮事,但能夠應王羲之、柳公權故里之邀題字,并被勒木刻石,高懸在書圣塑像的兩側,安放于人跡繁華的所在,這是多大的禮遇,又是何等的榮耀?似乎可以說是“書法到家,書家到家”了。
對于書法家王定成先生來說這兩次“具有標志性”的題字,卻是在表達著多年來對王右軍、柳河東的“心慕手追”,更是接受社會的批評和檢閱。甲申年秋,他為浙江嵊州王羲之故里大華堂抱柱撰聯并題寫:秉真行之要逸少法書醉天下,執隸草其權子敬妙跡希世間。甲午年春,他又為陜西耀州區柳公權故里題寫:關莊柳公權社區;公權公用。
“雄渾、飄逸”是定成先生的書法給人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印象,他的筆墨情懷與審美趣識始終以清正的書風,顯示著他對中國書法傳統的虔誠與敬重。無論是王羲之故里所題,還是柳公權故里所寫,從不豪言豪語的王定成先生,不僅寫出了如此好聯好語,更是將豪壯豪邁盡付筆端。
人品書品皆在品,書道人道皆在道,文脈書脈皆在脈。在談及王羲之、柳公權對自己的影響時,定成先生坦言,古今書家書品多有悲壯悲憤之作,右軍書作,柳公法帖之所以光耀后世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書品人品、書道人道的同等標高。蘭亭集序中天地死生之大矣彰顯的是大情懷,因此成就了千古美文,柳公一生為官,心正、身正,筆正,因此才有了備受推崇的千古名帖。至于說文脈書脈,何以為脈?—風骨為脈!




王定成,與共和國同齡,出生于陜西省平利縣。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研習書法六十余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原陜西省書法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翰墨傳承,風骨延續的書法文化復興,是他書法愛好的最大夢想。在北京、成都、西安、洛陽等近百處風景名勝、文化經典之地,留存有其墨跡石刻、牌匾、對聯等。

“翰墨猶在,風骨猶存”,這是王定成先生對千百年來文脈書脈的感悟,但也同時道出了他對清正書風的追求。書有風骨,人亦有風骨。書界人皆聲稱風追“二王”,但是真正融入“二王”風骨的人卻少之又少。許多時候,創新以破壞的方式取代了切合時代,切合民心的審美追求;許多書家,自我標榜自以為是追求“變態”之美;許多評論,人云亦云胡吹亂捧能夠幾個敬由心生?由此亂象之下,再來看王定成先生書法所收獲的美譽和禮遇,是有著必然的道理。
甲午馬年的初春里,于定成先生朗潤軒中,聽先生論道,觀先生書作,既有看萬馬奔騰之雄渾豪邁,又感覺如春風撫柳般的俊秀飄遮。現場觀摩先生揮墨,“二王”秀美之中融入魏碑之剛勁,點線轉折中有板有眼,有靈有性。正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令人如沐春風,心旌搖蕩,齋號以“朗潤”二字命名,再貼切不過。再思定成先生所言“翰墨猶在,風骨猶存”,有風骨在,風清氣正,明朗乾坤,潤物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