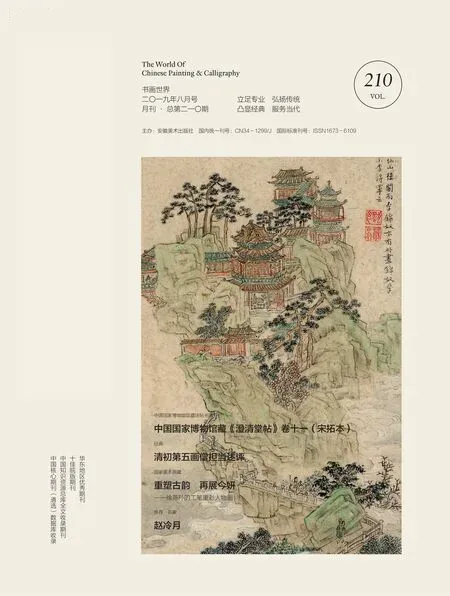“造型之為造”—論蔣兆和水墨人物畫造型語言
文_劉含倩
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內容提要:“造型之為造”是傳統人物畫的一個重要思想,其產生一方面是由畫家自身的性質和歷史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時代的文化環境。造型是中國畫重要的表現語言和手段,是人物畫的核心問題。中國畫造型藝術的最大特點:它是對客觀物象外形的描寫以及精神的刻畫,最重要的是以簡練的線條來呈現的。畫家是通過對客觀物體的主觀表達進而創造出自己的造型風格,即蔣兆和所言畫“專業素描”運用線的造型,要在白紙上表現體積和能動性,因此造型是解決水墨人物畫的第一步。
造型,創造形象之型式也,故“美術”亦曰“造型藝術”。畫之形象必可視、可想,方可謂藝術之詩意形象。可視以通真,可想以通情。自然形象為本,藝術形象為變。自然形象為具體,藝術形象為典型。近現代人蔣兆和曾闡釋說:“學習西畫不是為了造型而造型,更深層次的是為了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造型不僅是形體的造型,更是精神的造型。”繪畫史上持相同論斷的人還有徐悲鴻、黃胄、傅抱石、范曾等人。蔣兆和所說的“形體造型”“精神造型”,正可以對應中國畫學中的“寫形”與“傳神”,即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線條在中國繪畫中起到強化氣勢、表達心意、傳達信息的作用,重點是用精煉的線條去追求主觀心境和意境。遠在一千五百余年前,東晉時代的顧愷之對人物造型方面已提出過“以形寫神”的論點,即要達到“神形兼備”的最高目的。蔣兆和先生在水墨人物畫衣紋的處理上,多用短而頓挫的線條去表現衣服上的褶皺,其以長線條定外形,并以粗線確定外形輪廓,以短線條勾畫人物形體的一些細節。蔣兆和融合了西畫造型之長和山水畫的皴、擦、點、染技法,畫風質樸穩重,筆墨精湛嫻熟,有體積感,人物形象生動真實。在豐富中國水墨人物畫的表現手法方面,他突破了傳統以形寫神的表現。他所開創的人物畫新面貌在造型藝術上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人物整體造型的歸納呈現出形的雕塑感,二是對對象進行了“盡精刻微”、形神兼備的描繪。劉驍純先生曾指出,蔣兆和的水墨人物畫是“精微寫實和疏放用筆兩極結合的探索方位”從西畫的引入向轉化的過渡。
蔣兆和造型語言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追求有規則、有準則的美,也就是說遵循傳統骨法用筆原則,要求下筆追求準確肯定。首先就要做到認識客觀形象構成原因;其次要繼承傳統造型的創作技術及經驗,只有這樣才可以在實踐中鍛煉眼睛和手的操作能力,眼睛和手的關系關鍵在于感性知識提升到理性知識層面,由此才能算是得心應手。所謂“中得心源”,指的就是思想感情的來源主要是借助眼睛的認識深入形象精神的根本,由此才形成畫家自身真正的感受。這種感受,已經是畫家通過客觀物象獲得的主觀判斷和肯定,因而才能“得心應手”。該階段要通過國畫白描打下堅實的現代寫實的造型基礎,在此階段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木炭。
第二階段要“盡精刻微”之造,即要達到“應物象形”的目的。由于第一階段有了一定的造型準則,第二階段就必須進一步刻畫人物的精神特征。根據顧愷之的傳神論點,著重于“形神兼備”的描寫。形與神的關系是互相依存,但兩者之間又不是無所區別的。因形似還不等于神似,所以這里所指的形似即是“應物”。只有認清構成形象的規律,即“骨法”,才能有條件“象形”,畫出形象的精神特征,即是要“以形寫神”。但是在實踐中如何才能做到形神兼備呢?這就必須要盡精刻微,即對構成形象的主要部分,必須畫得精確。而主要部分中的微妙變化,特別要著重刻畫,加以提煉、取舍、夸張、突出。因為形象的精神本質,不僅是寓于形象的特征中,而往往是在特征中的細微變化,甚至是一瞬間的變化。要善于抓住變化,并且在“盡精”的基礎上從微觀上追求藝術的美感,由此惟妙惟肖地展現出事物。徐悲鴻先生曾經說過,惟妙惟肖中的“妙”指的是美、“肖”屬于藝術,由此在實際畫畫中要憑借寫實做到“惟肖”。等到繪畫技術嫻熟后,即便是不憑借寫實,下筆畫畫時不會產生違和感,“易以渾和生動逸雅之神致而構成造化。但偶然一現之新景象,乃至‘惟妙’,然肖或不妙,未有‘妙’而不‘肖’者也”。這就是說,只有抓住微妙的變化,才能“傳神”。所以在這一階段里必須發揮造型的精確能力,否則不可能貫徹中國畫造型藝術的基本訓練。至于表現形式,基本上是白描的形式,工具是用毛筆。
第三階段著重筆墨的運用,也就是說注重接受傳統技法在寫生中發揮其自身創造性的運用。“六法”中的“隨類賦彩”就是指物象自身具備的質感及色澤,必須隨著不同物類、性別、質別使用筆墨,包括顏色的運用,以更好地完成形象化過程中精神的塑造。由此,我們需要采取多樣的表現形式及表現技法,比如水墨以及重著色等形式及各種不同的勾、皴、點、染的傳統技法,在白描造型基礎上采用多種不同形式的技法。
結論:上述三個階段,雖然說各有重點,但不是互相脫節,自始至終都要貫徹“白描”作為造型的基礎。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因為如果水墨人物畫創作沒有堅實的“白描”基礎,一切造型都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