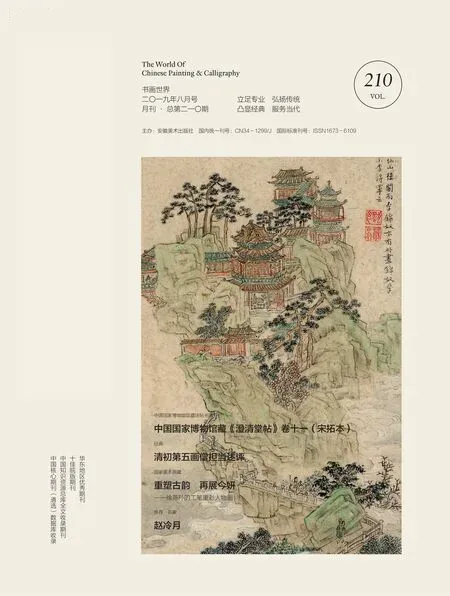《今古奇觀》與《喻世明言》版畫插圖比較研究
文_張媛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
內容提要:《今古奇觀》共四十卷,其中有六篇內容來自《喻世明言》。本文通過對寶翰樓刊本《今古奇觀》與衍慶堂刊本《喻世明言》中圖文對應關系的分析,探究相同文本、不同版本版畫插圖的區別,探討版畫插圖的藝術特征及圖文關系。
《今古奇觀》是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選集,明抱甕老人編,主要選自馮夢龍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共四十卷,其中有六篇內容來自《喻世明言》,分別是“滕大尹鬼斷家私”“裴晉公義還原配”“吳保安棄家贖友”“羊角哀舍命全交”“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以下就二者的版畫插圖來進行探討。
一、文本與插圖的關系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今古奇觀》為明末吳郡寶翰樓刊本(以下簡稱《今古奇觀》),四十卷,其中有版畫插圖八十幅,月光型;《喻世明言》為明末衍慶堂刊本(以下簡稱《喻世明言》),二十四卷,其中有版畫插圖四十八幅,單頁整版式。兩書中共有六篇內容相同,每一篇都各自有兩幅版畫插圖,具體如下。
1.滕大尹鬼斷家私
“滕大尹鬼斷家私”出現在《今古奇觀》第三卷和《喻世明言》第三卷,講述明朝永樂年間年太守倪守謙家庭內部財產紛爭,以及滕大尹裝神弄鬼斷家私并攫取余銀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倪守謙遇梅女子的情節,《今古奇觀》中插圖人物、背景刻畫更加準確、生動。在第二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滕大尹觀看《行樂圖》,失手弄濕畫軸并發現畫軸中的秘密的情節。《今古奇觀》中插圖人物動態準確、生動,完全符合原文描述;而《喻世明言》中《行樂圖》被掛在墻上,不可能被弄濕,插圖內容與原文相悖。
2.裴晉公義還原配
“裴晉公義還原配”出現在《今古奇觀》第四卷和《喻世明言》第十三卷,講述的是唐朝裴度立下平叛奇功,還朝拜相,當地刺史把唐璧未婚妻黃小娥獻給裴度,裴度得知真相后將黃小娥還給唐璧并為其主婚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唐璧遇難的情節。在《今古奇觀》中,唐璧動作幅度更大,動態、表情也更加準確、到位。在第二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裴度還妻的情節。《今古奇觀》中插圖人物呼應關系、主次安排更加準確、到位。
3.吳保安棄家贖友
“吳保安棄家贖友”出現在《今古奇觀》第十一卷和《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講述的是吳保安花費十年時間外出做生意,以便籌得絹布而救贖郭仲翔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郭仲翔負骨歸葬保安夫婦的情節,人物動態準確到位,表情堅毅、生動。在第二幅插圖中,《今古奇觀》選擇了保安贖友的場景,而《喻世明言》選擇了楊安居見吳保安的場景。相較之下,《今古奇觀》所選取的場景更能體現故事的重要內容和精彩瞬間。
4.羊角哀舍命全交
“羊角哀舍命全交”出現在《今古奇觀》第十二卷和《喻世明言》第十二卷,講述的是西漢左伯桃與羊角哀結伴求見楚元王,途中遇到大雪,左伯桃為了成全朋友犧牲自己,后羊角哀受到楚王重用回來厚葬左伯桃,并自刎去幫助左伯桃對抗荊軻鬼魂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左伯桃為友脫衣并糧的情節。在第二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羊角哀拔劍自刎的場景,人物刻畫準確、生動,但在場景處理上《今古奇觀》更勝一籌。
5.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出現在《今古奇觀》第二十三卷和《喻世明言》第四卷,講述的是襄陽商人蔣興哥的妻子王三巧幾經輾轉、后來破鏡重圓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兩書都選擇了王三巧初見陳大郎的場景。在第二幅插圖中,《今古奇觀》選擇的是蔣興哥辭別陳大郎、重見珍珠衫的場景,《喻世明言》選擇的是蔣興哥與王三巧再相見的場景。
6.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出現在《今古奇觀》第二十四卷和《喻世明言》第二卷,講述的是魯學曾和顧阿秀自小“面約為婚”,后顧阿秀因事自縊,魯學曾身陷囹圄,陳御史徹查案件,魯學曾沉冤得雪,幾經輾轉,娶表哥前妻為妻的故事。
在第一幅插圖中,《今古奇觀》選擇的是假公子“應邀”前來相會顧阿秀的場景,而《喻世明言》則選取了管家婆給假公子引路的場景。在第二幅插圖中,《今古奇觀》選取了陳御史審案的場景,而《喻世明言》選取的是梁尚賓買布的場景。
六個故事中,盡管所選情節有些區別,但兩書中的版畫插圖都盡力表現原文內容,在畫面刻畫手法及藝術特色上也有一定的區別。
二、版畫插圖的藝術特色
版畫插圖版式的區別:《今古奇觀》中有插圖八十幅,月光型版式。周心慧在《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中說:“晚明時期蘇州率先流行所謂‘月光式’版式,圖版外方內圓,是對中國古版畫版式的一大創新。其形如鏡取影,畫面雖小,卻雋秀典雅。”這種“如鏡取景”的插圖形式是整版式插圖的變形,帶來畫面集中的效果。《喻世明言》中有版畫插圖四十八幅,單頁整版式。“圖繪占滿書頁,一面書頁即是一幅完整的畫面,這種插圖的獨立性較高,具有單獨欣賞的價值。”[1]由于插圖在卷首與正文分離,插圖所需要表達的信息量也隨之增加,插圖自身的獨立性、表現性、完整性使得畫面中情節的復合再現,畫面構圖多層次化,并增加圖目和贊語,增加了插圖的內涵和意境。
構圖形式的區別:《今古奇觀》和《喻世明言》都以景物為中心、人物小型化的構圖方式處理畫面布局,除了畫幅形式的不同,兩者在畫面布局及處理上也有較大區別。《今古奇觀》版畫插圖特別注意畫面的疏密、聚散關系,有一定的節奏感,主次分明;《喻世明言》則是平鋪直敘,缺乏審美考慮和藝術處理。如在《今古奇觀》中,“裴度還妻”的場景構圖均衡飽滿,人物安排疏密有致,被簇擁的黃小娥、拈須微笑的裴晉公、慌亂又驚喜的唐璧相互呼應,共同構成畫面焦點,可讀性強,耐人尋味;在《喻世明言》中,整體布局左重右輕,黃小娥被淹沒在侍女群里,裴晉公則被過度“放大”而顯得孤立,唐璧則被“邊緣化”,畫面中各部分缺乏呼應。
人物造型的區別:在《今古奇觀》版畫插圖中,人物線條流暢、動作準確,人物之間動態呼應關系較好,主次分明,主要人物的表情刻畫生動,服飾紋樣細致。如“裴度還妻”的場景中,鳳冠霞帔的黃小娥被一隊侍女簇擁著,格外突出,侍女們服飾簡單概括,動作準確,前呼后擁,主次分明。裴晉公作為畫面主角之一,除了動作、表情準確,對其帽冠、衣服紋飾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刻畫,突出其主要地位。在《喻世明言》版畫插圖中,人物線條流暢,但動作雷同,人物之間的呼應性差,主要人物的細節處理簡單。在“裴度還妻”的場景中,侍女們的表情、提燈侍女的動作等都過于雷同,對主角黃小娥、裴晉公的服飾也沒有更多的細節刻畫。人物之間的呼應關系、疏密關系、節奏關系考慮得較少,畫面效果也不如《今古奇觀》中的精彩和生動。
場景塑造的區別:在《今古奇觀》版畫插圖中,場景刻畫細致、到位,不管是建筑、山石、江河、植物等室外場景還是屏風、家具、器皿等室內陳設都一一交代,烘托出故事背景。在《喻世明言》版畫插圖中,場景處理過于簡單,虛實、疏密關系欠推敲。如在“裴度還妻”的場景中,《今古奇觀》中版畫插圖對花燈、帷幔、燭臺、屏風等的處理無不仔細推敲、細致描繪,對裴晉公身后的屏風也進行了細致描繪,而起伏的群山、廣闊的水面、精巧的樓閣及湖中的扁舟等,既豐富了畫面內容,使畫面均衡,又通過山水烘托出裴晉公寬廣的胸襟和助人為樂的精神。在《喻世明言》中,屏風只勾勒了輪廓,帷幔和花燈刻畫程式化,畫面下方的欄桿刻畫過于瑣碎反而影響了畫面整體疏密布局。在“羊角哀舍命全交”場景中,《今古奇觀》的描繪可謂細致深入:左伯桃的墓地周圍有一片松樹林,有墓碑,并題寫碑文“中大夫左伯桃之墓”,周圍還有兩座華表,墓前有一供桌,桌上擺滿酒菜,桌下還有香案,案上有點燃的香燭等,在畫面左上角還有建筑屋頂,正是文中提到的“享堂”,等等。如此細節在《喻世明言》版畫插圖中則并無交代。
三、《今古奇觀》與《喻世明言》的圖文關系分析
在比較版畫插圖與小說文本的關系、版畫插圖藝術特色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對其“語-圖”互文的現象進行分析,挖掘和探討兩書的圖文關系。
1.因文生圖
有的研究者“把‘圖源于文’‘因文生圖’視為明清小說版畫插圖‘語-圖’互文的第一個層面”[2]。所謂因文生圖,簡單地說,就是“用圖畫來表現文字所已經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3],使“文”具象化、直觀化。“中國古代小說插圖同樣如此,在圖像生成機制上,首先受到的是語言文本的影響,圖像形象地再現了語言文本的情景描述,或抓住關鍵情節進行瞬間定格,因而‘圖與文合’是圖文結合最常見的現象。”[4]
《今古奇觀》和《喻世明言》的版畫插圖也不例外,“因文生圖”是其圖文關系中最常見、最主要的類型。從前文“文本與插圖的關系”分析中可以看出,兩書中的插圖雖然構圖布局、選取場景、表現手法等因素有所區別,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圖與文合,較準確地體現文本內容。
2.圖異于文
除了“因文生圖”的插圖之外,圖異于文是兩書“語-圖”互文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這里所指的“圖異于文”既非圖文相左,亦非下文將論述到的“圖溢于文”,而是指“插圖在表現小說故事情節時,在環境創設、人物配備、動作刻畫等方面出現與小說文本內容不相匹配的現象”[5]。
《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斷家私”中滕大尹觀看《行樂圖》場景中的人物動作,“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王三巧初見陳大郎時的王三巧的動作等都與原文有出入。因前文已述,此處不再贅述。
3.圖溢于文
在準確表現文本內容的同時,突破文字限制,加入畫家情感,讓插圖更加生動、感人。如在《今古奇觀》“羊角哀舍命全交”中,畫面中除了描繪文中提到的墓地、松柏、華表、享堂等外,作者還在墓前添加了供桌,桌上擺滿酒菜,桌下還有香案,案上有點燃的香燭等,升華了羊角哀、左伯桃之間的偉大友誼;在“裴晉公義還原配”中,裴晉公身后的屏風上繪制的山水圖卷烘托出裴晉公寬廣的胸襟和助人為樂的精神。《喻世明言》中的每幅插圖中都有文字,主要包括兩大類:圖名和贊語通過文字來渲染環境、升華主題,同時留給觀眾很大的遐想空間,也擴展了畫面的內容、意境。
四、結語
載寶翰樓刊本《今古奇觀》和衍慶堂刊本《喻世明言》相同的六個故事中,插圖的表現都是以景物為中心、人物小型化的構圖方式處理畫面布局,但畫面所呈現的效果則不盡相同,盡管都能準確傳達原文意思,但相較之下,《今古奇觀》中的版畫插圖更加注重畫面的細節刻畫,對背景處理以及人物動態的呼應關系、疏密關系、節奏關系的把握都更加考究和到位,給讀者一定的視覺美感。版畫插圖在準確表現文本內容,體現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等方面的潮流與特征的同時,也是對畫家基于現實或想象思維的一種印證,代表著創作者的思想意識,也是對當時社會民眾視覺沖擊力的一種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