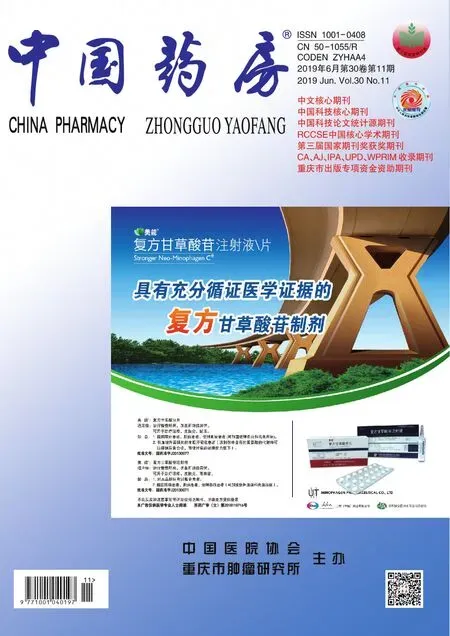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法律保護Δ
王艷翚,姚崢嶸(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經濟管理學院,南京210023)
在中醫藥領域,技術秘密是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概念,中醫藥技術秘密包含了技術知識、實踐操作和經驗等幾個層次[1],技術秘密一部分以藥物等載體形式呈現,表現為中藥配方和方劑的配伍,由于可以離開主體而獨立存在,這類信息屬于顯性知識,有條件與其他生產要素相結合而形成產業[2]。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技術秘密不能脫離個體單獨存在,而是必須依附于人身。這部分信息負載了鮮明的人格特征,因而構成了中醫藥隱性知識的一部分[3]。
在整個中醫藥體系中,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占據了一定的比重,因對主體的附著性較強,其存續以傳承人的承載為主,這就意味著這類技術容易隨著傳承者的變化而衰減甚至流失,因此法律對其實施的保護,應與已經產權化了的顯性中醫藥技術秘密有所區別。以此為起點,厘清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構成、類別及法律屬性,并在此基礎上尋求相應的保護方法,就成為完善該領域法律保護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就此進行探討,為法律對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予以保護的思路及運作提供參考。
1 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構成及類別
目前,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尚未從一個小范圍的局部擴展到整個中醫學共同體[4],相當一部分仍散落在民間。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應簡單地歸結為中醫的保守所致,隱性知識無法獲得知識產權法的有效保護才是主要原因:鑒于知識產權的客體需要具備如藥品、中藥制劑等外化的有形載體形式才能獲得法律保護,而隱性知識的人格依附性特征使其無法脫離人體實現客觀化,無法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財產”,因而不能滿足該條件。作為一種個性化的信息,中醫藥隱性知識無法從既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尋求保護方案,而更多的是以“技術訣竅”
“祖傳秘方”等形式呈現出來,主要涵蓋了中藥材炮制加工技術和中醫診療技術兩種類型。
1.1 中藥材炮制加工技術
炮制又稱修治、修事,是指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將中藥材加工成中藥飲片的方法和技術,涵蓋了浸、泡、鍛、煨、炒、制、蒸、煮等各類操作。中醫臨床所用中藥皆為經過加工和炮制而形成的飲片,對中藥材的炮制加工技術成為決定藥效有無和藥效高低的關鍵,中藥材炮制也逐漸成為我國獨有的一門學科。由于自然資源、用藥習慣、生活習俗、文化傳統甚至方言語音的不同,各地的炮制加工形成了不同的技術派別,影響較大的有北京的京幫、江西的樟幫和建昌幫,以及四川的川幫等。其中,“京幫”炮制的特點主要體現在炮制方法和輔料特色上,其代表性飲片包括百藥煎、七制香附;“樟幫”注重切制,對枳殼、臨江片的炮制廣受贊譽;“建昌幫”所用炮制工具和輔料獨特,著名的炮制飲片有姜半夏、明天麻等;“川幫”則多采用前店后坊的模式進行經營,其九制大黃、九轉南星等炮制品為業界稱贊[5]。
在中藥炮制技術中,一部分較為簡易的操作目前已被公開,這使得其不再被納入私權范疇,屬于人人可以共享的公有知識。還有一部分仍由特定人員掌握,尚未公開,這一部分多為某些特殊的中藥材處理工藝,帶有明顯的技術訣竅的特點。從實踐中看,盡管2015年版《中國藥典》(一部)及(四部)或地方標準中有關于中藥材炮制方法的描述,但不依靠技術人員的指導而僅靠閱讀文字,其操作技巧并不容易真正被掌握。在這個過程中,人成為中醫藥技術秘密的載體,缺乏了必要的人工指導,初學者通常難以炮制出質量上乘的飲片,正所謂“心中易了,指下難明”[6]。
1.2 中醫診療技術
在中醫藥技術體系中,方劑的組成、用法和功用等都是可以編碼的知識,因可以用語言、文字進行表達而比較容易傳播。但在這些顯性知識背后,還隱藏著更多的“隱性知識”[7],例如何時使用這些方劑?如何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進行藥味的加減?每味藥的劑量如何變化?等等都形成了行醫者對疾病的構象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到的就是中醫的診療技術。
中醫的診療包括三類信息的處理,一是通過望、聞、問、切采集的四診信息,二是根據中醫理論分析四診信息所判斷的證候或疾病,三是在診斷的基礎上給出治療方案[8]。診療是一個比較個體化的過程,包含了患者的個體化和行醫者的個體化兩個層次,對于同一病種的同一證候,不同患者的四診信息會因為體質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生命狀態的這種不完全能觀性[9],使行醫者對同一類疾病的構象不盡相同,這是一個隱性知識發揮作用的過程,對于這些技術信息,其傳習依賴主體之間的有效互動。
2 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法律屬性
2.1 技術秘密的人格依附性
一般認為,語言使用和工具制造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而技術則將其自身內化成為人的一部分,從“人的延伸”演變成為“人性的固有部分”[10]。技術的這一特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無法真正脫離人的主觀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中醫藥領域,透過對中藥隱性技術秘密的上述兩種類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該類信息具有明顯的人格依附特征,許多信息的運用往往與行醫者的行醫實踐融為一體,并與持有人(主要為行醫者)本人的經驗、技能等不可分離。
如同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遺產”,而應視作一種人的技能[11],隸屬于特定主體的人格一樣,帶有人格依附性的中醫藥信息并不屬于持有人真正的“財產”。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概念涉及的是可以與人身相分離的獨立客體。附著于人之上、依賴特定主體的實施才能呈現的中醫藥技術秘密,雖然同樣能夠為持有人帶來經濟收益,但并不具備財產的獨立特征。相反,中醫藥信息具有比較明顯的人格色彩,不能脫離持有人直接在市場上被交易。
2.2 技術信息的傳承性
不同于知識產權制度對個體私權利的張揚,中醫藥技術秘密的形成和發展往往由多人實踐并完成,這是一個知識不斷創造和累積的過程,這類信息因而帶有了一定程度的公開和共享的特點[12],其傳承表現為信息的從“人到人”的轉移。由于屬于隱性知識,這類信息難以用數字或公式來表達,也很難被編碼,其內容的轉移取決于傳承者與研習者之間的交流和意會的互動。
在這個過程中,人是知識和技術得以創造并轉移的內生力量,因而該過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雙方當事人,特別是其中的傳承者的主觀意志。傳承者對該技術信息的控制具有獨占性,除非本人愿意,否則技術就無法外傳。筆者認為,對這類中醫藥技術秘密而言,傳承究竟意在公開還是保密并非法律對其實施保護的根本目的,保持中醫藥的整體性和延續性、發揮其治病救人的功能并實現對公民健康的維護,才是法律保護中醫藥的最終目標。因此,法律對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保護,不僅在于對該類信息予以保密,防范其被他人侵犯,更重在保障相關知識和技術的傳承,以防止其滅失。
3 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法律保護方法探索
3.1 公法的介入和傳承機制的運用
3.1.1 對中醫藥傳承機制的保護 鑒于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群體性特征,公法和私法的保護在該領域都必不可少,其中公法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對中醫的傳承機制的保護。
在中醫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師徒傳承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需要依賴當事人的記憶及臨床的實踐方能掌握,而師承方式則提供了這種便利及條件,使學習者能夠盡早接觸中醫理論和實踐技術操作,這對于學習有著較高悟性要求的中醫知識十分必要。通過口傳心授,師者把個人對中醫的價值體系、理論和技術的把握以及臨床的操作技能傳授給學習者,后者通過抄方侍診了解和把握治病、用藥的方法,進而得以繼承老師的醫術[13]。這種師徒間的言傳身教帶有個人化和情景化的特征,其知識和技術的轉移通過個體之間的密切接觸和相互切磋得以實現。但與此同時,這種模式也帶有效率偏低、傳播范圍小的不足,在中醫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就因此被視作農耕時代的產物而一度遭到擯棄。
師徒傳承的教育方式在我國曾經一度受到指責,反對者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認為這種教學帶有較大的主觀性,缺少一個相對客觀化的語言環境,使得相關信息的傳遞容易失真。實際上對于此類人格色彩濃厚的中醫藥技術秘密,其內容的傳播正是高度個人化的,師承師法,自拜師開始就決定了學習者的學習內容、研究特點和發展方向。中醫之所以學術流派眾多,師徒傳承的教育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隨著中醫傳承出現斷檔危機,傳統的師承培養模式重獲重視。師承模式重新回歸到中醫教育系統中并與院校教育相結合,在培養中醫人才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作用。雖然從傳播途徑上看,這種傳承模式遵循的是“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教育過程,中醫藥理論技術體系仍然是在師者與學習者之間通過意會思維分享的方式進行傳播,但是其在客觀上順應了這類技術信息傳遞的需要,于中醫藥的傳承和可持續不可或缺。
3.1.2 對中醫傳承人的保護 法律對中醫傳承機制的維護需要以承認并保護傳承人的合法地位為前提,這是完善傳承機制的關鍵舉措。中醫傳承人的范圍包括行醫者、中醫藥的秘方持有者等以個體身份活動的人,在當前西醫占據了統治地位的醫學領域,來自于現實與傳統的不同的角色期望,使這些中醫傳承人面臨著繼續保持中醫傳統抑或向西醫妥協的兩難[14]。但無論哪一種選擇,傳承人個人力量的薄弱,使其無力改變中醫當前所處的被動局面。因此在該領域有必要發揮公權力的統領作用,有意識地借助政府手段促進中醫藥傳承機制的良好運行。為此,我國把涉及隱性知識的中醫藥技術列入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中,嘗試借助公法的力量實施保護。
截至目前,在我國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國務院已經公布了5批傳統醫藥傳承人的名單,僅2018年就有58人被授予該稱號[15]。依照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政府對這些獲得“中醫傳承人”稱號的中醫執業人員,通過給予津貼或經濟資助[16],以改善其行醫條件。在這方面,圍繞中醫傳承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各有特色,法律的調整重點應做到有所區別,其重心應落實在為傳承創造良好的環境、制訂激勵政策、扶持并保障傳承人主動傳承的措施等方面,從而使其對延續和傳播這一類中醫藥技術信息的貢獻能夠獲得回報。
3.2 契約的保護和隱性知識的轉化
3.2.1 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顯性化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技術秘密,中醫藥隱性知識的傳承特點使得這類技術秘密不易被他人盜取,但這并不意味著該領域不存在被侵權的可能。尤其當牽涉到中藥企業的生產時,其外泄的風險會相應加大。現代化的中醫藥生產走的是集約化、規模化道路,不再以過去的小作坊為單位,這就意味著技術秘密權利人不得不將其秘密與企業內部成員分享。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以人為載體、需要由人加以掌握和運用的特性也使得人才流動的過程往往同時伴隨著信息的流失。由于隱性技術秘密不能在市場上被獨立交易,對其潛在的經濟收益可以通過對勞動力的交換來實現,企業由此可以借助勞動力市場,通過“挖人”而實現對所需信息的獲取,這成為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流失的重要原因。
為減少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流失的風險,實現其向顯性知識轉化是一種積極的思路。隨著現代化科技手段的應用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中醫藥隱性知識能夠實現向顯性知識轉化和分離,轉化后的顯性知識可以通過知識產權制度獲得保護。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明確了構建中醫藥傳統知識數據庫制度的思路。從一定意義上說,數據庫制度的建立意在統和、整理中醫藥技術信息,保護中醫傳承人,實現對中醫藥傳統知識的利益分享,這就需要持有人對中醫藥信息予以提供,實現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轉化。而這種轉化實際上受制于更多地主觀因素的影響,是否轉換和轉換多少,需要根據當事人的披露意愿、對該類技術的價值的認識、以及如何將這類信息準確表達和外化出來等因素來決定,因此有必要考慮設置相關激勵措施以促進這種轉化行為的實施[17]。相應地,要求相關人員簽署競業禁止協議和保密協議就成為必要的保護手段。
3.2.2 競業禁止協議和保密協議的簽署 競業禁止協議和保密協議屬于對技術秘密的契約式保護,其中競業禁止協議更偏重對威脅性侵害的預防。實踐中,掌握或知曉中醫藥隱性技術秘密的技術人員在離職后從事與該秘密信息相關的工作,是對技術秘密構成威脅性侵害的最主要情形,競業禁止協議的簽署就在于以事前預防的方式對這些潛在的侵權者的行為予以防范,降低侵權行為實施的概率[18]。
競業禁止協議的簽署需要明確涉密人員的范圍。如前所述,由于有些中醫藥技術信息存在與技術人員的個人技能和經驗相互滲透的情形,即便企業在自己擁有的技術秘密信息上劃定了界限,也難免因人員流動使該信息被帶離企業,因此在涉密人員范圍上不應局限于直接接觸技術秘密的人員,適當擴大競業禁止協議的主體范圍是一個相對有效的解決辦法。
除競業禁止協議外,為了保護技術秘密,中藥企業還需要與企業內部的技術研發、技術生產、技術管理人員等以及企業之外因經濟合作關系獲悉技術秘密的合作方分別簽訂保密協議,明確他們對因工作獲悉的中醫藥技術信息的不泄露義務。
作為對保守技術秘密的一種承諾,保密協議建立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合意的基礎上,其保密期限不限于雙方存在雇傭關系或合作關系的期間內,也可以輻射到義務人解除或這類關系消失之后。為將對企業技術秘密的侵犯的幾率降至最低,保密規范應盡量細致并有可操作性,保密協議應根據涉密人員的不同崗位或者與秘密信息接觸的程度的不同,在保密事項、保密范圍、保密措施及違約責任等方面分別做出約定。
4 結語
在中醫藥技術秘密中,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并存。其中法律對技術秘密中的顯性知識的保護,更多的是與專利制度相對比,在知識產權領域開展的[19];而對于隱性知識的技術秘密的保護,由于其不具備獲得知識產權法保護的客觀性條件,因而需要從其人格依附性特征出發,借助于對“人”的保護和管理而實現。在此基礎上,公法視野中對中醫藥隱性知識傳承機制的完善和私法領域中相關競業禁止和保密協議的確立及簽署,為該問題的解決拓展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