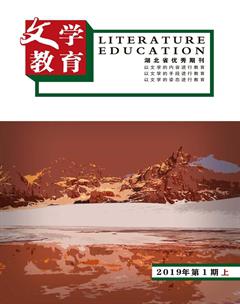在時間的縱深里,領受時代的開闊
卡西爾在《人論》中指出:“時間和空間是一切實在與之相關聯的構架。我們只有在空間和時間的條件下才能設想任何真實的事物。”這說明具有時空意識對于人類認識世界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對于一個不經常“穿越”的人而言,這種意識可能在感官本能上已經隔膜;而對于一個經常“穿越”的人而言,這種意識則會在心靈中逐漸滋長。
對比中西文化,我們發現,海洋文化沉淀出了西方人以空間型為主導的意識結構,農耕文化沉淀出了中國人以時間型為主導的意識結構。然而從楊克側重表現時空意識的詩篇中,我們卻并不能提煉出上述觀點。在他有關時空觀念的詩篇中,以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為主導的詩篇平分秋色,這反映出楊克的時空意識與傳統有了變化。在這些詩篇中,《夏時制》和《1999年12月31日23點59分59秒》以時間意識為主導,前者寫因人為的時間變動所帶來的空間移位或者錯亂,后者則以既是新舊年之交又是新舊世紀之交的一個特殊時間點來細節性地凸顯其對時空的精致打量。而《有關與無關》和《地球 蘋果的兩半》則以空間意識為主導,前者以時間軸中的某一時段為參照,力圖展現不同空間中所發生的世界大事;后者則以十分形象的比喻,將兩個空間進行既對立又統一的觀照,盡管有歷時性的敘述,但空間的意識占據了主導。楊克詩歌中時空意識及其觀念的變化,個中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客觀而言,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大背景導致了東西方不再是互相隔膜的世界,而科技的發展更是使遙遠的空間在短暫的時間中變得不成問題(參閱《地球 蘋果的兩半》);主觀而言,楊克的人生閱歷,使他在承繼以時間型為主導的文化意識結構的基礎上,又觸摸到了西方文化,具備了西方人的眼光,打開了全球性視野。其實,不論是以某個意識為主導的詩篇,還是意識互相合流的詩篇,楊克在其中都渾融了中西文化。他的這種時空觀念與卞之琳詩中的時空關系多注重古老的中國意識(渾融儒道)有所不同。
有研究者認為,對時空的體驗乃是人的內在生命覺醒的起點,同時也是藝術的起點。由于詩歌是人類藝術之一種,故而在詩歌中有意或無意地進行時空變換將使詩歌在內容和審美的形式上更加富于藝術性。中國的美學家向來喜歡探討藝術中的時間和空間問題,以期藉此來發掘中國藝術所特有的個性與精神品格,而藝術家也希望憑靠此一技巧來使自己的藝術形式及其所蘊含的意趣進一步深化。在中國古典詩詞的經典范例之中,杜甫和周邦彥在這方面的修為可謂已經登峰造極。楊克身為一位中國詩人,其詩歌藝術中應該說還是有無法抹去的“集體無意識”所留下來的“結構影子”。“所謂時空意識,不僅僅是指人們對時空的意識和把握,更是指一種以時間和空間思維特征為基礎的感知、體驗和思維的模式,它其實是一種生命感知形式,在文化傳統的基因里先驗地存在于我們生命中。”(參閱程明震著《心靈之維:中國藝術時空意識論》)楊克的《際會依然是中國》,從章法而言是一首較為繁復的詩。他的感知形式,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宋詞的集大成者周邦彥。周詞長于鋪敘,并且擅長“變直敘為曲敘,往往將順敘、倒敘、插敘錯綜結合,時空結構上體現為跳躍性的回環往復式結構,過去、現在、未來和我方、他方的時空場景交錯疊映,章法嚴密而結構繁復多變。……還善于增加并變化角度、層次。”(參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該詩以暴雨中朗讀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國詩》為背景,調動一切元素進行交錯穿插,詩歌的時空秩序一度回環。其時空序列之繁復,既體現在此詩本身與扎加耶夫斯基《中國詩》的層疊上,又體現在借助各種關聯意象將過去、現在、未來以及我方、他方的時空場景進行的交錯上。比如,現在場景中的“暴雨”讓人聯想到“宋朝的屋檐”;詩歌通過“我”的視角關聯起扎加耶夫斯基,并透過他的“藍眼睛/看到故國詩人行船在江面上”。同時,詩中更細節化的想象也將現實中的國際空間(克拉科夫)轉換到過去(宋代)的中國空間。詩的第三節也是一個富于戲劇性的結構,前半截通過想象將現在導向“未來”(扎加耶夫斯基的方向),同時以隱喻的方式將“未來”進行“味外化”處理。在最后,詩人仍意猶未盡,又將充滿彈性的藝術時空進行了一次伸縮。
楊克詩歌的時空意識糅合了古今中外,既豐沛又精致。他對詩歌的時空感相當敏銳,讓“在時間的縱深里/領受當下這個時代的開闊”變成了既定的事實。
趙目珍,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