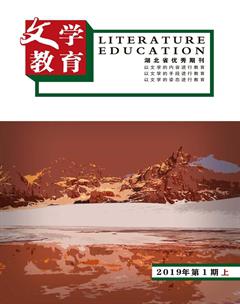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80后”的“一地雞毛”
“80后”作家孫睿曾以《草樣年華》(2004)而獲得文壇關注。對這一代作家來說,書寫青春的迷惑、痛苦、追尋、感情等體驗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甚至是構成這代成名甚早的作家幾乎唯一性的主題。數年過去后,當年的“80后”都已各有歸處。有的泯然于眾人,有的經營文化營生,有的成了資本運作者,有的依然在寫作。
《寶貝兒,帶我飛》是孫睿近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從名字即可看出,它與孩子相關。說到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系,孫睿并非首次書寫。他200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我是你兒子》涉及到了“父子沖突”,以兒子楊帆的視角講述對父親楊樹林從懷疑、叛逆到最終回歸的溫情故事。事實上,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這就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倫理不斷進行質疑、審視和解構的主題。洪峰的《奔喪》、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朱文的《我愛美元》、東西的《耳光響亮》都對傳統農業社會倫理的父子關系進行了極具革命性的挑戰甚至是挑釁。
現在,已屆中年的孫睿對這個敘事母題進行了反轉性的敘述。他不僅僅是子一代,也是父一代。《寶貝兒,帶我飛》講述一個畫家父親在與妻子發生爭吵后,獨自帶著女兒生活的一段時光。“米樂把油畫顏料甩到老婆臉上后,他老婆也甩了臉子,不到十分鐘便拉著行李箱走出家門,留下米樂和一個兩歲的孩子。”這個頗有戲劇性的開頭簡潔有力地把小說的主題和敘事張力展現了出來。都市人都知道,在“喪偶式教育”的家庭里“超人媽媽”離家出走的嚴重后果。孫睿選擇這樣一個激烈矛盾作為敘事的開口,既是生活經驗帶來的智慧,也是寫作經驗帶來的敏銳。
作家將一個只知埋頭畫畫不知育兒為何物的年輕父親在這種情況下的狼狽寫得細致生動而不乏幽默感。女兒睜眼要媽媽,米樂費勁地撒謊解釋;女兒要睡覺,米樂胡亂拍打,還是在女兒的引導下拍屁股窩兒把她哄睡著了;早上醒來,發現自己準備賣的商品畫被小孩的涂鴉給毀了,畫室的房貸又沒了著落;好不容易讓女兒吃完飯,她又要各種玩樂,過家家、放兒歌、跳舞、冒充動植物;米樂在女兒的指揮下帶她去了游樂場,玩得正歡,一轉眼她又跟別的孩子因排隊問題打了起來……這是“80后”的一地雞毛,它們和劉震云時代的“一地雞毛”雖然內容不同,但都同樣地瑣屑、磨人。
磨人的不僅僅是小孩,也不僅僅是離家出走的妻子。在小說中,作家只是借這“一地雞毛”作為開篇,真正讓男主人公陷入絕境的,是一代“北漂”從藝術院校的佼佼者“墮落”到以給酒店飯館畫廣告畫為生的痛苦,是他們被生活一點點磨去高傲心性和純粹藝術理想的痛苦,是他們在當年被群嘲的充滿銅臭味兒的同學老板面前不得不低下頭去的痛苦,只為一份從前看不上眼的訂單。在這些內外困境的交疊下,“房子”作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讓米樂徹底崩潰了。
這是真正的都市一代人的煩惱。關于這樣的煩惱,是只有像孫睿這代擁有豐富甚至純粹的城市經驗的人才能夠體會并寫出的,這也是我一直所看重的當下作家寫當代生活的敘事資源和能力。當然,在“一地雞毛”中,作為藝術家的米樂也曾經有過事業上的“輝煌”。他在畢業展上的畫作《笑臉》直接被搬進了798,他也被畫廊老板看中,簽了十年合同,是“最對得起這個專業的出路”。最初的“笑臉”系列米樂畫起來得心應手,當他被生活一點點打敗時,他再也畫不出那樣的畫,而生活需要付費。備受折磨之下,他的心境只適合畫“苦臉”,但不出意料,這么沉重苦澀的作品被老板拒絕了。
作家能夠寫出生活,能夠寫得婆娑葳蕤是敘事功底之所在,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要在這生活書寫外找到具有超越性的意義和價值。在小說中,這種超越性的價值來自于“飛”的意象。米樂的“笑臉”系列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感覺到“在那種笑臉中,人是飛起來的”。之后,作家為他設置了諸多的挫折、憤怒、驚慌和恐懼,讓他被生活生生地折斷了翅膀,但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他能夠再次“飛”起來。這一次,是他在新的顏料嘗試中畫出了飛翔的小孩拉著大人的手飛向天空。這時,出走的妻子回來了,女兒看到媽媽后如小天使般快樂地“飛”了過來。
這是一個接近完美的結局。它的溫馨甜美與小說開頭的粗暴冰冷形成了鮮明對比。作家在敘事中將“飛”進行了巧妙含納,那對小翅膀并非突如其來,而是在米樂的生活一塌糊涂的時候就悄然出現了。因此,當它最后與米樂一家的生活相融后,“飛”既是敘事的縫合,也是意蘊的水到渠成。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