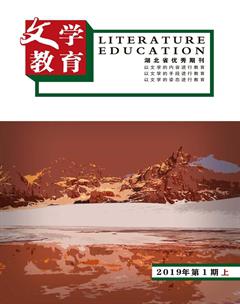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透明的紅蘿卜》中的白癡敘事
內容摘要:“白癡”、“傻子”作為特殊形象經常出現在作家的筆下,這一社會邊緣人成為敘事性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病理意義上,“白癡”、“傻子”通常指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人,一般指有先天生理、心理缺陷的人,身體畸形、智力為零。還有一種,是具有文學性的,如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與常人相比,是一“白癡”形象,與普通白癡相比,又似“精靈”一般,既沉默又靈異,既沉迷自我又向成人世界靠攏。
關鍵詞:透明的紅蘿卜 黑孩 白癡敘事
一.失語與暴語
《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稱其為“傻子”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的沉默、失語。通觀整篇作品,可以發現黑孩只在四個地方發出過聲音,除此之外,作者對黑孩的描寫只有肢體行為,而沒有話語表達。稍加注意就能發現,這四處僅僅只是發出了聲音,并非具有意義的言語。喪失了語言能力也就沒有了話語權,黑孩就真正成為了一個社會邊緣人。
分析黑孩的生存處境,作者通過小石匠之口注明了黑孩的過去,“這孩子可靈性哩,他四五歲時說起話來就象竹筒里晃豌豆,咯嘣咯嘣脆。可是后來,話越來越少了,動不動就象尊小石像一樣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在尋思什么。”可見黑孩的“失語”是由于后天環境造成的,自幼沒了親娘,親爹續弦后獨自下了關東沒個影,跟著后娘生活,后娘并不把他當人看待。在親爹走后,后娘愛上了喝酒,“喝醉了他就要挨打、挨擰、挨咬”,連小石匠都調侃黑孩是被后娘“打傻了”。莫言在小說中兩次以括號的方式注明黑孩身上有兩塊大疤瘌,可見,是作者有意為之,是在暗示和強調黑孩所受身體摧殘之重。如果說“兩塊大疤瘌”道出了家庭之不幸對其身體的摧殘,那“失語”乃是生理至心理整個的戕害。
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觀點,自然人到社會人之間是社會化,通常認為自閉患者、白癡、瘋子等都屬于社會化失敗的結果,很顯然黑孩就屬于社會化失敗的一列。試看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對黑孩的態度及語言描寫,和黑孩說話的第一個人隊長一見黑孩就對他呼哧道:“黑孩兒,你這個小狗日的還活著”,“劉太陽”看到黑孩后的第一句話就是:“這也算個人?”菊子姑娘是唯一一個愿意真正關懷黑孩,愿意同他說話的人,當菊子姑娘靠近他和他說話時,卻引來了周圍人的戲謔,“菊子,是不是看上他了?想招個小女婿嗎?那可夠你熬的,這只小鴨子上架要得幾年哩……”,雖然不是直接和黑孩對話,卻直接給他造成了傷害,也以至于黑孩從始至終都不敢接受菊子的關愛。自稱是黑孩師傅的小鐵匠,“滾”、“小混蛋”、“小狗崽子”這樣的話語更是不甚枚舉,這種語言暴力對黑孩是精神、情感和自尊的傷害。
可以說“失語”是黑孩面對外部環境而選擇的一種自我封鎖,此外還有身體封鎖。當黑孩被鐵錘砸手,被后娘用掃帚打屁股,赤身用肚皮貼著河墩向下滑,赤手撿起淬火的發紅的鉆子時,作者把場面描寫得驚心動魄,黑孩卻是一副“慢悠悠”、“不慌不忙”樣子,冷、熱以及痛感似乎在黑孩身上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也就是說,這就不單單只是外部環境的原因,更深層的是黑孩的一種自虐傾向和感官封鎖。
二.回憶敘述與夢幻敘述
張檸在其《敘事的智慧》中論述到,除了外部條件對聲音的擠壓可以造成聲音的復雜化,另一方面個人的“自我意識”也能對聲音產生影響,“用中國民間的說法,叫‘火焰低,即容易見神見鬼,五官出奇地敏感。這種‘自我,不但不能有效地抵制外部壓力,防止聲音變形,反而是逃到了私人的夢幻中,說一些咒語般的獨白。”①面對黑孩的失語,相應的補償機制就是黑孩擁有敏銳的五官,使黑孩身上透露出一股靈異的氣息,他能夠聽見蟲鳥音樂般的鳴叫、魚群唼喋,甚至能夠看見透明的紅蘿卜。菊子姑娘也多次注意到黑孩耳朵會動,眼眸深邃就像一個小精靈,這就使黑孩在“白癡”這個意義上,加入了“精靈”的色彩。
黑孩“自我意識”通過回憶和幻想顯現,逃到了私人的夢幻中,遁入為一種潛意識。回憶和夢幻既是小說的主要內容,又是重要的敘事方法。如馬爾克斯,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匯聚于同一語言時空的敘事模式在莫言作品中也頻繁出現。在《透明的紅蘿卜》中,作者就在順敘的基礎上運用了插敘。這既打破了時間順序,也在不經意中交代了黑孩的成長經歷和生存環境。“回憶敘述”在整部作品中就像網一樣,將人物的主要成長階段串聯起來,同時又使作品具有延展性,在有限的文本中表現出更大時間的內容。這個“回憶”包括兩個維度,一是前面提到的關于黑孩的回憶,從這些插敘中讓我們知道黑孩的成長經歷,知道黑孩失語的真相;另外一個是作家與文本之間,同樣可以稱之為“回憶敘述”,莫言12歲時參與修建水利工程,也曾因偷吃紅蘿卜而受眾人批斗。本篇就是在童年記憶上的加工,莫言自己也曾坦言自己就是書里的那個黑孩子,可見莫言將自己的童年經歷寫進了小說中。不同的是,莫言偷蘿卜是因為饑餓,而黑孩則被加工為遁入了自身的幻夢中。
再者就是“夢幻”,如果說“回憶敘述”打破了時間順序,那“夢幻敘述”就打破了空間界限,但同時也混淆了現實與夢幻間的距離,因為黑孩的幻想和夢境又時時沾染著現實的影子。黑孩一直在現實和幻想中徘徊,出出進進,這也折射出其自我與外界的矛盾。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菊子、小石匠、小鐵匠等都主動和黑孩發生過很多次語言關系,話題的焦點在黑孩身上,往往是旁人說得火熱,黑孩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沉默處之。這就形成了兩個圈子,一個是熱鬧的外部世界,一個是冷靜的黑孩世界,黑孩與外界存在著距離。而在黑孩的幻想與回憶中,卻呈現出了一個人的狂歡。黑孩的狂歡往往依托于自然環境,與人關系失敗,卻與自然相容。細看會發現,作者筆下的自然環境描寫跟隨著黑孩心境的變化而變化。當黑孩第一次下河去撿水桶時,魚兒親吻他,而當小鐵匠將透明的紅蘿卜扔掉之后,黑孩“身體軟軟的倒了下去”,不僅黑孩像丟了魂一樣,就連周圍的環境,也變得情緒化,“河水在霧下傷感地嗚咽著”、“幾只早起的鴨子站在河邊,憂悒地盯著滾動的霧”,同樣的是要下河去撿東西,這次面臨得卻是鴨子的嫌棄。學界很多人根據莫言童年的饑餓經驗,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人在極度饑餓的之下,食物被神化所產生的幻覺。這就致使很多讀者覺得莫言所寫過于魔幻化,失真。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正常的物理現象,烤熟了的蘿卜在火光的照耀下,的確是既透明又火紅,還能看清蘿卜中的經脈,只不過莫言用文學性的語言描述了出來,但這一很正常的現象,恰恰只有黑孩關注到了,所以透明的紅蘿卜就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是黑孩心象的載體,感情的投射,是潛意識在其夢中的表象,“透明的”、“發光發亮”的紅蘿卜與“灰色的”、“無愛的”現實形成巨大反差。小鐵匠把它丟掉了,就意味著丟失了黑孩的幻念,同時也剝奪了了黑孩與大自然“物我合一”的準許證。
三.代際隱喻
黑孩用“失語”和超強的“自我意識”將自己封鎖起來,但這并不意味著黑孩的世界里沒有成人世界,黑孩在封鎖自身的同時,也在尋找個體與世界兼容的途徑。
黑孩是一個羸弱且沉默的小男孩,除了出場不多的后娘的兒子,黑孩是整個作品中唯一的兒童形象,這就形成了黑孩一個人組成的兒童世界和其他所有人組成的成人世界兩個世界,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代際差異。黑孩對成人世界最初的認識是母親還在時的那個充滿愛的世界,后來出現的小石匠、菊子姑娘也是對這個世界的補充和發展。與此對立的是由劉副隊長、小鐵匠等人組成的一個冷酷、無愛的世界。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交錯影響于黑孩身上,形成了黑孩對成人世界復雜的認識,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黑孩一方面陷入“自我意識”無法自拔,一方面又在尋找通向成人世界的門票。
小說中有幾處黑孩向成人世界靠攏的例子,當決定派小石匠和黑孩去滯洪匣后,“孩子慢慢地蹭到小石匠身邊,扯扯小石匠的衣角。”二人行走時,黑孩“盡量使頭處在最適宜小石匠敲打的位置上”,這都可以看出黑孩努力使自己跟上小石匠的步伐,努力與成人步調保持一致。接著出場的就是菊子,雖然面對菊子的關懷黑孩仍不做聲,但他內心中是有感覺的,“現在,全工地的男人女人們都叫他‘黑孩兒,他誰也不理,連認真看你一眼也不。只有菊子姑娘和小石匠來跟他說話時,他才用眼睛回答他們。”可見,黑孩對成人世界是做了區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黑孩也在一步步向小鐵匠靠攏。小鐵匠對黑孩的態度不是打就是罵,但面對小鐵匠惡意的指使,黑孩都去做,如果說這些事情是黑孩面對強勢壓力所做出的被動選擇和妥協, 那面對小石匠和小鐵匠之間的戰爭,黑孩自動站隊到小鐵匠一方就足以說明黑孩自愿向小鐵匠靠攏。
在石匠鐵匠發生沖突時,黑孩幫著打罵自己的鐵匠,我認為原因是黑孩安全感的缺失。小鐵匠曾對黑孩說過要收他當干兒子,雖然小鐵匠是別有用心,但對這個世界充滿模糊認識的黑孩,他認為這是一個“名分”,不管是“干兒”還是“徒弟”,都可以,對于黑孩來說,這就是歸屬感。而小石匠和菊子姑娘,作者通過對這兩人的描寫,使小說增加了一個戀愛主題,而正是兩人戀愛關系的逐漸發展,使黑孩與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兩人相對于其他人來說確實對黑孩很好,但對于一個內心極度缺愛的孩子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
黑孩幾乎一直處于無愛的環境中,是一個極度缺愛的人,當小石匠和菊子姑娘這樣善良的人闖入他的生命中時,看似并沒有改變黑孩什么,但在黑孩的心靈深處,潛藏著連黑孩自己也不知道的波瀾。這種剛聚焦過來的愛,轉瞬又擴散開去。所以黑孩寧愿跟著使喚自己的“師傅”,也不愿再在沒有歸屬感的姑娘與石匠身上找關懷。
無論是對姑娘、小石匠,還是對小鐵匠,都表現出了黑孩在成人世界中的掙扎。一方面陷入超強的自我意識之中,“逃到了私人的夢幻中”,一方面又主動往成人世界靠攏,想在成人世界中找到安全感。
參考文獻
1.莫言.<透明的紅蘿卜>創作前后[J].上海文學,2006,(08).
2.莫言.透明的紅蘿卜[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3.莫言、王堯.莫言王堯對話錄[M].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3.
注 釋
①張檸.敘事的智慧[M],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
(作者介紹:江曼,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現當代文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