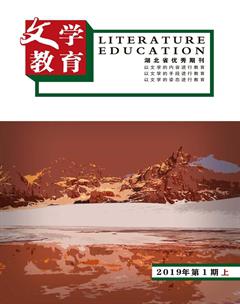周曉楓散文的題材取向
內容摘要:周曉楓散文,堅決地放棄選材上的潔癖,而保存葉子上的泥。作為一名女性寫作者,唯美與溫柔并非她的關鍵詞,暴力與純粹才是流淌于她骨骼中的血液。其散文挖掘隱秘而復雜之處的黑暗,努力地逼近破損的真相,最后獲得藝術的真實。
關鍵詞:周曉楓散文 題材 破損 真實
周曉楓的散文,在表達上給人印象很深的無疑是穿插在字里行間的“巴洛克的修辭”,這是她一直以來所偏愛的形式。對于語言的打磨和技巧的運用,她有著匠人般的執念。但這并不是她在追求華麗的語言所帶來的閱讀與審美快感,而是要通過一個絕妙的比喻,將看似無關的事物聯結得恰到好處。“修辭立其誠。”【1】越過考究且濃稠致密的語言,去抵達純粹的真實和事物的真相,才是作者真正的創作立場。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周曉楓的文字,在唯美和沉郁之外更多體現著冷靜的觀察和凌厲的表達。她常常發問,繼而思考有關于女性、身體、人性等一切復雜的事物。但在我看來,最特別之處還在于她的散文在努力地逼近破損的真相以還原某種藝術意義的真實。人們的內心往往是復雜而隱秘的,對于現實生活中的苦痛與黑暗,往往選擇逃避或修飾,“我們不敢面對,我們包庇,我們在黑暗上刷涂明亮的油漆以自欺欺人”【2】。而周曉楓以此為切入口,不斷地去挖掘光明背后藏著的黑夜,讓真相和無法示人的丑陋如決堤的洪水噴涌而出。
一.被蟲子啃過的壞果子
《有如候鳥》講述了一個小女孩在童年被性侵,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如候鳥一般不斷地遷徙,讓靈魂和肉體四處遠游和流浪的故事。對于世人羞于啟齒的丑惡,周曉楓選擇大膽地撕破并直白地暴露:“她躺上羞恥之床,再次分開蚌殼般閉合的部分……聽任探測者打開光線,照射秘密的溶洞。”類似這樣的描寫文中還有許多,不禁讓我聯想到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運用比喻方面,這兩位女性作家都是天賦異稟的:每一個比喻都是一個暴力現場,每一句話都仿佛是一記重拳,重重地打在讀者的心上,疼痛與眩暈中還帶有血的咸腥。散文中的小女孩把自己當作“一枚被蟲子啃過的壞果子”。她失眠,與和她年齡相仿的房思琪一樣害怕閉上眼睛,因為即便進入夢里,也只是墜入深深的黑暗:“夢里的鐵匠帶著強烈口臭,用老年的猥瑣,釋放他不能平息的情欲……叔叔的犁,數次開墾在她身體荒涼而堅硬的凍原上,他身體前行的每一步,都是她每一公分的黑暗。”小女孩夢里的鄰居叔叔就像房思琪噩夢里的李國華老師,他們一步步地吞噬掉少女的肉體和靈魂,肆無忌憚。因為,他們知道“一個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臟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傷人傷己的針,但是在這里,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3】。
由于社會觀念和家庭教育向來都和性保持著一種安全距離,即使是公開談論也都被當成一種禁忌。因此,當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后,作為受害者的女性,特別是沒有接受性教育的年幼者,往往羞于啟齒而選擇獨自忍受。說到底,性侵其實是一場社會性的謀殺,施暴者逃之夭夭,旁觀者冷眼相向,只留下受害者獨自將丑惡與骯臟深埋土中,最后,沃土變成荒原,寸草不生。
二.男友的密紋唱片
“假設抹除那些破損,我們只會目睹一個失真的豐收。”【4】周曉楓深知,真實的丑要比失真的美更具有存在的價值。因此,除了寫性侵,她還在《布偶貓》中揭露了愛情中的破損:男方對女方的暴力行為。
女主人公叫小憐,聽名字就讓人憐惜,而她正是這場愛情中的殉葬品。布偶貓是作為一個施暴者的男友在肢體沖突后給她的道歉和補償。布偶貓因性格溫和而常常成為家養寵物的首選。可不幸的是,在這場愛情悲劇中,小憐的命運和這只貓有著驚人的相似:她們一同收起自己的爪牙,以超乎尋常的忍耐去艱難地消化著自身的不幸,向“主人”乞討垂青與偏寵。
在同樣作為女性的“我”看來,她可真傻,就算是被傷到劇烈,也還要在掩飾中歌唱,“仿佛注定是男友的密紋唱片,可以承受他重復中不斷的劃痛”【5】。“我”并不明白,為何小憐會對施暴者產生如此強烈的依戀。但在惋惜和不解之余,卻忍不住想要去剖析這場悲劇中的男女主角。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女之耽兮,不可脫也”,小憐已沉湎于這場悲劇的美學之中。可“我”需要在這場關系失衡的畸形愛情里,把那些埋藏在內心隱秘處的病態的念頭全都暴露出來,并在此基礎上去思考暴力與愛。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身邊有千千萬萬個小憐存在,她們“蜷起四肢,形同遭受暴力的姿態,回縮成為母腹中脆弱的胎兒……既不能接受現實,也難以面對未來”【6】,而悲劇的根源正是她們和布偶貓一樣,擁有著耐痛的美德。
在社會角色的認定中,除去母系社會的那個時代,很多時候,女性都被當作弱勢群體。因為她們的身體里總是流淌著母性的血液,其中包含著寬容。而流淌著“暴君”血液的男性,常常會選擇暴力來完成他們的統治。沉湎于錯覺的女性,在畸形的寬容中,進行自我欺騙以實現自我的救贖。當逾越界限的暴力將失控的情緒和肢體配合在一起時,她們以為這是強烈到失控的愛欲。既然是愛,當然需要無限的給予:讓自己如教堂一般的身體,去寬容那些施暴后的悔意與求饒,讓這具傷痕累累的身體去孕育暴力與愛交媾的產物。然而,在男性眼里,女性的“悲戚、恐慌和屈服,對他來說是一種小娛樂──哭紅的眼睛,顫抖的肩膀,女人反而具有旦角般的一種嫵媚……哀感頑艷的形象讓他興奮,仿佛聽到做愛中的嘆息”【7】。他們尋求的是快感,即使這背后充斥著罪惡與殘忍。
三.殯儀館里的化妝
在《離歌》中,周曉楓說屠蘇那張像經過不自然地敷粉的美顏自拍給了她不祥的感覺,因為這有點像殯儀館里的化妝。描寫中流露出作者對“化妝”的厭惡。當然,這里的“化妝”應該是廣義的。是的,化妝掩蓋不住殘酷的真相。在周曉楓的散文中,她索性將人世間的“美顏”“化妝”通通卸掉,還他一個真實的面容。
青春或是童年,這些詞語“特別容易被文人過度修飾,其亮度幾近飽和,最后變成美妙的烏托邦”【8】。很多文人深知世人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他們選擇自動過濾掉丑和惡,為讀者構筑一個虛幻卻又真實的烏托邦。但周曉楓不同于這些文人,她在散文中常常給那些過度修飾的詞語卸妝。在《惡念叢生》中,童年的我們不再如表面那般天真無邪,其中還隱藏著常常被大人們忽略的殘忍:“我們燙死螞蟻和蝴蝶;撕斷蜻蜓的翅膀,讓它成為一根新鮮的鐵釘;我們用汽油浸泡野貓的尾巴,讓它邊奔跑、邊燃燒,像雷神降下的小火球……”【9】卸掉濃妝艷抹,童年也有其殘忍的一面。這或許才是童年的真實面目。
周曉楓的散文中,還有比這更為殘忍的景象。
在《石頭、剪子、布》中,她這樣描寫被無軌電車碾壓后的貓:“前半截的身子粘貼在地面,突然消滅了體積,只有勉強形成的厚度;后半截的肢體完整,甚至飽滿,奇怪的是兩條毫發無傷的后腿一直在輪流蹬踏,遭受了電擊似的。這只貓暫未接受自己瞬間的死,它還在持續逃跑的慣性里。沒有頭臉和胸腔的貓,它只剩腰下的抽搐身體。”周曉楓在冷靜地描述一個無比慘烈的畫面,但越是這般的冷靜,就越使人毛骨悚然。她的這類文字,已接近于孫紹振先生所說的“審丑”了。孫紹振先生指出,“審丑不一定是對象丑,而是情感的冷漠,冷漠是最根本意義上的丑”【10】。被碾壓后的貓,已經是“丑”了;而把如此慘烈的畫面當作藝術品去細細地品鑒,則顯示出情感的冷漠,冷漠到近乎殘忍,這才是真正的“丑”。作者想要傳達的,或許就是人性中的破損。
對于那些被掩蓋掉的破損、殘忍等丑惡,周曉楓選擇“放棄選材上的潔癖,保存葉子上的泥”【11】,用豐富的聯想、曖昧的象征以及絕妙的比喻去和讀者的精神“潔癖”來一場正面的交鋒。她深知讀者保留著美化女性的期待,但她卻偏愛站在邊緣寫作,因為邊緣地帶往往更靠近真實。她不會回避靈魂或肉體的黑暗與不堪,相反,她“小心翼翼地敲擊一個又一個的詞,直到它們的蛋殼上出現細小的裂隙。那些精美因她而破裂的紋路,是屬于她的創造”【12】。正是因為破裂,才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圓滿。因為,透過破裂的縫隙,讀者才能看到隱匿于文本背后的真相——作者以恥為榮,以冷靜和理性去直面破損和羞于啟齒的欲望。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想要“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強光里造成瞬盲”,【13】本就不是一件易事,而要在黑暗中找到裂口去更深入地逼近真相也就更難。但是,“老少咸宜”的安全,只會使人錯失探險者才能目睹的極境。只有直面自身的黑暗帶給我們的危險,才會在探險中收獲“其見愈奇”的真實與美麗。在散文的這場探險中,周曉楓無疑是滿載而歸的。
參考文獻
[1][2]周曉楓:《與姜廣平先生對話》,《周曉楓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97頁。
[3]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24頁。
[4]周曉楓:《來自美術的暗示》,《周曉楓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頁。
[5][6][7]周曉楓:《布偶貓》,《有如候鳥》,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1、47頁。
[8]周曉楓:《與姜廣平先生對話》,《周曉楓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頁。
[9]周曉楓:《惡念叢生》,《有如候鳥》,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頁。
[10]孫紹振:《孫紹振解讀經典散文》,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75頁。
[11]周曉楓:《來自美術的暗示》,《周曉楓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頁。
[12]周曉楓:《初洗如嬰》,《有如候鳥》,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頁。
[13]周曉楓:《有如候鳥》,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頁。
(作者介紹:薛勝寒,山東大學文學院在讀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