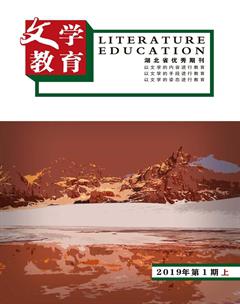論《無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識和“記憶”與“夢”
內容摘要:學界關于《無名女人》及湯婷婷的解讀與研究,主要圍繞著女性主義、性別與種族歧視等方面,而對于其中體現的“身份意識”與“記憶”、“夢境”等問題卻相對缺乏重視。本文將從弗洛伊德的“身份”與“夢”的理論出發,從而挖掘《無名女人》中潛藏著的“身份”意識、“記憶”與“夢”的獨到存在。
關鍵詞:《無名女人》 弗洛伊德 “身份意識” “記憶” “夢”
《無名女人》是華裔女作家湯婷婷《女勇士》的第一章節,也是窺探湯婷婷內心深處關于“身份意識”、“記憶”與“夢境”的重要考察文本。深入考察文本可知,湯婷婷除了展現了“中國人”和“女性”的雙重“身份意識”,在書寫過程中同時展現了她深層次的童年記憶及獨到的“夢”。
一.《無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識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的A Studentc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認為,“身份就是一個個體所有的關于他這種人是其所是的意識。”[1](P87)弗洛伊德曾用“Identification”的概念來解釋人對他人的歸屬。“身份”一旦被“認同”于某種屬性,則其他屬性的差異便被確認。錢超英進一步解釋“身份”意識在移民及群體中的重要意義:“‘身份概念尤其便于用來考察和研究那些在明顯不同的‘文化歷史設定的裂縫之間漂移運動的‘主體——移民、‘問題群體、在全球化中經歷急劇社會轉型的民族——所必然面臨的生活重建經驗。一個人從原居國移民到另一個國家,或者從鄉村遷往城市,所面對的不僅是居住環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變化等實際問題,而且更是關于‘我曾經是誰、現在是誰、‘我為什么如此生活的問題,他需要有一種令其滿意的完整解釋,以便接受和平衡轉變所帶來的風險,使自我和變化著的環境的有效聯系得以重建,以免生活意義的失落和虛空。[2](P91)
《無名女人》中的“身份意識”,筆者認為,至少有3層:一.姑姑的姓名以及其作為家族女兒的身份;二.女性在舊時中國兩性關系中的身份;三.作者在美時反觀自我國人的身份。
第一層是故事層面上的身份確認,即姑姑的名字。從題目《無名女人》中已經看出,書寫“無名”是為了證明“有名”。這個“名”不僅僅是姓名的意思,還有的是一個人曾為人的憑證。“無名”就意味著“姑姑”得不到“認同”,所以無法確認有無。要么是帶有他傳性的真實存在,要么是“幻想”與構筑。姑姑除了不被家族承認,也不被村里承認,“就跟沒出生過一樣”[3](P66)也就是說,姑姑的身份,被剝奪被消滅了。為了彌補身份缺失,“我”選擇了“幻想”。
其次是女性身份在舊中國兩性社會關系中的重提和肯定。“我”在母親的勸慰下,重提了女性在兩性社會關系中重要地位。有研究者認為湯婷婷的書寫有過分媚俗嫌疑,主要是她對舊中國的某些現象加以歪曲或者丑化。筆者認為,湯婷婷之所以強化某種現象的書寫,其實是對女性身份的再肯定。除了直面描寫姑姑以外,作者還從側面展現否定女性身份的現象,“兄弟姐妹們都剛剛成人,他們必須抹去性別的特征,表現出普通的儀態。”[3](P71)
第三則是在美華人反觀自我國人的身份。盡管是美籍,但身體總不免流淌著中國人的血,也就是說,浸潤著中國文化血統的作者,需要找回這種陌生的熟悉感。筆者認為,作者的異鄉書寫,實際上是在“尋根”。身在異鄉的“我”,不免感慨“作為華裔美國人,當你想了解自身哪些東西屬于中國時,你怎分得清哪些是中國特有的,哪些是童年,貧窮,瘋狂以及一個家特有的,哪些是你成長過程中給你講故事的母親特有的呢?什么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什么又是電影里虛構的東西?”[3](P67)
二.《無名女人》中的“記憶”與“夢”
F.W.希爾德布蘭特解釋“記憶”和“夢”兩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無論出現什么樣的夢,它的材料都來源于現實,來源于以這個現實為中心的精神生活。......換言之,它必定來自我們已客觀地或主觀地體驗過的事物中。”[4](P6)弗洛伊德進一步闡釋兩者關系,“所有構成內容的材料均按某種方式來源于體驗,它們在夢中再現或被記起——這些至少可以當作不容爭辯的事實。”[4](P6)換言之,現實或者記憶由于種種條件的阻礙,無法滿足人類所有期盼,對于這種不爭的事實,人類不得不接受。當這種矛盾的情感帶入到夢境中,則盡情釋放,由此擬補了現實或者記憶中的空缺。所以夢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它的內容”[4](P79),以至于具備了以下特點“短小和簡單”[4](P79)的、“混亂和繁雜的”[4](P79)。
關于《無名女人》中的“記憶”與“夢”,筆者看來,有以下兩種解讀方式:1.假如姑姑已死是“記憶”,那么作者對姑姑的生平則是“夢”,作者通過想象姑姑的生平傳達對姑姑的思念;2.假如童年禁欲是記憶,那么對姑姑生平的想象則是實現生理欲望的釋放。對姑姑生平的想象,即“幻想”,屬于“夢”的范疇。作者在有意識地“做夢”,而這種有意識地“做夢”是某種程度的理性壓制。
如果禁欲是記憶,那么作者在書寫姑姑的生平時實際上是生理欲望的釋放。筆者認為可以采用倒推的方式對文本進行探討。所謂“倒推”,即至把文本進行倒置閱讀,然后再進行分析。參看以下兩段文字:
或許返祖現象多于恐懼,我曾經暗暗地在男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兄弟二字,這樣一來,不管這些男孩子請不請我跳舞,我已叫他們都中了魔法——他們顯得不那么可怕,反而像女孩子一樣親近,一樣值得善待。
當然,我也給自己施了魔法——不約會。我本該站起來,揮舞雙臂,隔著圖書館大喊:“喂,你!愛我吧。”但是我不知怎樣有選擇地吸引異性,吸引誰,吸引到怎樣的程度。假如我顯示出自己美國式的風采,從而使班上那五六個中國男孩愛上我,那么班上的其他人——高加索人、黑人和日本人也都會愛上我。看來還是莊重、可敬的姐妹版的風采更為適宜。[3](P71-72)
以上文字不得不讓筆者產生以下疑問,作者基本上是以激情洋溢的狀態對姑姑的生平進行了一番盡情的想象與描繪,可是卻又在文本后半段用壓抑遮蔽的手法展現現實的對立,這種矛盾性如何理解?筆者認為,正是這種“記憶”中的壓迫(筆者注:此處“記憶”包含過去時和現在進行時),才導致夢境的張揚跋扈。換言之,主人公通過對姑姑生平的激情想象來滿足自我愿望,這個目的直指生理與欲望上的滿足與釋放。
弗洛伊德將這種夢概括為“感情的夢”,他認為“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渴望”和“煩躁心境”的夢是相似的。[4](P82)筆者認為,作者負有激情的對姑姑生平的想象與描繪,也體現著一定程度上的煩躁與焦慮。有如這段姑姑生產的文字描述:
她跑到外面地里,跑得遠遠的,直到聽不見他們的聲音。她把身子緊緊地貼在地上,這再也不是她自己的土地了。她感到臨產前的陣痛,還以為是自己受了傷,身子縮成一團。她想:“他們把我傷害得太狠了。太可恨了,就要害死我了。”她用額頭和膝蓋抵著地,身體抽搐起來,一會兒又放松了。她翻身平躺在地上。天空有如一口黑井,星星一顆顆地熄滅,熄滅,永遠熄滅;她的身體。她的全部好像都消失了。她也是一顆星星,黑暗中的一個亮點,沒有家,沒有伴,永遠在寒冷和寂靜之中。一種對曠野的恐懼從她心底油然而生,越升越高。越變越大,她沒辦法控制了:這無邊無際的恐懼
上述文字張力十足,姑姑宛如一匹受傷的狼在原野上嚎叫。但是,與《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受傷的狼不同,姑姑更多的感到外在世界的恐懼而蜷縮,而《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女人卻更多表現對殘酷命運的怒號。所以前者體現的除了焦慮,還有恐懼,后者更多的體現憤怒。以至于姑姑后來跑向豬圈,此處作者用“虛無”一詞來強調一種無意義——外部世界的冷漠與自我生命的凋零。
三.結語
本文從弗洛伊德的“身份”、“記憶”與“夢”的理論出發,挖掘《無名女人》中潛藏著的“身份”意識、“記憶”與“夢”的獨到存在。這種“身份”意識體現在三個層面:一為姑姑的姓名以及其作為家族的女兒的身份;二為女性在舊時中國兩性關系中的身份;三為作者在美時反觀自我中國人的身份。此外,“記憶”與“夢”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姑姑已死是“記憶”,那么作者對姑姑的生平則是“夢”,即作者通過虛構想象姑姑的生平以達到滿足好奇和表達意志的愿望;二是童年禁欲是記憶,那么對姑姑生平的想象則是生理欲望的滿足于釋放。綜上所述,關于心理學與《無名女人》之間的關系,還有更多的可供挖掘的空間。
參考文獻
[1]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A Studentc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Z]. Edward Arnold, 1988.
[2]錢超英.身份概念與身份意識[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4).
[3]胡上花.華美文學作品集:短篇小說卷[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4](奧)弗洛伊德著;張燕云譯.夢的釋義[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作者介紹:黃恩恩,廣東科技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