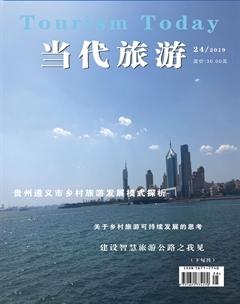缺席審判實務問題淺談
張昌蘭
摘?要:當前我國法律對于缺席審判實務方面的限制相對簡要,在進行庭審的過程中,不同的地區亦或是不同的法院對于缺席審判的適用條件以及對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的認識存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因此這就導致司法程序的統一性丟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當事人利益受到沖擊。本文從缺席審判的兩個角度著手,即缺席審判的適用情況以及缺席審理案件中證據的判定,以求能夠為有關工作者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缺席審判;實務問題;適用情況;證據判定
缺席審判從屬于對席審判的對稱,二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存有當事人之間產生的辯論,在庭審過程中,法官需要按照雙方當事人的辯論情況來作出相應的判決結果。然而在缺席審判的過程中,某方當事人由于非正當原因而沒有到場,因此這就導致當事人辯論環節無法正常進行,在此種情況下如何更為有效地判定缺席審判的適用性與證據的準確性就顯得極為重要。
一、缺席審判的使用情況
按照我國有關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被告以及被訴方在收到傳票傳喚后并無正當理由便缺席庭審,或者在為獲得法院允許便退庭的情況下,可以執行缺席審判。如果因為被訴方收到傳票傳喚卻無緣無故缺席庭審而執行缺席審判的話,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對被訴方實行傳票傳喚之后才能夠執行缺席審判。這里所說明的傳喚表明的并非是傳票發出,而是被訴方已經收到傳票的情況下,包含直接送達、公告寄送以及郵寄送達。如果并未向被訴方做傳喚處理,那么不能適用缺席審判。即便有證據能夠證明被訴方已經得知庭審的音訊也不能執行缺席審判。
正當理由的有無是執行缺席審判與否的重要支撐。在庭審過程中,被訴方由于何故缺席庭審是其自身需要證明的問題,但是在庭審當日,被訴方并為出現自法院之中,因此法官無法要求被訴方當庭進行解釋,而如果不予以開庭處理,那么勢必會導致當事人產生怨言,導致法院的整體公信力受到沖擊。在此種情況下,應該確定缺席當事人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然而實際上,此種情況下的當事人還有可能因為正當理由缺席,例如,被訴方偶遇車禍或者重病住院等等,因而無法及時聯系法院,此種情況下適用缺席審判顯然會導致當事人所具有的實體權利受到侵犯。鑒于此,如果出現當事人已收傳票但是卻并未出庭的情況,應該為其留出相應時間,以方便當事人提出自己缺席庭審的理由。結合民事訴訟法的第76條規定,應該于當事人缺席庭審之后的10天內進行庭審宣判。如果在二次開庭之前,缺席被訴方存有能夠證明自己缺席的正當原有,那么法院應該另行安排開庭時間。
在民事訴訟之中,如果第三人缺席庭審,應該如何進行有效處理,其在法律范圍內并未作出明確規定。雖然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于第三人缺席庭審的情況進行了規定:第三人經過合法傳喚后并無正當理由卻為出席庭審,或者未經法院允許擅自提聽的情況不影響案件的正常審理。但實際上,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的本質差異較大,民事訴訟過程中不能照搬行政訴訟的有關規定。在民事訴訟中所涉及到的第三人主要包含具備以及不具備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結合法律的具體規定來看,具備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通過提起訴訟的方式參與到原定訴訟之中,其在庭審過程中的地位與原告的本質類似,如果庭審過程中,第三人并無正當理由缺席,或者在庭審過程中未經法官允許便退庭,那么可以視作其放棄正當訴訟權利,庭審過程中裁定第三人撤訴,繼續審理原告和被告二者的民事爭議。
此外,部分學界人士指出缺席審理案件并不適合采用簡易程序完成,此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在我國有關法律條文中明確指出,起訴階段被告如果下落不明,不能通過簡易程序完成。被告如果未經出現,那么案件的審定自然而然就是缺席審理,但是此規定的適用范圍是起訴階段、被告、下落不明的交集,并非說明所有因為被告未經出現的情況均能夠應用簡易程序。如果起訴階段的被告的下落并不明確,那么法院只可以借助于送達公告的方法來為被告出具傳票,在此種情況下,被告自身對于庭審的事情可能一概不知,為求慎重,此類案件的審定與判決均不能依靠簡易程序完成。在部分案件中,在法院傳達傳票之前其并未消失,但是在傳票到達之后其突然下落不明,如果是此種情況,那么法院可以按照具體情況執行簡易程序,通過缺席審理的方式完成庭審工作。
二、缺席審理過程中的證據以及事實的判定
在《證據規定》中明確指出證據需要在法庭中初始,由當事人進行質證,如果證據并未被質證,那么其不能用作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在進行具體庭審判決的過程中,如果當事人缺席審理,訴方所提交的證據并不能直接交由被訴方進行對峙,在此種情況下,倘若法官單純地認定被訴方未質證證據而拒絕認定訴方所提供的證據,那么定然會導致此后庭審的缺席審理概率大幅增加,訴方所具有的權利受到巨大侵犯。所以,如果庭審過程中出現缺席審理問題,那么應該當做被訴方放棄自己所具備的質證權利,訴方所呈交的證據均被是做已經受到質證。然而,在缺席審理過程中的被訴方是沒有發表意見的,因此法官對于證據是否具備真實性的判定缺乏。實際上,對于此種情況也是具有明確規定的,在《證據規定》中提出法官在遵從自己的職業道德情況下,按照日常經驗以及邏輯思維來進行推理,用以判定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
結語:
總之,缺席審判的立法初衷是為了保障出席庭審的當事人的正常權益,避免訴訟資源的浪費。但是在我國實際法律規定中,對于缺席庭審的多種情況的規定并不清晰,因此在進行具體審定的過程中,需要從多方面著手,顧全大局,充分體現出訴方的利益方可。
參考文獻:
[1]石竺鑫.?論我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的完善[D].遼寧大學,2019.
[2]李煥芝.?論我國刑事訴訟缺席審判制度的構建[D].遼寧大學,2018.
[3]霍穎.?民事缺席判決制度研究[D].遼寧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