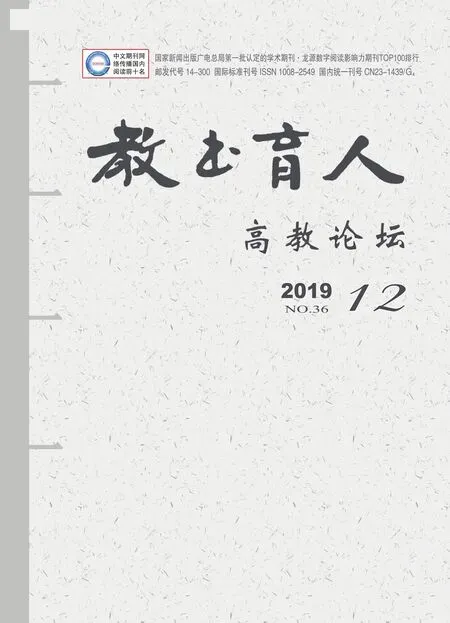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技術對高校思政教育的作用
——以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理論為視角
高尚 (北京城市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當代中國大學生越來越傾向于在網絡文章、影視劇等文藝作品中接受多元化思想的沖擊,排斥過于枯燥正式的宣傳教育方式,且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已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傳統的理論書籍、先進人物報道等難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腦、入心,這使得高校思政工作面臨很大挑戰。本文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本雅明的文藝理論為基礎,分析技術在文藝影響意識形態過程中的作用,并探討文藝技術的革新在“互聯網+”的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體實踐。
一 技術:生產理論視閾下藝術性與政治性之爭的新解
文藝作品的藝術性與政治性在歷史上通常被解讀為三種關系模式:一是作品的政治性要高于(甚至控制)藝術性,如在柏拉圖所構想的“理想國”中;二是作品的藝術性要高于(甚至抹殺)政治性,如以王爾德為代表的唯美主義流派;三是要求作品的藝術性和政治性兼備,如孔子提倡文藝要“盡善盡美”。但無論哪種模式,都把文藝性和政治性看成是相互對立的兩個目標,要么是簡單地把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要么是高難度地苛求兩個不同的目標都實現,二者的矛盾未得到真正的解決,也無法給藝術家指引一條真正可行的、將兩者統一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發展,二十世紀現代派藝術繁榮發展,其技巧性不可謂不高,但這些作品的政治傾向又很難讓那些提倡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將它們評價為進步的藝術。這個問題同樣歷史性地擺在法蘭克福學派面前,本雅明用文藝生產理論創造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曾對技術、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做過諸多具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論述,其中,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作為生產者的作家》。[1]這篇由演講稿整理而成的馬克思文藝理論經典著作成文于歐洲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經濟上,資本主義經濟飛速發展,工業化程度不斷加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也上升;政治上,正處于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期,法西斯勢力猖獗;思想上,左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唯意志論和新現實派盛行;文化上,現代派文學藝術顛覆了古典主義藝術,廣播、報紙等大眾傳媒流行。本雅明在此背景下從“技術”進步的視角,肯定了現代主義藝術是現代社會的必然選擇,大眾傳媒的技術代表著先進的藝術生產力。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文學家不能固守舊有的形式技巧,而應采用新的藝術形式,推進藝術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他把馬克思主義生產理論和藝術生產觀念創造性地運用到文藝批評當中,認為文藝創作也是一種生產,文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影響生產力,藝術家作為生產者,以某種生產方式為某一階級服務,藝術質量和政治傾向是可以達到統一的,“技術”是關鍵,先進的文藝生產技術必將帶來進步的生產關系,文藝的傾向性可以存在于技術的進步或者倒退中。他所言的技術一方面指文藝作品的創作技巧,一方面指媒介傳播技術。因此,藝術家不僅要通過提高文藝生產技術創作更多質量更高的作品,更要改進生產機器,使更多藝術家和接受者都參與到無產階級的文藝生產實踐中。
二 技術在文藝影響思想政治過程中的作用
歷史上,技術對思想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在創作技術發展中,俄國作家謝爾蓋·特列契雅科夫主張在行動中創作,再用創作影響民眾的行動,他親身參加1928年俄國農業集體化運動,寫出的《土地的主人》一書促進了集體經濟的進一步完善。這種創作方法是一種技術。本雅明從這個例子中特列契雅科夫的身份可能被定義為新聞記者或宣傳家而不是作家來引出文學形式的問題,提出小說、悲劇、史詩劇、翻譯、修辭學等形式所處的地位都不是永恒的,由于技術的發展,“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文學形式的巨大的重新熔合的過程之中”[2],由此得出內容和形式、正確的傾向性和文學質量的對立是無意義的,它們在“技術”的基礎上是辯證統一的,技術變革了文學形式,提升了文學質量,也更有利于政治運動的發展。正確的政治傾向依賴于進步的文學技術,文學的傾向性也就可以存在于文學技術的進步或者倒退中。
報紙這一傳播方式可以作為另一個例證。報紙技術的出現使科學與美學、批評與作品、教育與政治之間的對立可能會消失。讀者吸收著大量內容,急切地希望自己的興趣被表達,因而就有可能成為作者的合作者甚至自己成為作者。建立在職務意義而非專業意義上的作者是在多種技術訓練中建立起來的,他們把生活境況文學化,代表其生活發言,并且這種技術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特權,而是被大眾廣泛掌握,這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因此,報紙——生產工具,是作為生產者的作者通過提高文學技術可以促進思想政治傾向這一論點的很好的例證。
此外,技術具有革命性。藝術生產理論視域下,作家不僅要在觀念上經歷革命的發展,更要對他的工作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以及對他工作的技術進行真正的革命的徹底思考。“一種政治傾向,不管它顯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思想觀念上,而不是作為生產者與無產階級休戚與共,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3]他用布萊希特的“改變用途”概念——生產形式和生產工具的改變來補充他的觀點,即布萊希特向知識分子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要求:“不提供沒有盡可能地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加以改造的生產機器”[4],也就是作家不能僅僅提供生產機械,還要改變它,使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成為衡量文學技術進步與否的一個標準。所謂僅僅提供生產工具,主要是針對左翼知識分子而言的,他們有革命的沖動和要求,他們也通過新的技術形成的文學運動來表現這種革命的沖動,但是他們并不是借此將生產工具從統治階級手中解放出來服務于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雇傭文人而已,他們所提供的工具并不具有進步的性質。為了佐證,他又舉了兩個反面例子——德國左派知識分子中的唯意志論和新現實派。唯意志論所推崇的“有精神的人”是游離于現實階級之外;新現實派在發行技術的進步下促進了攝影的發展和報告文學的流行,卻墨守成規,其生產機械即便出版大量的革命論題,也不曾對它和占有它的資產階級的存在真正提出質疑,甚至即便站在批判的立場上也把苦難美化成享受的對象,把痛苦的斗爭從生產資料變成消費品,逃避了政治責任,因此,也陷入了反革命的深淵。
變革生產工具還意味著推翻束縛知識分子生產的另一種障礙——專業化。例如圖畫和音樂,在資產階級的觀點里,少數人的專業化有利于提高藝術的質量,這種專業化的權限建立生產過程的秩序,但在本雅明眼中,技術生產力的進步是政治生產力進步的基礎,作為生產者的作家必須超越生產過程中的專業化權限,通過與以前對于他們不太重要的生產者取得一致,使文字和照片、詞和音樂結合。把藝術賦予文學的說明,變革生產工具,才能使藝術生產技術和文學生產技術共同發展,并使這種生產具有革命的使用價值,還能使藝術家和消費者、技術和內容的對立得到克服。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技術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化生產的專業化,使包括普通教師在內的更多人能夠參與到文化生產中。
三 “互聯網+”時代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兩個優秀案例
《那年那兔那些事兒》和“TED 演講”正是在“互聯網+”時代運用上述理論中技術的兩個層面——“文藝創作技術”和“文藝傳播技術”。
《那年那兔那些事兒》是網友“逆光飛行”基于“野風之狼”所寫《小白兔的光榮往事》長貼所改編的漫畫,從2012年在新浪微博、那年那兔那些事兒貼吧、有妖氣、飛揚軍事論壇等熱門網絡社區連載開始,至今已吸引了眾多網友。作者用漫畫的形式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兩彈一星、中蘇關系、中美外交等重大軍事、外交事件生動地表現出來,所用詼諧的網絡語言給枯燥的歷史增添了趣味,是一部很有網絡特色的愛國主義作品。這是典型的文藝創作技術創新,比起歷史教科書,更便于大眾接受,也成為多所高校思想政治課堂上播放的教學視頻,贏得了學生的廣泛歡迎,也在潛移默化中使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植于學生內心。
“TED 演講”是發源于美國,借助互聯網得以迅速傳播的品牌。TED 本是以技術(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設計(Design)聚集在一起的俱樂部,其主旨為Ideas worth spreading,在傳播的過程中,由于網絡視頻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社交的思維方式日益盛行,TED 已經成為日流量超過10 萬人次的網絡社區,在科技、藝術乃至意識形態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其中的演講者李世默從一個風投的角度在TED 平臺上演講了《兩個制度——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元敘事的終結》,對西方民主制提出了質疑,為中國的一黨制做了論證,在世界范圍內肯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制度是多元趨勢下的一種合理的存在,深入淺出,易于受眾接受,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宣傳的一個值得借鑒的范例。
上述“互聯網+動漫”和“互聯網+演講視頻”的案例中,文藝作品都實現了藝術性與政治性的統一,在文化生產力的提高的同時進行了有效的思想政治宣傳,可以打破傳統思政教育中形式枯燥與藝術性削弱的歷史常態,為新時代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綜上所述,關于文藝和政治之間的關系,本雅明創造性地消除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所構成的無法統一的二元標準問題,用技術將文藝作品的藝術性和政治性聯結起來。因此,重視文藝生產技術是今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忽視的、需要大力發展的一個關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