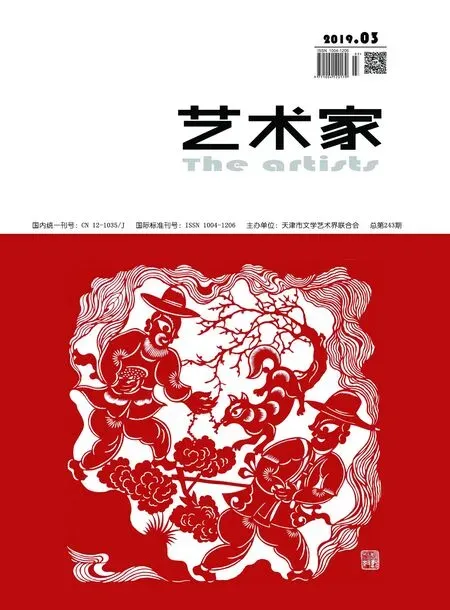怪誕之筆 極簡之墨—淺談八大山人繪畫藝術風格
□郭術山 天津博物館
一、朱耷的身世背景對其藝術造詣的影響
(一)身世背景
朱耷(1626-1705)于明朝天啟六年出生于江西府南昌的弋陽王府,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的后代[1]。其父朱謀覲擅長畫山水花鳥,對書畫藝術有很深的造詣,其在朱耷幼年的習畫過程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從小受皇室級別的文化教育,加上對繪畫的熱愛,使朱耷有了很好的文化藝術基礎。崇禎十七年(1644)清軍的入侵使明朝滅亡,朱耷全家為躲避迫害開始南遷,在諸多現實的打擊之下,朱父抑郁身亡,此時年僅十九歲的朱耷可以稱得上是國破家亡,至親逝世,無依無靠。他從皇室貴族生活跌落為前朝遺民,并時刻提防清王朝的迫害,后期清朝“文字獄”盛行,各種政治迫害愈演愈烈,朱耷不得不四處流離,隱姓埋名的生活。
(二)思想轉變
相傳他在生活中裝聾作啞,一言不發,并在門前貼一個“啞”字,僅以手勢、筆墨進行交流。曾經“少為進士業,試輒冠其濟。隅里中曹碩,莫不噪然”的朱耷[2],如今開始與之前有著天壤之別的逃離生活,令人唏噓。爾后,在清朝“留法不留人”的嚴政條例下,為了自保同時留住朱家皇室的氣節,朱耷選擇遁入空門,修佛參禪十幾余年,佛學禪宗的思想使他的作品得到了空靈的浸潤,滌蕩了浮躁。在此期間,朱耷開始使用“八大山人”作為其落款,“八大山人”四字在他連綴的寫出后,看起來很像“哭之”“笑之”。他曾題詩“無聊笑哭漫流傳”之句,以表達故國淪陷,哭笑不得之心。在經歷了十幾年佛教生涯后,朱耷又成了一所道院的開山鼻祖。面對不能改變的社會秩序,他選擇了在藝術上超脫,“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這便是人生的高級境界,法道自然,領悟整個自然中的順序、法則變化,順勢而行,了解自然世界的海納百川、包容之心。朱耷以道悟畫,以佛參禪,亦佛亦道地生活,“禪宗”與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共同被朱耷融入作品中,使其作品達到簡靜虛和,墨入傳神,意味深遠。
國破家亡,異族入侵,出世入佛,后入道教,生活環境的跌宕,精神上的挫折,心理上的“禪”“道”之變,使朱耷的繪畫藝術思想發生了質的改變。他把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之意通過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在書畫中通過夸張的藝術處理手法,用隱喻的表現形式來宣泄內心難以言喻的情感。他的諸多作品中以花鳥畫最為突出,并借助畫中“物”喻己,用特殊的象征手法來表達寓意,使畫面更富有個人情感色彩,與其說是畫面中的意境表達,不如說是作者本人情感升華的寄托[3]。
二、“怪誕之筆”
朱耷從小接觸了很多畫作真跡,從他的筆墨中我們可以看到董其昌、黃公望、倪瓚等大家的畫風,但朱耷并不是一味地師古,而是在學習各種前人畫法的基礎上,融入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創造具有獨特鮮明個性的藝術風格。朱耷的作品風格與其他描繪花鳥的寫意畫家不同,傳統花鳥畫追尋的是一種安逸、享樂的情景,而他筆下的萬物皆怪誕、放肆,仿佛漫不經心的幾筆卻勾勒出粗獷、不羈的形態,創造出以怪誕、丑拙美為主的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借此表現出自己內心的孤傲和對世俗的不滿。
朱耷的作品構圖奇異,筆墨雄健,枯枝冷葉,孤鳥癲狂,道不盡的凄涼、孤寂之情。他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花一枝、一魚一鳥盡顯怪誕奇異,這種獨特的繪畫風格使朱耷的畫作自成一派。他的作品構圖多采用“截枝式”,布局著眼于大意境,不遵傳統法度,看似信筆狂涂,實則胸有成竹。“白眼”是其一系列怪誕作品的點睛之筆,給畫面意境的表達帶來一種新的方式,如《魚鳥冊》中的鳥,寥寥幾筆把似鳥似魚的“鳥”刻畫得栩栩如生,鳥身魚尾的造型昂首挺立,“白眼”望天,偏于紙面一隅,盡顯倔強、輕蔑之意,略帶一絲無助的悲鳴之感,此時作者內心對世事的變故還未平靜,從畫中能表現出作者桀驁不馴的姿態與面對國破家亡的無助。
這種怪異的構圖不是隨意而為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借助荒謬、怪誕的繪畫方式比喻本身生活之窘迫,也不失為一種自嘲的表現。這些怪誕的造型就好比朱耷在社會歷史潮流中的跌宕起伏,始終無法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彰顯了作者內心的悲寂與失落,生動地表達了一個落寞皇室的真實生活困境。
三、“極簡之墨”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的思想觀念完整地映射了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留白”風格,在朱耷的作品中更是運用到了極致。他的作品大多數是用墨極簡,可謂“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他的畫不求精琢但求意到,這種畫風對中國傳統繪畫“大寫意”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作品一般都是以淡墨干筆為主,集各家之所長,融于本心之隨意,揮揮灑灑,意到而筆收,篆筆禿毫簡單扼要地皴出山巒、樹木、人物等主體,隨之稍加點綴,畫面用墨極少,但韻味不減。如其作品《荷花》,畫面大幅度留白,只用一線一面來表現一株清蓮出落于水中,在似與不似之間,意到情深,借蓮喻己,仿佛本人就像那一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在朝代變遷后仍保留本心,不隨波逐流,仍堅守血液中的那份傲氣。
不僅在布局上占有空間極簡,在用色上也極其單純。中國畫憑借著對水墨的極致處理,結合宣紙浸染的效果,將白紙黑墨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渲染出中國繪畫藝術的光輝歷史。朱耷更是把單色的處理用到了精湛的地步,在他留世的諸多作品中,幾乎全是黑與白的結合,水與墨的相融。就如他本人對社會的看法,非黑即白,他用黑白兩色填充了畫面內容,敘說著自己的經歷,借筆墨抒發出內心的凄苦、壓抑之情。
朱耷把一生動蕩坎坷的經歷融于思想之中,通過極簡的手法創造出一幅幅流芳百世的佳作。這種極簡主義的畫風是一種內心對事物理解的升華,每一筆在整體布局中都起到“四兩撥千斤”之力,再融入八大山人幾十年對“禪宗”“道家”思想的理解,每一幅作品都很好地體現出了作者的個人精神。朱耷通過極簡的構圖方式,大面積的留白,以有限的界面給人無限的遐想,因心造境,意味深遠。
結 語
歷史的變動對整個明朝是殘酷的事實,但卻給了朱耷一段生活中不可磨滅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歷練,特殊的人生經歷造就了朱耷筆墨藝術的獨特風格。作為一名藝術家,他把生活中的苦難,內心對前朝的留戀,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全部融合于本心,并融入作品中。正是憑借這獨特的藝術風格、空靈的畫面意境、隱喻的表達手法、精湛的畫技才使朱耷的作品在中國文學歷史的長河中備受推崇,深刻影響著后人,對無數畫家的創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