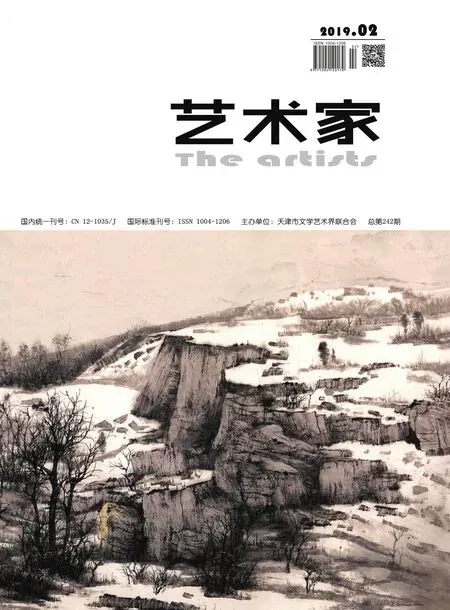從《金剛經(jīng)》看早期木刻線條的發(fā)展
□趙暘祉 沈陽大學(xué)
說起木刻版畫,不得不談到它的起源——印刷術(shù)。印刷術(shù)是我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之一,代表著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歷程。印刷主要包括圖像印刷與文字印刷兩部分,最早的木刻版畫就由圖像印刷發(fā)展而來。隨著印刷術(shù)被大眾廣泛了解與使用,我國古代的制版技術(shù)也隨之發(fā)展。我國歷史中,很早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甲骨、陶器、玉石、青銅等物體上的紋樣雕刻。制版技術(shù)在中國古代發(fā)展迅速,一度出現(xiàn)了十分貼近藝術(shù)版畫的印章藝術(shù),而印章藝術(shù)也被業(yè)內(nèi)人士與專家認(rèn)定為現(xiàn)代版畫的前身。到了唐代,印刷術(shù)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宋朱翌筆下的《猗覺寮雜記》(下卷)提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中國現(xiàn)存的最早寫明具體刊刻日期的印刷成品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于唐咸通九年在敦煌被發(fā)現(xiàn)。卷中精致細(xì)膩,扉頁中的木刻線條流暢自然,豐富完整。1907年被盜至英國,被大英國家圖書館收藏至今。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的內(nèi)容包括人物形象和經(jīng)文,其扉頁的物像被認(rèn)為是世界上有據(jù)可考的最早版畫形象之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刻本共6紙,每紙70余厘米,四周單邊單框,框高23.7厘米。首有凈口業(yè)真言、奉請八大金剛等前儀5行;尾有真言4行,題記1行,題記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經(jīng)文飄逸秀美,通篇唐楷風(fēng)格融匯其中,自成一格,墨色均勻。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早期木刻版畫的線條流暢洗練,細(xì)膩柔和。縱觀通篇可以看出,雕版印刷術(shù)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達到了相當(dāng)高的水準(zhǔn)。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的扉畫長約30厘米,左上方書“祗樹給孤獨園”字樣,畫面描繪的是釋迦牟尼在舍衛(wèi)國祗樹孤獨園向四弟子宣說《金剛經(jīng)》的場景,單線邊框。畫中,身著通肩式袈裟的釋迦牟尼至于畫面正中說法,護法金剛立于兩旁,畫面中還置有桌、蓋布、花氈、香爐等供養(yǎng)物品。釋迦牟尼兩側(cè)有四眾弟子16人,僧人均身著袈裟,其余均著華裝合十恭立,肅默聽法。
扉畫畫面構(gòu)圖設(shè)計巧妙,人物安排布局合理,人物面容安詳寧靜、生動自然,刀法技法結(jié)合完整細(xì)膩,畫面中線條圓潤流暢,通篇無瑕,走刀精準(zhǔn),已經(jīng)可以看出當(dāng)時木刻版畫技術(shù)十分成熟。第二張到第七張的《金剛經(jīng)》木刻文字展現(xiàn)了唐楷風(fēng)格,行云流水,一氣呵成,也為后代楷書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史料,成為里程碑式的存在,有“雕版印刷第一神品”之稱。
我國早期流傳的木刻版畫以宗教形式居多,內(nèi)容也多與宗教相關(guān)。這與當(dāng)時佛教興盛的社會大背景息息相關(guān)。但唐朝后期文化興盛交融,各民族經(jīng)濟往來密切,時代背景的改變使雕版印刷的內(nèi)容產(chǎn)生變化,佛教題材被世俗生活所替代,木刻版畫的運用范圍也更加廣泛。宋代伊始,印刷技術(shù)已經(jīng)被應(yīng)用至?xí)c插畫中,技法嫻熟,紙牌以及小型木版畫已與世俗生活聯(lián)系緊密,代表木刻版畫藝術(shù)開始重視與人們的精神世界形成聯(lián)系。
到了明清時期,版畫承襲前朝,推崇陽刻,木刻插圖中多用陽刻來表現(xiàn)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傳統(tǒng)版畫的線條運用在明代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在繼承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用線特色的同時,將其提升至一個更高的層次。雖然版畫線條仍然受到器具的限制,但已形成別具特色的形式美。明末清初,神話故事是版畫的主要題材,其中較為突出的人物是陳老蓮。陳老蓮的《九歌圖》用線較散,但筆法細(xì)圓,方折分明,每處下筆都有經(jīng)過思考刻意為之的痕跡。《九歌圖》總共有十一幅,依次為東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皆為楚國神話中的人物,每個形象都飽滿各異,神采奕奕,極富生命力。著名的《西廂記》中的仕女造型也是刻法精妙,造型豐富多彩,線條細(xì)膩,豐潤傳神,唐韻猶存。其中最妙的屬鶯鶯像,在含羞中又感憂郁,寧靜又端麗,十分出彩。陳老蓮的木刻版畫不僅在當(dāng)時博彩出挑,更對后來清代的木刻版畫藝術(shù)帶來極大影響。清代的木刻版畫名家劉源和任熊正是因為受到陳老蓮的作品影響才創(chuàng)作了《凌煙閣功臣錄-自序》和《劍俠傳》等精彩作品。清代更是涌現(xiàn)出一批十分令人驚贊的版畫藝術(shù)作品。由改琦所繪刻的《紅樓夢圖詠》不僅承襲了明代筆法的精湛和傳神,在風(fēng)格上更加清淡格雅,其中100多個人物,一人一圖,線條娟秀而流暢,十分別致。
明清版畫插圖中的“線”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水墨線條與刀、木本身的結(jié)合效果,不但能讓人感受到筆法的鋒挺、骨法的剛勁,更有刀法的技韻以及木痕本身的自然淳樸。這一時期的“線”更注重裝飾性質(zhì),對于人物的刻畫也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強調(diào)線條本身與人物形態(tài)特征和神情充分地結(jié)合。線條在這一時期也有了更為豐富、嚴(yán)謹(jǐn)?shù)谋磉_。如在木刻插圖中,表現(xiàn)人物的線條多為細(xì)致柔韌的曲線,表現(xiàn)山水的線條多為筆觸強硬的粗線,表現(xiàn)亭臺樓閣的線條則多為精細(xì)工整的排線。而這一時期在畫面上提倡以線表示面,更加注重線條的疏密有致,使其作品富有節(jié)奏韻律。
雖然中國明清時期的版畫形式未能從文學(xué)插圖的形式中脫離出來,沒有真正形成獨立的版畫藝術(shù)類別,但是仍然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寫下了燦爛輝煌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