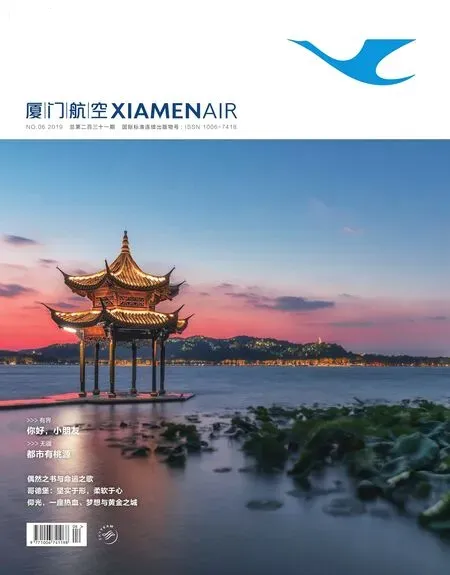給孩子們的詩
編輯_來
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詩意的。
尼爾·波茲曼在他那本高唱時代挽歌的《娛樂至死》書中,預示文化的兩種結局:“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波茲曼不無焦慮地警示,“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目前看這樣的警示正在成為現實。
在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商業化娛樂化時代,當下一代到來時,我們將雙手捧出什么來迎接他們?或許你可以給他們一首詩,就像是取自他們身體中的部分一樣。這世上最適合孩童的文字我想應該是詩歌了;詩歌最好的吟唱者應該也是孩童吧。
詩歌音樂節奏的韻律,音符般跳躍,在孩子的世界里會如七彩的珠子引領他們探究奧秘森林。他們的純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的靈動也是躍然于神的。英國18世紀的天才詩人威廉·布萊克有一本詩集叫《天真與經驗之歌》,天真和深刻怎樣定義?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跟文本完全脫節的天真,也沒有完全抽象出來的深刻。我總以為孩子多少都是淺薄的,但他們的深刻卻偶爾如箭擊中我。比如一個八歲孩童的《原諒》,令我只想原諒自己的平庸。
《原諒》
鐵頭
春天來了
我去小溪邊砸冰
把春天砸得頭破血流
直淌眼淚
到了花開的時候
它就把那些事兒忘了
真正原諒了我
即便是成人,也必要一種如赤子的心情才能領略其中奧義。無論是沉重,灰暗還是悲痛。詩是絕望的吶喊與希望的喃語,孩童的心是那能燒破黑暗的火光。
這一百年來,愿為孩子寫詩,想為孩子寫詩的作家,或許多少都如魯迅先生曾經說的那樣“肩著黑暗的閘門”是想將把更多的年輕人送往光明的地方去。當世界光亮,人生的艱難還是難以回避。當代詩人北島早前花費三年時間為孩童編著了一本《給孩子們的詩》,起因正是看到兒子在學校參加朗誦節時背誦了一首粗劣不堪的詩歌,深感“壞的語言”足以傷害孩子們的想象空間。“在人生艱難的路上,他或許會被詩歌之光照亮,讓他醒來。”詩歌是最容易走進孩童內心的語言,是最深情的注視,和最真切的禮物,“我希望,我們每個孩子都是幸運的”。
讓他們小小的身軀行在我們當中,如一線鎮定而純潔之光。因為讓我們愛他們,我們因此彼此相愛。
《一束》
北島
在我和世界之間
你是海灣,是帆
是纜繩忠實的兩端
你是噴泉,是風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間
你是畫框,是窗口
是開滿野花的田園
你是呼吸,是床頭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
在我和世界之間
你是日歷,是羅盤
是暗中滑行的光線
你是履歷,是書簽
是寫在最后的序言
在我和世界之間
你是紗幕,是霧
是映入夢中的燈盞
你是口笛,是無言之歌
是石雕低垂的眼簾
在我和世界之間
你是鴻溝,是池沼
是正在下陷的深淵
你是柵欄,是墻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