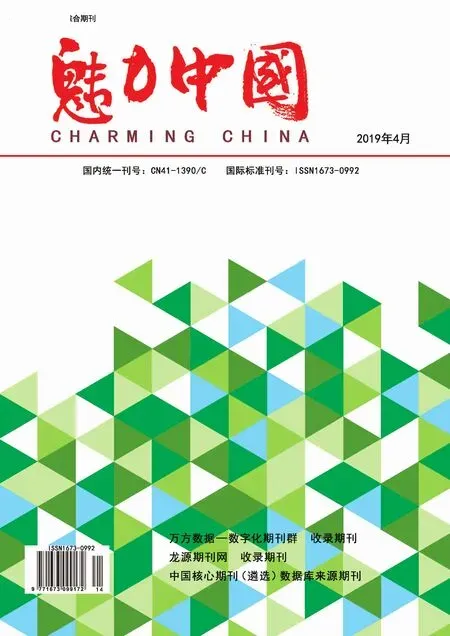梅堯臣詩歌藝術特色例析
康玉琨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學,福建 泉州 362600)
被譽為宋詩“開山祖師”的梅堯臣無論在創作實踐還是創作主張上都對宋詩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藝術上,他特別注重詩歌形象、含蓄等特點,提出了狀難寫之景如在眼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引)這一著名的藝術標準。錢鐘書稱他:“主張‘平淡’,在當時有極高的聲望,起極大的影響。”梅堯臣作詩追求“苦硬”、“瘦勁”,喜歡平淡的風格,其實是要求平淡其表、深邃其里,內核“深遠”,淡而屢深。梅詩的“平淡”具備這樣的特點:構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遠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語句平淡;寓奇峭于樸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修辭的運用尤其獨具匠心,平中見奇。今以其《送門人歐陽秀才游江西》為例試做分析。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
又隨落花飛,去作西江夢。
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
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
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這是一首送別詩,作于1059年(嘉祐四年),作者時年五十八歲,在汴京(今河南開封)任國子監直講,奉命編修《唐書》。歐陽秀才名歐陽辟,字晦夫,桂州靈川(今屬廣西)人,據蘇軾跋此詩語,他此時二十五歲(見《東坡題跋》),曾和弟歐陽簡從梅堯臣學詩。“秀才”本指才能優異的人,漢代以來曾作為薦舉人員的科目之一,唐初設有“秀才”科,后廢去。這里用作讀書應舉的士人的泛稱。
一提到送別詩,我們很容易想到唐朝詩人王勃的名句“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不過,梅堯臣的這首五言古詩卻別具特色,因其是老師送別學生且寄語殷殷而在宋詩中獨樹一幟。
全詩分作兩節。前四句先從對方著筆,寫學生歐陽秀才即將啟程出游。詩中用了兩個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歐陽秀才。春風一吹,草木都開始萌芽,歐陽秀才心中也像草木發芽一樣,產生了出游的愿望。“忽與春風動”點出時間。“忽”字、“動”字下得特別精當。春天的花草樹木,往往頭一天看還光禿禿的,第二天卻忽然綻出棵棵新芽來了。“動”字不僅是說萌芽的發生,還指它在春風吹拂下不斷成長;它一經萌芽,不久就要長出枝葉,開出鮮花。出游的念頭也是如此,它一經產生,就不斷滋長,變得愈來愈強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隨”二字緊接轉入下文。由蔭芽而開花,花又被風吹落,飛向天空,歐陽秀才的心,又像落花似的,飛向西江。“西江”指大江(長江)下游西段,也就是題中的“江西”。古典詩詞寫落花,常常帶著感傷的情調,此詩寫其飛舉飄揚,卻充滿生機。“西江夢”指想象中即將開始的江西游歷生活。夢境是變幻莫測、飄忽無定的;既可以夢見過去,也可以夢見未來。用“夢”形容游歷生活,可以引起無窮聯想:使人聯想到歐陽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蹤不定,生活的豐富多彩、難以預測,使人聯想到他醒里夢里對此日客居京中這段生活——包括作者這次送別在內——的回憶;既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也包含著對過去的深長懷念,情致綿邈,意味無窮,造語之妙,已臻極致。這四句比喻新穎貼切,把歐陽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變成生動的形象描繪,可見作者的才思和藝術創造力。
下面六句轉到作者方面,正面寫送別,仍然全用比喻。鳳凰是傳說中的神鳥,據說它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天下安寧,它才出現。詩中用它比喻歐陽秀才,是說他才華出眾,非常人可比,表達了作者對他的贊賞,同時也是希望他以后能為朝廷建功立業。“家無梧桐”既是詩人自謙,也是對學生的勉勵,愿他振翅高飛,奮力進取。學生即將遠行,作老師的對他將來的一切非常關心,下面兩句就是對他的諄諄囑咐。桂林指桂樹林,傳說桂樹林是鳳凰棲集之處。《天地運度經》說:“泰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鳴集于此。”劉向《九嘆》:“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鸮。”鸞為鳳屬。舊說烏能反哺。晉代束皙《補亡詩·南陔》:“嗷嗷林烏,受哺于子。”此詩即以“烏哺”指烏鴉,是凡鳥,借喻平庸之輩。屈原《楚辭·涉江》:“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比喻賢士遠離,小人竊位,可見鳳凰烏鴉,品類不同,不能共處。此詩“鳳巢”兩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歐陽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擇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處和往來;同時也是獎譽歐陽秀才,說他今后前程遠大,絕非“烏哺”輩所能相比。這是作者的臨別贈言。結尾緊接“桂林”,舉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補足送別之意。《晉書·郤詵傳》:“累遷雍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稱科舉及第為“折桂”。“無忘桂枝榮”,就是要歐陽秀才不要放棄科舉;舉酒相送既是送別,也是祝愿他異日科舉及第,不負所學,施展平生的抱負。在科舉時代,一般讀書人要躋身仕列,只有應試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結,鄭重叮嚀,表達了對學生的殷切期待。據《宋詩紀事》記載,在這次送別后的三十二年,歐陽辟中了1091年(元祐六年)進士,沒有辜負老師的希望。1100年(元符三年),蘇軾南遷過合浦(今屬廣東),見到歐陽辟,歐陽辟將珍藏的梅堯臣送他的這首詩給蘇軾看。蘇軾和歐陽辟同出于梅堯臣之門,并受知遇之恩。所以蘇軾見此詩后,還寫了一段很有情意的跋語。
古代詩歌運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這首十句的五言古詩,通篇從頭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卻不多見。這正是此詩藝術上的成功之處。比喻可以使詩含蓄蘊藉,更富形象性,并增添詩情畫意。歐陽修稱“圣俞(堯臣字)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見《六一詩話》)。全篇絕無華麗秾艷語,精致細密,韻味悠長,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