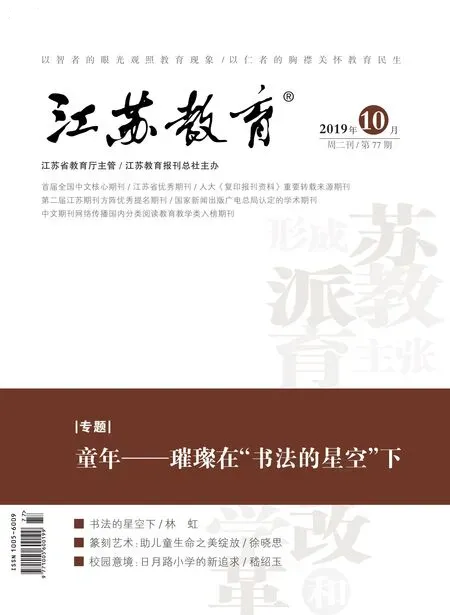法 意(二)
閆 帥
經(jīng)過前面的幾次討論,我們對(duì)書法中的“法”與“意”有了更加具體、深入的認(rèn)識(shí)與理解。可以這樣說,書法中的“法”與“意”不僅是我們進(jìn)行的一種抽象層面的理論概括,也不僅是由書法的點(diǎn)畫形象、識(shí)讀形象、人格形象以及韻律形象所傳所達(dá),而且甚至成了一種客觀性的存在。這是一種文化存在的客觀性,書法中的“法”與“意”早已深深積淀于古往今來的字體、書體當(dāng)中,積淀于世世代代吾土吾民的書法觀念當(dāng)中。故當(dāng)我們以此種書法觀念來審視字體、書體時(shí),便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一般與具體兩個(gè)不同層面的“法”與“意”。
首先來看字體、書體中存在著的一般層面的“法”與“意”。
文字是書法的物質(zhì)載體,脫離文字,書法便不復(fù)存在。文字并非是一種虛幻的存在,它實(shí)實(shí)在在地以各種字體、書體形式來呈現(xiàn)。因此,與其說書法的“法”與“意”存在于文字當(dāng)中,毋寧說存在于各種現(xiàn)實(shí)的字體、書體當(dāng)中。撇開具體的歷史時(shí)代或個(gè)體,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字體、書體本身存在著最基本的“法”與“意”,它們構(gòu)成了字體、書體最基本的規(guī)定。唐代孫過庭《書譜》有云:“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jì)成厥美,各有所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wù)檢而便。”即是說不同字體、書體具有不同的形質(zhì)特征以及不同的意態(tài)傳達(dá);在書法的篆、隸、真字體以及各自的楷、行、草書體中,有著各自不同的“法”與“意”。
篆體作為字體中最古老的形態(tài),由于其保留了胎息于圖形文字的某種象形性,因此,從書法的識(shí)讀形象層面看,我們透過篆體的字形(能指)可以追尋其義(所指),亦即在篆體中,“法”(形)與“意”(義)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原始對(duì)應(yīng)。但是,這種識(shí)讀形象層面的形義關(guān)系并非篆體之“法”與“意”的主要指向;篆體的點(diǎn)畫形象、韻律形象的“法”與“意”,才更具有書法的意義,是我們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篆體以相對(duì)單一的點(diǎn)畫來組合較為復(fù)雜的圖案,其用筆可以“一法”來概括;且其點(diǎn)畫粗細(xì)變化最不明顯,書寫韻律最為平和安穩(wěn),因此,篆體的點(diǎn)畫、韻律之“法”蘊(yùn)涵著原始古樸、神秘不測(cè)、畢恭畢敬等“意”。不同于篆體,隸體更趨向于一種抽象的表意符號(hào),遠(yuǎn)離了象形文字及其原始的形義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被視作今體文字的開始。從點(diǎn)畫形象來看,隸體在筆法上出現(xiàn)了“波磔”“掠筆”,增加了隸體點(diǎn)畫的豐富表現(xiàn)力,其結(jié)體的平直橫勢(shì)也較篆體更為簡便;而從書寫韻律上來說,隸體則出現(xiàn)了明顯的輕重緩急的韻律節(jié)奏。其“法”的改變必然引發(fā)“意”的更新,隸體在質(zhì)樸之上增加了雍容的華麗與鋪陳的威儀。當(dāng)字體發(fā)展到真體時(shí),“法”與“意”又是一變。從識(shí)讀層面來講,真體同隸體相仿,都是作為一種抽象的符號(hào)而存在。而從點(diǎn)畫、韻律形象來講,真體的“法”最為復(fù)雜,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一方面,真體形成了一套復(fù)雜的點(diǎn)畫系統(tǒng),即所謂“八法”(側(cè)、勒、弩、趯、策、掠、啄、磔);另一方面,真體有著相對(duì)穩(wěn)定的書寫次序(筆順),它們既造成了真體長短粗細(xì)、起收轉(zhuǎn)折等的復(fù)雜變化,也決定了用筆輕重緩急的豐富韻律。
不僅不同字體有著不同的“法”與“意”,在同一字體的不同書體當(dāng)中,又表現(xiàn)出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法”與“意”。作為各種字體的楷體(正體),從“法”的一面來講,強(qiáng)調(diào)點(diǎn)畫規(guī)范,韻律節(jié)奏平穩(wěn),因此呈現(xiàn)出一種“靜態(tài)”之“敬意”;作為各種字體的行草體,從“法”的一面來講,點(diǎn)畫靈活且變化豐富,運(yùn)筆迅捷且節(jié)奏分明,多表現(xiàn)出一種“動(dòng)態(tài)”的“率意”。因此,從書法史的發(fā)展來看,在歷朝歷代官方的、正式的書寫中,諸如祭祀、記功、封禪、墓志、詔書等方面,多選擇字體的楷體形態(tài),這些楷體莫不是法度嚴(yán)謹(jǐn)、點(diǎn)畫分明、結(jié)體規(guī)范,以凸顯崇敬、莊重、靜穆之意;而那些非正式的,人們?nèi)粘鴮懙暮啝⑹衷噙x擇字體的行草體,這些行草體莫不是書寫簡便,表露出一種自由、率意。因此,從一般層面來看,書法中的字體、書體有其自身相對(duì)穩(wěn)定的“法”與“意”,這是任何歷史時(shí)期字體、書體所共同具有的,它們構(gòu)成了不同字體、書體最基本的規(guī)定。
其次來看字體、書體中存在著的具體層面的“法”與“意”。
從書法歷史的發(fā)展來看,字體、書體的“法”與“意”并非一成不變,它們?cè)诓煌瑲v史時(shí)期乃至不同個(gè)體手中有著更為具體的表現(xiàn),這造成了字體、書體“法”與“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這個(gè)問題。
其一,由于不同歷史時(shí)期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的差異,導(dǎo)致了字體、書體在遵循基本“法”與“意”的基礎(chǔ)上,呈現(xiàn)出有時(shí)代特征的“法”與“意”。因此,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字體、書體表現(xiàn)的“法”與“意”是不同的。例如,就篆體而言,殷商時(shí)期甲骨文的虔誠神秘,商周時(shí)期金文大篆的禮儀秩序,秦代李斯小篆的嚴(yán)謹(jǐn)規(guī)范,唐代李陽冰小篆的清麗典雅,清代鄧石如篆書的剛勁婀娜,都是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篆體之“法”與“意”的具體表現(xiàn)。又如,就真體而言,漢末鐘繇真體楷書的質(zhì)樸,東晉王羲之真體楷書的精巧,北魏真體楷書的奇逸,唐代真體楷書的謹(jǐn)嚴(yán),清代碑派書家真體楷書的雄強(qiáng),又都是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真體之“法”與“意”的具體表現(xiàn)。
其二,由于同一時(shí)期不同書家的性情、趣尚、取法諸方面的差異(這里主要是指那些杰出的、在書法史上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書家),導(dǎo)致了字體、書體在遵循基本“法”與“意”的基礎(chǔ)上,呈現(xiàn)出有個(gè)體特征的“法”與“意”。例如,就隸體而言,東漢時(shí)期隸書碑刻幾乎是一塊碑就有一種“法”與“意”;而清代中期以來金農(nóng)、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等書家的隸書也幾乎是一個(gè)人就有一種“法”與“意”。又如,就草書而言,無論是在哪一個(gè)歷史時(shí)期、哪一種字體當(dāng)中,幾乎每一位草書家都有自己的“法”與“意”,甚至同一位草書家的不同作品也都有其獨(dú)特的“法”與“意”——它們具體表現(xiàn)在書法史上眾多的優(yōu)秀書法作品當(dāng)中。
綜上所述,一方面,字體、書體的一般層面的“法”與“意”有其相對(duì)獨(dú)立的意義,即作為漢字演進(jìn)的古體、近體與今體,篆、隸、真三字體及其正、草書體有其特定的歷史排序,因而它們各自的“法”與“意”也存在著先后承替、各成體系的關(guān)系;即使是在字體、書體演進(jìn)完成之后,各種字體及其書體并存的情況下,吾人仍然保存著對(duì)其一般層面“法”與“意”的經(jīng)驗(yàn);另一方面,字體、書體一般層面的“法”與“意”又總是體現(xiàn)在具體層面的“法”與“意”之中,即不同歷史時(shí)期、不同個(gè)體所書寫的字體、書體之具體層面的“法”與“意”,共同構(gòu)成了字體、書體完整意義上的“法”與“意”。換言之,字體、書體的“法”與“意”是由不同歷史時(shí)期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所共同組成的,是一個(gè)形式多樣、意涵豐富、兩兩對(duì)應(yīng)的書法藝術(shù)語言體系,并且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這個(gè)獨(dú)特的語言體系應(yīng)當(dāng)不斷豐富。
認(rèn)清這一點(diǎn),對(duì)于現(xiàn)今的書法藝術(shù)創(chuàng)作至關(guān)重要。書法是藝術(shù),而絕不僅僅是一種書寫技術(shù);書法家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就絕不僅僅是在賣弄“法”,而是要運(yùn)用最合適的“法”來表現(xiàn)自己所欲表現(xiàn)的“意”。書法家進(jìn)行書法創(chuàng)作時(shí),絕非是簡單地書寫規(guī)范的文字,而是有選擇地去依托特定的字體、書體;而當(dāng)確定了字體、書體之后,書法家又會(huì)受到不同字體、書體“法”與“意”的規(guī)定,并以此為基礎(chǔ)進(jìn)行不斷調(diào)試,從而塑造出自己獨(dú)特的“法”與“意”。因此,具有不同的“法”與“意”的字體、書體便成了書法家創(chuàng)作的必備素材。這就是說,書法家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是明了篆、隸、真三字體及其楷、行、草三書體的“法”與“意”兩個(gè)層面的含義,即不僅要深入體認(rèn)各種字體、書體一般層面的“法”與“意”的表現(xiàn)規(guī)律,對(duì)書法史上優(yōu)秀作品的具體層面的“法”與“意”表現(xiàn)也要爛熟于胸。在此前提下,書法家才能夠依據(jù)自己所欲表現(xiàn)先在一般層面上選擇相宜的字體、書體大類,進(jìn)而綜合歷代優(yōu)秀書法作品“法”與“意”的具體表現(xiàn),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法”與“意”。
當(dāng)然,在進(jìn)一步討論這個(gè)問題之前,我們還需要明白,由于書法自身發(fā)展存在著多種歷史形態(tài),造成了不同歷史時(shí)期,書法家對(duì)字體、書體的選擇有著不同的原則與要求,因此,我們還必須透過書法的種種歷史形態(tài),來進(jìn)一步把握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書法家選擇字體、書體的緣由。
在實(shí)用書法階段,書寫者立足實(shí)用立場(chǎng),遵循美觀、便利等原則,去選取相應(yīng)的字體、書體以適應(yīng)不同場(chǎng)合的書寫。即在具體的書寫中,如果是官方正式場(chǎng)合,那就不會(huì)選擇草率簡便的行草體;如果是急務(wù)纏身,大概很難會(huì)選擇一筆不茍的楷體。因此,在實(shí)用書法階段,書寫者在進(jìn)行書寫時(shí),會(huì)充分考慮書寫用途,從而選擇合適的字體、書體——這是實(shí)用書法形態(tài)對(duì)字體、書體之“法”與“意”選擇的基本準(zhǔn)則。
到了藝用書法階段,對(duì)字體、書體的選擇,則是基于實(shí)用與審美相統(tǒng)一的立場(chǎng),即一方面要考慮實(shí)用性;另一方面則要考慮個(gè)人的審美趣味。具體來說,這一時(shí)期的書法家,一方面會(huì)考慮到不同字體、書體最基本的“法”與“意”,以適應(yīng)不同書寫場(chǎng)合的需要;另一方面,會(huì)根據(jù)自己的審美趣味,有選擇地去取法、借鑒前代優(yōu)秀的書法家所塑造的“法”與“意”,并在此基礎(chǔ)上,融合構(gòu)建人格形象層面上的自己的“法”與“意”。
現(xiàn)今,書法已經(jīng)步入美術(shù)書法形態(tài),書法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由于書法家藝術(shù)本位精神的覺醒,對(duì)字體、書體選擇的主動(dòng)性,更是由于在經(jīng)歷了長期的歷史發(fā)展,字體、書體“法”與“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以此造成了書法家選擇的多元化。此時(shí)書法家對(duì)字體、書體的選擇,立足藝術(shù)立場(chǎng),建立在書法形象的構(gòu)思基礎(chǔ)之上——以識(shí)讀形象為言說,以點(diǎn)畫形象為骨肉,以韻律形象為行動(dòng),以人格形象為靈魂。因此,書法家在對(duì)書體、字體的選擇時(shí),又會(huì)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書法家會(huì)首先考慮書法的識(shí)讀形象,書寫文辭與字體、書體之“法”與“意”的匹配性;繼而在點(diǎn)畫形象與韻律形象的塑造上相互配合,曲盡具體的“法”與“意”的表現(xiàn);最終會(huì)充分考慮字體、書體“法”與“意”與自己人格精神的一致性,充分考慮點(diǎn)畫、韻律形象“法”與“意”與自己人格精神的整體性,從而通過書法形象充分展現(xiàn)自己的人格形象。即書法家通過體察不同字體、書體中所透露出的“法”與“意”,以其獨(dú)特的人格精神來統(tǒng)籌書法創(chuàng)作的識(shí)讀、點(diǎn)畫、韻律形象的“法”與“意”表現(xiàn),由此完成作品對(duì)人格形象的塑造。
可以這樣說,書法家在對(duì)古代字體、書體的考察與選擇過程,不僅是調(diào)用自己全面的書法藝術(shù)修養(yǎng)與才能的過程,也是一步步在認(rèn)清自己、追求本我的過程。如果選擇了與自身人格精神相匹配的字體、書體,那么就會(huì)容易在書法中表現(xiàn)本真、展現(xiàn)本色。這就如同運(yùn)動(dòng)員選擇到合適的鞋子,如此才能健步如飛、沖刺終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