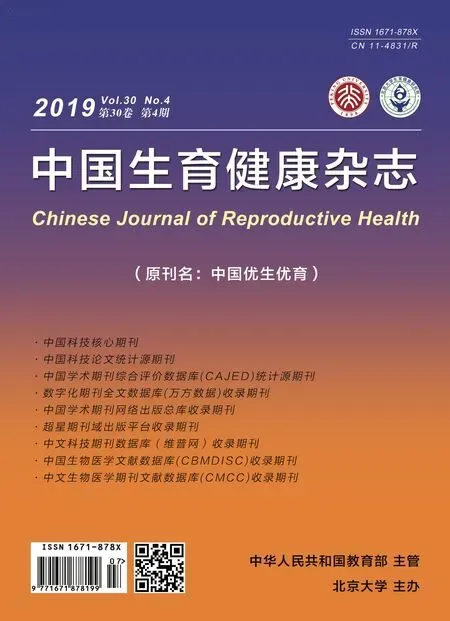自噬調節基因AMBRA1在神經管發育中的作用及機制研究進展
秦佳星 牛勃 王建華
一、神經管畸形
神經系統的發生起源于神經外胚層,由神經管和神經嵴分化而成。人胚第3周初,在脊索突和脊索的誘導下,出現了由神經外胚層構成的神經板。隨著脊索的延長,神經板也逐漸延長并形成神經溝。神經溝逐漸向頭、尾兩端閉合成神經管,并在頭、尾兩端形成前神經孔和后神經孔。胚胎第25天左右,前神經孔閉合;第27天左右,后神經孔閉合,完整的神經管形成。之后神經管的前段發育為腦,后段發育為脊髓[1]。基因缺陷和/或環境因素均可能造成神經管閉合障礙,從而導致神經管畸形(neural tube defects,NTDs)[2,3],包括無腦畸形(常伴有顱頂骨發育不全,稱露腦)、腦膨出、脊柱裂等[1],發病率為0.05%~1%,可造成孕婦流產、圍產兒和嬰兒死亡或終身殘疾,危害極大,給患者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與精神負擔。NTDs的發病差異可能是由不同的風險因素導致,如營養狀況、肥胖、糖尿病、葉酸補充、環境毒物以及不同種群中的遺傳易感性[4]。總體而言,盡管研究已經確定了許多危險因素,但這些因素在NTDs發生過程中的確切機制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明確NTDs發生機制,做到早期預防很重要。大量研究發現,自噬在神經管畸形發生過程中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
二、細胞自噬
1.細胞自噬簡介:自噬是真核細胞內通過一雙層膜細胞器結構進行自我消化、自我清除和獲得營養的復雜過程,使細胞在饑餓、氧化應激等狀態下能存活下來。這一過程受到一系列自噬相關蛋白(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s,Atg蛋白)的調控[5-7],可以是選擇性地去除細胞中有害或不必要的物質,也可以是非選擇性的[8]。自噬過程異常與神經變性[9]、癌癥[10]、衰老[11]和感染[12]等疾病關系密切。
哺乳動物細胞中存在3種自噬途徑:巨自噬(macroautophagy)、微自噬(microautophagy)和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chaperonr-mediated autophagy,CMA)[13,14]。巨自噬是真核細胞中通過起源于內質網的雙層膜結構形成的自噬體,包被蛋白質聚集體、損傷或衰老的線粒體和過氧化物酶體等,并將其轉運到溶酶體進行消化降解[15]。微自噬是溶酶體膜包裹胞質成分后內陷,進行消化降解,沒有形成自噬體[16]。CMA則是依靠特定的受體與靶向基序的特異性識別,對胞質內容物進行選擇性運輸降解,運輸過程中不形成中間囊泡或進行膜融合[6,17]。
2.細胞自噬分子機制:細胞自噬核心成分主要由4種大分子物質組成,即Unc-51樣自噬激活激酶1(unc-51 like autophagy activating kinase 1,ULK1)復合物、III類磷脂酰肌醇3-激酶(class III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III)復合物、泛素化修飾系統及跨膜蛋白[15]。ULK1復合物由ULK1、自噬相關蛋白13(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13,Atg13)、分子量大小為200 kD的黏著斑激酶家族相互作用蛋白(FAK family interacting protein of 200 kDa,FIP200)和Atg101組成,受調控分子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復合物1(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mTORC1)調節[16,18-19]。PI3KIII 復合物由Vps34、Beclin1、Vps15、Atg14組成,通過產生磷脂酰肌醇-3-磷酸(phosphatidylinositol 3 phosphate,PI3P)來啟動自噬體的形成[20]。泛素化修飾系統包括Atg5-Atg12-Atg16連接系統和微管相關蛋白1輕鏈3(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LC3)連接系統,作用于隔離膜的延長和自噬泡的形成。跨膜蛋白Atg9可通過影響膜泡運輸調控自噬[20-21]。
營養條件充足,自噬未啟動時,mTORC1通過磷酸化ULK1和Atg13使ULK1復合物失活,AMP依賴的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mTORC1-ULK1信號通路下傳中斷,從而阻斷自噬。當營養物質缺乏時,細胞內誘導磷酸酶形成,將mTORC1去磷酸化使其失活,對ULK1和Atg13磷酸化作用終止,使得ULK1和Atg13去磷酸化,促使ULK1復合物的激活[20]。激活的ULK1復合物磷酸化Beclin1和自噬/芐氯素1調節因子1(activating molecule in BECN1-regulated autophagy protein 1,Ambra1),Ambra1促進Beclin1和Vps34的相互作用,使PI3KIII 復合物形成和活化[14,22]。此外,活化的ULK1介導PI3KIII 復合物運輸至內質網(endoplasmic reticulum,ER),其中Vps34催化磷脂酰肌醇(phosphatidylinositol,PI)轉化為PI3P,募集自噬體形成所需的特定自噬蛋白,促使杯狀雙層膜結構的自噬前體形成[16]。隨后,自噬前體延伸包裹待降解底物,形成完全閉合的自噬泡。自噬泡通過Atg9系統運輸達到溶酶體,其外膜最終與溶酶體膜融合形成自噬溶酶體。最后,自噬溶酶體的內容物被溶酶體水解酶消化[16,21]。
3.細胞自噬與NTDs:自噬是一種很強的分解代謝過程,是胚胎發育過程中快速的細胞重構所必須的,可以通過環境和激素刺激誘導發生。基礎水平的自噬可以降解受損的細胞器和長壽蛋白質;相反,過度活躍的自噬可能干擾細胞的生理過程,甚至導致細胞死亡,干擾正常的胚胎發生[23]。Fimia 等[8]發現哺乳動物神經系統發育需要自噬,細胞生長和細胞死亡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當自噬損傷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將導致NTDs的發生。Wang等[24]的研究發現,通過敲除編碼自噬負調控的Prkcα基因,可以逆轉糖尿病誘導的細胞自噬損傷和細胞凋亡,導致NTDs減少。許多研究表明,自噬相關基因AMBRA1缺失導致大量的神經上皮細胞凋亡和NTDs的形成[13,15,22-25]。
三、 AMBRA1基因與NTDs
1.AMBRA1基因結構及功能:AMBRA1基因編碼Ambra1蛋白。人類AMBRA1基因位于11p11.2染色體上,包含23個外顯子,編碼的蛋白質分子量為142 kDa,包含1 298個氨基酸殘基。小鼠Ambra1基因位于2號染色體上,包含19個外顯子,編碼的蛋白質分子量為143 kDa,包含1 300個氨基酸殘基。Ambra1蛋白是脊椎動物細胞中一種保守的蛋白質,存在于細胞骨架、線粒體、細胞質、細胞核、溶酶體及內質網中,參與神經元發育期間自噬調控蛋白轉運以及細胞生存與增殖的調控。該蛋白質在N端區有一個特征性的WD40結構域可以通過為大分子復合物的組裝提供空間,介導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肽和蛋白質-DNA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參與不同的細胞功能(包括信號轉導,細胞分裂和RNA加工)。這種特征可能使Ambra1在自噬的復雜相互作用網絡以及自噬與其他途徑之間廣泛的相互作用中起到重要作用[26]。
2.AMBRA1基因與NTDs:小鼠胚胎中Ambra1缺陷會導致胚胎發育早期自噬損傷,細胞增殖過度,隨后細胞凋亡增加和泛素化蛋白在神經上皮中積聚,導致嚴重的NTDs[8]。Ambra1缺陷導致小鼠在胚胎發育10.5天(embryonic day 10.5,E10.5)到胚胎發育13.5天(E13.5)之間出現露腦畸形和脊柱裂,胚胎發育16.5天(E16.5)胚胎致死[8]。類似地,在斑馬魚中,抑制ambra1a和ambra1b會導致嚴重胚胎畸形及相關的不完全發育。受精后2天(2 days post-fertilization,2dpf),呈現廣泛的中腦和后腦室腦積水,并產生異常頭部和較小的眼睛。在3dpf時,表型進一步惡化,最終導致ambra1a敲除動物心臟水腫和胚胎死亡,ambra1b敲除動物在4dpf死亡[27]。因此,Ambra1在細胞自噬、凋亡、增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中樞神經系統發育過程中控制細胞增殖和細胞存活的必需蛋白質。AMBRA1基因突變可導致NTDs[13,15,22-23]。
在營養豐富的條件下,細胞自噬過程被抑制,mTORC1除了通過直接磷酸化ULK1對自噬進行負調控,還可以通過結合并磷酸化Ambra1抑制ULK1的泛素化,阻止ULK1的自我結合,降低ULK1的穩定性和活性,從而對自噬通路進行微調[28]。此外,在人成纖維細胞2FTGH中Ambra1還與Beclin-1和PI3KIII一起與動力蛋白復合物的動力蛋白輕鏈(dynein light chains,DLC)結合,阻止PI3KIII復合物移動至ER,導致自噬前體無法形成,抑制細胞自噬[26]。當營養條件缺乏,誘導細胞自噬發生時,mTORC1活性受到抑制,Ambra1激活促進ULK1的泛素化,增強了ULK1的自我結合,使其活性與穩定性進一步提高[15]。激活的ULK1又磷酸化與Beclin-1、PI3KIII和DLC結合的Ambra1,使Ambra1從動力蛋白復合物中釋放,促進了Beclin-1和Vps34的相互作用,并介導PI3KIII復合物轉運至ER,促進自噬體的形成,形成一正反饋調節通路[26]。
Antonioli 等[29]發現,在人成纖維細胞2FTGH的自噬反應過程中,Ambra1的穩定性還可被泛素/蛋白酶系統調節;磷酸化的Ambra1使Cullin-4與Ambra1解離,導致Cullin-4通過損傷特異性DNA 結合蛋白1(damage- specific DNA binding protein 1,DDB1)介導的Ambra1降解作用被終止;釋放的Ambra1又可以通過結合ElonginB抑制Cullin-5活性,減少Cullin-5對mTOR抑制劑DEPTOR的降解而使DEPTOR含量增加,增強對mTOR活性的抑制,促進細胞自噬。
Ambra1還在線粒體自噬調節中起作用。當線粒體損傷,線粒體膜電位下降明顯增加了Parkin與Ambra1的相互作用,Ambra1以Parkin依賴的方式被募集到去極化線粒體周圍,激活PI3KIII復合物并促進其通過自噬途徑清除[22]。此外,Ambra1-LC3相互作用可以將受損的線粒體轉運到自噬體,對放大Parkin介導的線粒體清除是至關重要的[30]。
四、展望
AMBRA1基因通過其編碼的蛋白質調節自噬過程,自噬對胚胎神經發育至關重要。目前發現AMBRA1基因突變與神經管發育密切相關,并已經確定Ambra1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對自噬進行調控,但仍有一些調節過程機制不清。隨著生命科學的發展,Ambra1在神經管畸形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將有可能被逐一闡明,這將有利于NTDs的防控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