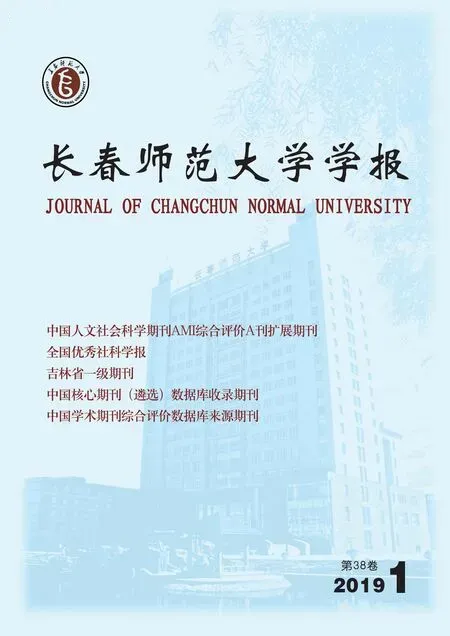功能性支配視角下聚眾斗毆罪論析
——從積極參加者入手
辛旭東,周高贊
(東北林業大學 文法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我國《刑法》第292條規定的聚眾斗毆罪處罰的主體僅限于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由于《刑法》對首要分子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實務和理論界對這一主體的認識是相同的。但是,《刑法》沒有明確規定“其他積極參加者”具體所指,導致實務和理論界的理解和認識產生分歧。
一、“積極參加者”被認定標準的司法現狀
聚眾斗毆罪罪狀表述簡單,積極參加者與一般參加者難以區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此并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兩高”的指導案例中也沒有對該問題的指導性示范。本文以中國裁判文書網2017年500起聚眾斗毆案例為研究對象,發現被認定聚眾斗毆罪積極參加者的五種情形。具體如下:

圖1 2017年500起聚眾斗毆案積極參加者被認定的五種行為分布
由此可見,多數司法人員認為聚眾斗毆罪積極參加者是指直接實施斗毆的行為人。而對于其他四種行為,不同的司法人員認知不一。圖1也說明我國司法實務界對聚眾斗毆罪積極參加者標準不一,且存在對同種行為不同處理的情形。
二、“積極參加者”被認定標準的理論觀點與評述
(一)綜合說
綜合說認為,“積極參加者是對參與聚眾斗毆活動的人參與程度的評價,這種評價既要考慮實施犯罪的危害行為在聚眾斗毆中作用的大小,也要考慮行為人參與聚眾斗毆的主觀惡性的輕與重。”[1]綜合說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角度來被認定積極參加者是值得借鑒和提倡的。犯罪本身就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體,它不僅要求行為人實施侵犯法益的行為,并且要求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明確行為的意義。對聚眾斗毆罪積極參加者主客觀的把握也是對行為人犯罪本質的一種理解,但該學說不能適用于所用的情形。就主觀惡性而言,行為人直接實施斗毆對社會的危害性非常直觀、明顯,但對其他四種情形不能一概而論。另外,該學說的實踐意義不強,行為在聚眾斗毆中作用的大小很難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
(二)客觀說
客觀說認為,聚眾斗毆罪的積極參加者是指行為產生嚴重后果或者在斗毆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行為人。這也是多數學者采取的觀點。傳統客觀說認為,聚眾斗毆罪中的“積極參加者”是指在聚眾斗毆中發揮主要作用或者在斗毆中直接致死、致傷他人的人。[2]現代客觀說認為,積極參加者中的“積極參加”指的是參與斗毆的實行行為,“積極參加”在實行行為中起主要作用。故積極參加者指實行斗毆行為的主要實行者,而不包括次要的實行者、一般的幫助者。[3]依據傳統客觀說,沒有造成此類嚴重結果的行為人、助威人員、提供幫助的人員均不是積極參加者。很顯然,傳統客觀說縮小了法益保護的范圍。現代客觀說提出的積極參加者系斗毆行為主要實行者的標準是值得提倡的,但現代客觀說排除次要的實行行為、一般的幫助者以及助威者。筆者認為,這混淆了積極參加者與主犯的內涵,聚眾斗毆罪的積極參加者并不能與主犯等同看待。積極參加是否起到主要作用、達到被認定主犯的程度,并不影響對積極參加者的被認定,其被認定的關鍵在于參與行為對斗毆產生的支配性的影響。
(三)主觀說
主觀說認為積極參加者是指具有主觀上積極參與的行為人。該學說分為主動說和惡性程度決定說。主動說認為“積極”表明了參加者在整個犯罪活動中的態度是主動的。[4]很顯然,主觀說認為行為人在斗毆中的主動性是被認定積極參與的關鍵。“積極”所體現的主動性一方面體現出行為人參與聚眾斗毆的熱切期望,另一方面體現出攻擊性。具有攻擊性是被認定參與人主觀惡性和行為危害性的重要表現。行為人的主動性突出的是先導性而不是被動性。依據主觀說,主動要求參與斗毆的行為人應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但那些被動提供交通等幫助、助威的人員難以適用該標準。惡性程度決定說認為被認定聚眾斗毆犯罪中“其它積極參加者”的關鍵是分析行為人在聚眾行為或斗毆行為或聚眾斗毆整個過程中的客觀行為體現出的主觀惡性的大小,而不是單純看其斗毆行為對危害后果的發生所產生作用的大小。[5]依據惡性程度決定說的觀點,被脅迫參與斗毆的行為人并不能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而提供交通工具等幫助、助威的人員反而可以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這不符合形式邏輯。
三、日本刑法典的規定及啟示
日本刑法對參與斗毆人員的行為模式明確規定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情形是直接實施傷害的行為。行為人直接實施傷害行為并產生后果的,如傷害罪、同時傷害罪;行為人直接實施傷害行為沒有產生后果的,如暴行罪。日本刑法學界認為,暴行和傷害的行為屬性是一致的,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產生了刑法意義上的結果。上述情形在日本刑法典中屬于對個人法益的侵害,而聚眾斗毆罪在我國刑法典中屬于對社會法益的侵害,故斗毆中是否產生傷害結果不是被認定積極參加者的關鍵。
第二種情形是準備兇器集合的行為。日本刑法第208條規定,二人以上的人出于對他人的生命、身體或財產共同加害的目的而集合的場合,準備兇器或知道有此準備而集結的,系準備兇器集合罪。[6]這里的集合是指為了共同的目的而準備兇器或明知備有兇器而在一定的場所聚集在一起的行為。日本通說認為,本罪對個人法益和社會法益都具有抽象的危險。聚眾斗毆罪同樣侵害和危險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我國刑法中聚眾斗毆罪處罰的主體是有選擇性的,與日本刑法中準備兇器集合的行為略有不同。該種行為人能否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關鍵在于其對聚眾斗毆產生何種影響。
第三種情形是助威模式。該種行為模式主要是指參與到傷害他人的群體性行為之中,但是沒有親手傷害他人的情形。對于該種情形,日本法有兩處予以規定。一處是日本刑法典第206條現場助威罪。依據日本刑法的觀點,本罪行為是在該犯罪現場實施煽動、強化行為人的犯罪意思的行為,通過“起哄者”的“煽風點火”,使本來不會發生的傷害或者傷害結果成為現實。另外一處是日本刑法典第106條騷亂罪,對指揮他人或帶領他人助威的以犯罪論處。這里的“助威”是指增加騷亂的氣勢或者是增強騷亂的效果而積極活動的行為。
從規定來看,助威強調的是對預想結果的有效性,另外騷亂者的責任主體還有附和隨行者。筆者認為,這一主體也是助威的一種。雖然附和隨行人員也參與到騷亂之中,但是行為人并沒有實施暴行、煽動等行為。附和隨行人員的行為實質是通過參與騷亂增加己方群體龐大的氣勢,這種氣勢是心理上的助威,而不是對騷亂結果具有有效性助威。我國《刑法》第292條把首要分子與積極參加者的量刑等同看待,可見其危害性相同。就圖1一般助威和持械助威來說,助威的有效性表現為對斗毆的實質性作用。總之,助威行為只有對斗毆產生促進、加功等功能性支配作用,才可以與首要分子等同看待。
四、聚眾斗毆積極參加者的被認定標準——基于功能性支配的視角
所謂聚眾斗毆罪的積極參加者是指參與聚眾斗毆并直接實施斗毆行為,或者雖然沒有直接實施毆斗行為,但對聚眾斗毆行為具有幫助、促進和加功等功能性支配作用的行為人。這種功能性支配作用包含兩種:直接的功能性支配作用和間接的功能性支配作用。
(一)直接的功能性支配作用
行為人只要在明知或者可能發生斗毆的情況下前去相約地點,均屬于參與聚眾斗毆的行為。侵害法益的程度究竟有多重才可以被認定為犯罪,是一個刑法規范的評價問題。我國刑法不像日本刑法,“附和隨行人”也要受刑法處罰。我國刑法明確把積極參加者與一般參加者區分開來,僅對積極參加者入刑處罰。從我國刑法第292條文義解釋來看,積極參加者的積極破壞性和主觀惡性是立法處罰行為人的實質所在。筆者認為,積極參加者的被認定標準之一就是行為人直接實施了斗毆行為。這種行為是破壞社會管理秩序最直觀的體現,是使民眾產生恐慌心理、打破社會秩序有序性和穩定性最有力的證據。這也體現出行為人熱情參與、渴望追求結果發生的主觀惡性。這就將被糾集之后僅僅跟隨前往、尾隨參與、沒有直接對對方實施不法有形力的“附和隨行人員”排除在犯罪之外。
(二)間接的客觀功能性支配作用
在實施助威和幫助行為時,行為人對聚眾斗毆發揮的是間接作用。如果這種間接作用對聚眾斗毆具有幫助、促進或者加功等功能性支配的效果,則應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
1.持械助威
一般意義上說,械具的作用力比用身體部位直接打擊的威力要大。但是,持械助威是否必然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呢?筆者認為,被認定持械助威為聚眾斗毆罪積極參加者的標準在于該種行為是否對聚眾斗毆行為具有幫助、促進和加功等功能性支配作用。如果有,應當被認定,反之則不應被認定。具體來說,行為人持械參與斗毆而沒有實施斗毆行為時,如同日本刑法騷亂罪的附和隨行者,行為人通過參與斗毆增加己方群體的氣勢。這種氣勢是心理上的助威,對聚眾斗毆不具有有效性的影響,應被認定為一般參加者。而持械行為人具有指揮、鼓動、慫恿他人參與的行為時,不僅僅追求斗毆結果,而且為斗毆結果的發生積極活動,則此時持械行為人對斗毆的發生、發展以及結果的發生具有客觀支配性作用,應當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
2.一般助威
這種行為模式包括不做任何行為、不發表任何言論,單純站腳助威;還包括不做任何行為,但用鼓動性語言等鼓勵、慫恿己方人員。前者是參與人跟隨他人前去斗毆現場,代表某一方成員,以個體的存在形成人員數量的優勢,給己方斗毆人員進行心理助威,給對方以數量優勢的威脅。這種助威僅僅是心理上的助威,對他人難以產生有效的影響,并不能與直接實施斗毆的人員一起支配聚眾斗毆的結果,對聚眾斗毆沒有客觀支配性的功能,此種情形不應以犯罪處理。對后者也要區別不同的情況予以處理。鼓動、慫恿等語言要具有效果,才可以評定為具有支配性功能,進而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其理由是己方人員在鼓動、慫恿下實施斗毆行為,說明鼓動、慫恿等言語行為加速了斗毆的發生、發展,對斗毆的結果具有客觀支配性作用。否則,即使行為人具有鼓勵、慫恿等言語行為,但是己方人員并不受其影響,那么行為人對斗毆結果就不具有客觀支配的作用,此時應被認定為一般參加者。
3.幫助行為
(1)提供械具的行為
該種情形包括受首要分子指派和命令而提供械具以及自行主動提供械具兩種情形。當行為人應他人要求提供械具時,行為人是否提供械具并不影響他人實施斗毆的主觀愿望,行為人僅僅是他人實施斗毆的工具。此時,行為人并不能客觀地促進、加速斗毆的發生、發展,不應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行為人明知將要發生聚眾斗毆時,自行主動為斗毆提供械具,此時參與斗毆的主觀惡性明顯,但也不應一概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當行為人自行主動提供的械具被己方部分或者全部人員直接用來實施斗毆時,提供械具的行為與持械斗毆的行為共同支配了斗毆的結果,此時應當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相反,僅僅提供械具,但械具并沒有被使用,那么械具對聚眾斗毆的發生、發展、局勢的加劇與否并不起客觀的支配性作用,則此時的行為系一般性的幫助,應被認定為一般參加者。
(2)提供交通運輸的行為
聚眾斗犯罪一般表現為結伙進行打架斗毆。該種犯罪往往要進行交通運輸,從一個地點達到斗毆地點。筆者認為,行為人僅僅實施提供交通運輸運送斗毆人員的行為時,并不能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即使提供交通運輸者屬于斗毆一方,也不應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其理由為:第一,行為人提供的交通工具本身并非一定直接作用于聚眾斗毆的犯罪行為。第二,犯罪分子如果沒有行為人提供的交通工具,也存在通過其他途徑到達作案現場的可能。提供交通工具把犯罪分子運送到作案現場,并非犯罪結果發生的必然條件,而是充分條件。第三,犯罪結果是由直接實施斗毆的行為人造成的,而非由行為人提供的交通工具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