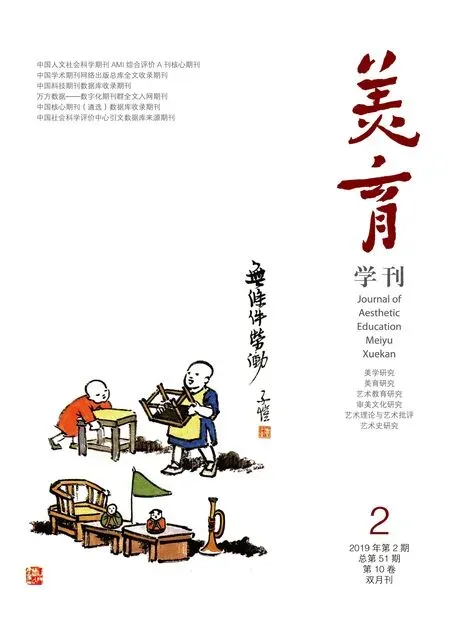藝術經典的美育價值探析
李一帥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北京 100732)
優秀藝術家的作品,特別是代表性、奠基性的作品常被稱為藝術經典。藝術經典是從歷史長河的無數作品中大浪淘沙,最終保留的一小部分有典范性和權威性的作品。藝術經典是藝術流派、藝術類型中特別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具備著某種永恒的美學價值或持久的藝術品質,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者空間的轉移而發生價值和品質變化的作品,是在每個時代經過選擇、比較、接受后依然對人們有著教育意義、指導意義、美學意義的作品。無疑,藝術經典對人們具有非同尋常的美育價值,這是我們一般欣賞藝術從“經典”開始的首要原因。
一、中西方文化中的“經典”與美育
“經典”這個詞在東西方文化中早就存在,但其意義在東西方有不同的起源。中國文化中的“經典”主要是指“圣賢之書”、“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和“古代儒家的經籍,也泛指宗教的經書”。中國藝術經典中的“經典”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和典范,在諸多著述中都闡釋了“經典”的相關意義。《漢書·孫寶傳》:“周公上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后漢書·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經典”在這里意為常讀的典范載籍。唐代劉知幾《史通·敘事》:“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四》:“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載于經典。”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經典”在這里意為圣賢之書。而在當今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經典”的意義為“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和“古代儒家的經籍,也泛指宗教的經書”。
西方文化中的“經典”(Canon)是經文用的典,它起初源于希臘文“kanon”,指的是度量的蘆葦和棍子,代表尺度。在基督教出現后,“經典”成為宗教術語,專指合法的經書或者典籍,所以歐洲文藝批評的誕生就與經典所代表的文藝尺度和規則的意義相關。在西方文化中,“經典”是文藝評論家、學者們用極高的文藝標準來界定的作品,20世紀以前的大部分學者、批評家認為一部作品沒有經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考驗是無法被認證為經典的,認為時間是衡量經典內容形成的必要條件。而“文學經典”作為一種特定理論的出現主要是從20世紀開始,理論家與批評家越來越多地開始反思宗教對文學的經典化過程的影響,加之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思想流派的興起,理論家們質疑“文學經典”的形成摻雜了政治、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因素,對于已存在的“文學經典”是怎樣成為經典的開始了爭論。西方學界先是掀起了“打開經典”“拓寬經典”的浪潮,要求“經典”的范疇擴大化,旨在擁抱多元化、解除歐洲文化中心論。但20世紀拓寬“文學經典”的論爭中,其實更多關注的是“經典”概念的包容性。
對于“經典”的標準和規則問題爭論不休,但“經典”的標準形成也有其規律性。起初是根據文藝批評家、理論家的審美標準來進行評判,但每個時代的理論家會受到時代審美背景的影響,對藝術經典標準的判斷也會不同,同時理論家的水平也參差不齊。20世紀以來,明顯加入了大眾的批判標準,印刷出版和數字媒體給予了作品量化結果的標準,不斷的翻印率、火爆的上座率、上升的點擊率是大眾助力藝術經典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無論如何,藝術經典都秉持較高的藝術標準,作為權威之作帶給人最根本的利益是用藝術來啟迪和教育大眾的美育功能,通過藝術經典,使人建立良好的審美標準和品位,甚至是建立一種道德標準和探尋自我人格的觀念標準。席勒在《美育書簡》中指出:“想使感性的人成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沒有其他途徑。”[1]朱自清早就發現經典在美育中的重要性:“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2]12朱自清認為經典的價值不在于功利,而在于文化的接受與傳承,在領略過經典的基礎上,才能對文化建立一種高度的視野,讓人們認識到經典和經典的重要性,是一種責任。
在對“經典”的擇取上,朱自清做了一個范例。他親自纂寫《經典常談》一書,《經典常談》對經典做了全面地深入淺出地介紹,分別概述了《說文解字》《周易》《尚書》《詩經》《春秋》《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經典典籍的背景和內容,還涉及諸子、辭賦、詩文各種類別中的經典。但是朱自清認識到古代經典典籍的語言與當代大眾之間有著隔閡,“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2]13。他意識到了古代經典如果不做整理,不加以解釋,大眾就難以理解,那么古代經典實際就失去了對當代大眾的美育功能,所以他將古代經典典籍用白話的形式加以概述,做出介紹,讓大眾真正理解中國古代文化精髓。為此,朱自清做了大量“翻譯”和“解釋”的工作。葉圣陶評價朱自清所做經典“翻譯”工作在美育上的重要性:“我又想,經典訓練不限于學校教育的范圍而推廣到整個社會,是很有必要的。歷史不能割斷,文化遺產跟當今各條戰線上的工作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牽連,所以誰都一樣,能夠跟經典有所接觸總比完全不接觸好。”[3]葉圣陶對《經典常談》價值的認可,也是對古代文學藝術經典進行當代形式改造后能更好地進行大眾美育教育的認可。
我們今天的藝術經典既有中國和西方作為原始意義上文藝標準的權威典籍,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最優秀的藝術形式和作品,又有在當代對中國大眾產生重要影響的藝術作品,具有推進或改變時代社會思潮的意義。藝術經典具備著傳承中華美學精神的重任,同時也肩負著美育的重任。藝術經典需要與時俱進,不僅西方藝術經典需要翻譯成中文,中國古代藝術經典同樣需要翻譯成今天的語言,經典需要傳承,需要接受,更需要轉化,才能在美育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二、中國藝術中的審美意識與審美育化
中國藝術中的審美主體與審美意識論題已經經歷了中國數代學人的探討,所以今天我們再次探討起審美意識的論題,重點應放在藝術經典中的美學精神與這個時代審美意識的結合。美學精神來自民族藝術作品中體現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理想,中國藝術經典中的美學精神主要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作品中的審美意識,它離不開美學基本理論和思想的支撐。中國美學的特征與西方美學的特征存在著根本的區別,西方的美學注重理性與邏輯,中國的美學注重生命與感悟,所以在對中國藝術經典的審美上,不只是屬于“經驗的”層次,更是走進“超驗的”范疇。中國古代的藝術經典正是體現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載體,古代傳統藝術中的繪畫、書法、音樂、戲曲、舞蹈、雕塑、建筑等藝術門類都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優秀歷史文明中留下了種種印記,同時也都鮮明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美學精神和民族特色。
審美主體在審美活動之中,必須理解創造主體的意識,才能更好地進行審美活動。在中國美學中,藝術作品強調“道”“技”“人”的統一,比如蔣孔陽認為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人格和哲學思想之“道”是統一的。“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重視的不是表面現象的真實,不是作品中寫的是什么,不是主題和題材,而是藝術作品的本身,是藝術作品當中所體現出來的宇宙原理‘道’,以及與‘道’冥契協調在一起的藝術家的人格。藝術作品—道—藝術家的人格,這三者的統一,就成了中國的藝術,成了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4]中國畫家畫梅花不像西方的畫家注重形態的寫實,西方畫家把梅花的形態如實地描繪下來,而中國畫家是抓住梅花的特點,要在梅花筆墨中體現作者自己的精神品格,體現藝術家自身之“道”,所以藝術家的創作最重要的并非梅花形象本身,而是藝術家的品格和精神。西方畫家認為筆和油彩是繪畫的工具,而中國畫家認為筆墨是體現精神氣韻的根本,是畫家的精神和人格本源。
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興焉。”天即是一種創造主體,天道在不斷地進行創造。《莊子》中言:“今一以天地為烘爐,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這里體現宇宙即是創造的烘爐,創造的原始空間,不停地進行創造。所以中國儒家與道家對于審美主體創造有著不同理解,道家是盡量消除人力,而借以自然之力,以自然的創造為創造;而儒家認為,人力可以充當天力,天不能言的人可以言,但是人的創造要符合天的秩序。中國美學中體現的“天地為體、造化為用、萬物為相”,也是中國的藝術家和創作者需要從古代藝術經典中體味“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精神”的“三位一體”的原因所在,藝術創作者并非要從美學理論著述中感悟中國藝術精神,相比之下,中國藝術經典為藝術家樹立了更直觀的參悟方式,在同一藝術門類的古今時間交融中進行心悟交流。
理解藝術創作主體的審美意識,是審美者對藝術經典審美的基礎,也是審美者接受美育過程的前提條件。審美者的范疇既包含藝術家和創作者,同時也可以是藝術鑒賞者。宗白華曾說:“這種藝術人生觀就是把‘人生生活’當作一種‘藝術’看待,使他優美、豐富、有條理、有意義。總是,就是把我們的一生生活,當作一個藝術品似的創造。這種‘藝術式的人生’,也同一個藝術品一樣,是個很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5]宗白華強調藝術與人生的兩者不分,即是強調藝術對人生的影響,通過藝術給予人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審美者通過藝術作品感悟創作者之境。如果說藝術家的藝術創造過程是“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精神”,藝術家通過藝術作品體現自我藝術精神,那么審美者審美過程在于“審美者—藝術作品—藝術精神—藝術家”,審美者通過藝術作品體會藝術精神,從而理解藝術家的精神品格。宗白華倡導的就是藝術的生命化和個體生命的藝術化,所以對中國藝術審美意識的理解和傳承不僅僅是藝術從業者的追求和責任,也應該是每一位審美者的追求和責任,也是審美者藝術自我教育的過程。
審美者與藝術家兩個個體生命通過藝術作品連接,所以藝術作品中也往往孕育出生命的氣息。葉朗曾指出:“宗白華先生認為中西的形上學分屬兩大體系:西洋是唯理的體系;中國是生命的體系。唯理的體系是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結構、秩序理數,所以是宇宙論,范疇論,生命的體系則是要了解體驗世界的意趣(意味)價值,所以是本體論,價值論。”[6]宗白華認為藝術創造的過程可以用一種物質作為對象,并使對象理想化,我們生命創造的過程有如有機的構造生命的原動力,貫穿于物質其間,美化人生命創造的過程。藝術創造的目的是形成優美高尚的藝術品,而人生創造的目的則是創造出一個類似藝術品一樣優美高尚的理想人生觀。宗白華從西方美學中汲取了一些思想,如柏格森、叔本華對生命哲學的認知,生命需要不斷地進化、不停創造,生命意志是無限自由的,機械論或目的論等決定論都不符合生命的自由發展。這與《周易》中的“生生而有條理”相似,“生生”指的是宇宙的日新月異,而“條理”指的是宇宙秩序的和諧相宜,即生命存于優美、和諧、高尚的形式之中。古代藝術經典體現的藝術生命精神同樣也是優美和高尚的,經過時間流沙的洗滌,具有魅力和感染力的藝術經典可以直接給審美者呈現出藝術的生命感,審美的時間長了,欣賞的次數多了,也自然而然會建立一種藝術的生命感。審美意象也是中國審美意識區別于西方美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國藝術經典所體現的重要特征,比如唐代的“境”和宋代的“韻”的特征,都構成了獨立于世界美學體系中的中國藝術精神因子。“每個時代的審美意識,總是集中地表現在每個時代的一些大思想家的美學思想中。而這些大思想家的美學思想,又往往凝聚、結晶為若干美學范疇和美學命題。”[7]這些美學思想必須以藝術經典為依托,在藝術經典的具象中讓西方人理解中國美學精髓,否則“象”“氣”“境”“妙”“味”“神”“骨”“韻”這些中國美學中的審美意識特征即使有對應的單詞進行翻譯,也難以讓西方真正理解其中的豐富內涵。
中國藝術思想中的藝術家創作體驗和經驗在西方往往被認為具有一種非邏輯、非理性的特征,但隨著中國哲學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傳播者介紹到西方,西方學者和藝術家了解中國美學思想特征后,中國特殊的“創作體驗”如今也被看成是一種極具特色的民族美學特征。因為西方的創造更重視“靈感”,從宗教意義上講,“靈感”是超然物外的神靈帶來的精神體驗,所以柏拉圖在《伊安》篇中強調:“神對于詩人們像對于占卜家和預言家一樣,奪去他們的平常理智,用他們作代言人,正因為要使聽眾知道,詩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無知無覺中說出那些珍貴的詞句,而是由神憑附著來向人說話。”[8]與西方美學中“上帝與我”的二分不同,中國美學講究“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自我沒有獨立出來,既是有我之境,又是無我之境,自我的精神存在文藝作品中,藝術的精神也即是表現一種自我。中國學者和藝術家認識到藝術經典中的“創作說”的重要性,從而也紛紛開始整理和闡釋藝術中的“創作體驗論”。所以美育的過程不僅來自藝術作品,更來自對創作源頭的理解,對藝術家的創作意識和創作體驗的融通。
三、藝術經典的普及性美育
藝術經典是人類文化創造的精神結晶,藝術離不開哲學、歷史、文學、宗教、科學、語言等學科的共同發展,藝術的歷史是和人類的文明史、文化史一樣古老,是隨著人類的誕生而存在的,又隨人類歷史發展而逐漸豐富。藝術經典的貢獻不在于物質的接受與滿足,而是書寫人類精神生活史中獨特的價值。所以藝術經典的重要價值不僅僅是針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美育作用,更是針對大眾群體、學生群體的美育作用,發揮藝術經典的普及性作用,相比之下,后者群體更加需要藝術經典。
審美教育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方式,不僅具有自己特殊的內涵與目的,而且具有與其他教育不盡相同的形式,比其他教育方式更重感受力、更直觀。葉朗曾談到藝術經典對大學生審美的重要意義:“因為文化經典是各個歷史時期人類最高智慧和最高美感的結晶,這包括哲學經典、文學經典、藝術經典。文化傳承離不開經典,人類的文明發展離不開經典。”[9]《尚書·虞書·舜典》有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不僅道出了藝術的本質和規律,也道出藝術的思想和靈魂,在藝術教育中要以“和”和“諧”為基本達到“神人以和”的目的。藝術經典正是讓大學生接受中國文化精髓,建立文化視野的敲門磚,通過藝術經典高藝術標準,來潛移默化啟迪大學生的智慧,塑造大學生完美人格。因為大學不僅有傳承文化的使命,還有發展和創新文化的使命,這種大學文化本身就包含著審美教育的過程。蔡元培認為:“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10]蔡元培把美育看成是一種自我道德標準,通過建立自我道德,通過藝術可以做到自我凈化,培養自己高尚品德。美育是與人生品質關聯的教育,所以藝術經典正是對大學生人生的審美品質構建的最佳范本,對大學生美德教育和審美教育的要求,是對大學教育更高層次的要求,對學生高尚品德和審美精神的培養,既是教育的本質和宗旨所在,又是教育職責的使命使然。
藝術經典美育價值不僅僅在于接受藝術精神,更在于藝術精神的內化,德性的養成。王陽明有言:“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11]“誠自家意”的意思就是成就德性,而“格天下之物”則是成就知識。以王陽明的理解來看,成就德性與成就知識并不是一個范疇,知識的增長并不代表德性的修得,重點不是在于如何窮盡天下之理,而在于怎么通過成就知識上升到成就德性,即“誠自家意”。這也證明了美育普及的重要性,因為獲得知識并不代表提升德性,而美育是提升德性的一種方式。所以在藝術經典的熏陶下,審美素質得到提升,人格情感得到升華,從而影響人生觀念和態度,這對于學生群體尤為重要。因為學習階段是實施美育不容錯過的關鍵時期,這對于大學生審美素質、生活認知、人生態度、德性涵養、個性建構、人格完善等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藝術經典不僅對大學生群體有美育的普及性價值,對于大眾群體也具有美育普及性價值。大眾審美的娛樂化、媚俗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沖擊,大眾對于媚俗文化的沖擊并沒有過多的抵抗力和判斷力。大眾藝術興起的過程就是西方大眾文化進入中國的過程,但中國大眾文化結合了西方大眾文化并與我們的媚俗鄉土文化、媚俗市井文化相融合,雖然大眾文化為不同文化層次、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娛樂選擇,但是不追求意義的文化會使大眾文化變成一種不能促發文化進步的形式。所以對藝術經典的選擇、甄別尤為重要,不僅要具有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功能,還要具有抵制大眾媚俗文化的功能。
在今天,藝術經典的選擇不僅由經典的內部價值決定,同時還有大眾審美者來決定。大眾審美者也是藝術經典的鑒賞者,大眾審美者的廣泛參與能定位藝術經典的歡迎度和購買值,所以大眾審美者的審美水平一定意義上也決定著藝術經典的美育價值能發揮到什么樣的高度。接受美學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這種方法明顯地提供了一個決定其審美價值的尺度。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12]也就是大眾審美者的“期待視野”是大眾審美的關鍵問題,大眾審美者的對藝術作品的藝術特征有預設的“期待視野”。如果大眾的“期待視野”與最終作品的審美判斷之間存在差距,那么對舊的審美經驗可以進行翻新或者通過新的經驗把原先的審美層次再提高一級,于是就會生成審美“視野的變化”,即“審美的距離”,“審美的距離”是根據大眾審美者或自發地、或主客觀地對藝術作品進行判斷。如果要縮小大眾審美者“期待視野”的距離,那么接受意識并不會轉向未知經驗的視野,藝術作品更可能是媚俗的、通俗的、娛樂化的作品。所以,藝術經典若想做到美育普及,就必須認識到藝術經典對大眾的兩層價值,首先需要通過藝術經典把大眾審美提高一個層次,再通過藝術經典進入美育德性培養的階段。大眾的接受意識很可能隨著流行的趣味標準改變,產生媚俗的文化藝術,而大眾接受意識的迎合使得媚俗文化藝術再生,接受意識和期待情感都逐漸固化,即使文化藝術作品中產生一些道德問題,也會被大眾的固化情感和定式思維所擁戴。藝術經典應該被作為提高大眾審美、驅除媚俗文化的主要內容,在提高大眾審美標準、趣味、水平上應該建立一種范本。“美育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審美力本來就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人類社會愈朝前發展,人的審美力應該愈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然包括健康的審美力的培養。”[13]所以美育在大眾文化與大眾接受的問題上承載著更多的意義。
藝術經典的美育普及化不僅可以讓審美者認識國家和民族引以驕傲的美學精神,同時也認識到良好的民族形象,幫助審美者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培養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方式、思維結構、精神氣質,體現民族的共性,即藝術中的民族性。民族性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個性的總和,是分散個性中的集合點,這些同一民族人民的個性中的共性就形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在歷史中慢慢形成的,民族性就是本民族的基礎價值觀。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藝術也同樣彰顯著民族性,藝術家有民族的屬性,這種民族性的烙印同樣會顯示在藝術經典作品當中。藝術經典的美育價值是無可替代的,通過藝術經典進行美育,不僅有助于個人審美鑒賞力的增強,做到知識與情感的升華,健全人格和行為準則。同時藝術經典發揮的美育價值也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綜合人文素質,是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的內在的情感動力的一部分,所以美育更是傳承中華美學精神的一種方式,是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一種手段,這正是通過藝術經典進行美育的當今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