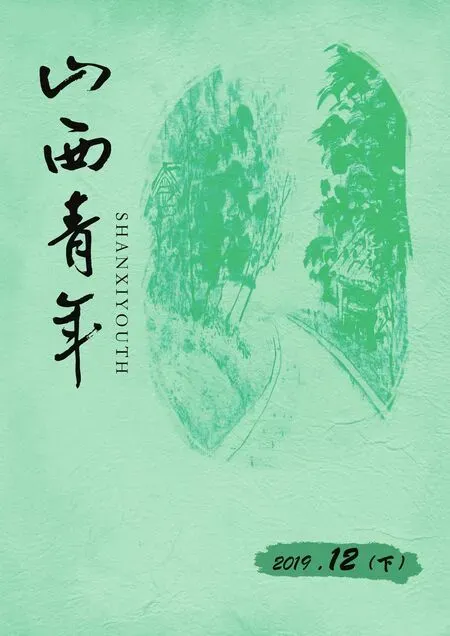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
饒媛媛
(云南大學法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國家法律體系也逐漸完整合理了,但目前的部門法還有待完善的地方。從歷年婚姻法的演變及出臺的司法解釋可以看出法律天平從傾向債務人到債權人,再到追求中間平衡點做了很多努力。1950年《婚姻法》第24條的規定將男方的責任無限擴大,當共同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應當全部由男方負擔,可見當時的規定比較極端。1980年《婚姻法》規定共同財產不足以清償時,由雙方協商或法院判決。此時法律偏向于保護夫妻雙方作為債務人的權益,開始出現對債務認定采共同生活目的論的偏向。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明確表示若證明債務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是《婚姻法》第九條第三款的情形,則可以認定為個人債務——這顯然站在債務推定的視角。這是為保護債權人的權益,日常生活中,由夫妻雙方共同出面向債權人借款還是少數,多數還是夫妻一方出面借款,借款最終是為夫妻共同生活所使用還是個人使用,債權人往往無法接觸真相,若由債權人對此舉證,不僅困難,還容易導致敗訴[1]。2018年最高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3條(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以夫妻共同簽字或者另一方事后追認來衡量;若是個人名義所借,債權人就要證明該筆債務的用途的確是用到夫妻雙方的日常事務中,相對于夫妻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債權人作為一個“外人”很難去證明夫妻財務的最終流向。
一、具體問題
(一)矯枉過正的債務認定
《婚姻法司法解釋(二)》規定了唯一可以排除夫妻雙方中非舉債方責任的兩種方式:1.債券設立時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這在實際生活中,若夫妻一方有意損害另一方的權益,實際債務人不會與債權人作此約定,受損的一方也很難對該債務的約定情況進行證明。2.夫妻雙方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且債權設立時債權人知曉該約定的內容。還是同樣的道理,若夫妻一方有預謀的要損害夫妻另一方的權益,即便夫妻雙方有分別財產的約定,對債權人進行隱瞞也是輕而易舉,若是債權人與夫妻雙方中的舉債方合謀虛構債務,債權人即便知道也會聲稱不知情。另外善意債權人基于對自己權益的保障,很少會和債務人單獨將債務約定為個人債務,進而免除夫妻中非舉債方的責任,提高自身風險。將債務關系中的債權人和作為夫妻關系的債務人相比較,債權人本身對債務人夫妻兩人對于借款的實際用途就處于不知情的弱勢地位,將夫妻兩人作為一個整體在法律上對債權人承擔償還借款的義務是對債權人的保護,但《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有矯枉過正的情況。立法過程是不同價值之間的博弈過程[2]。《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選擇了保護債權人的法益,雖防止了夫妻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債權人利益,顧此失彼,該條規定不僅對夫妻關系中非負債一方的權益沒有進行保護,反而有損其合法權益。要求夫妻中的非舉債方對另一方與債權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甚至連債權債務成立的時間、約定的條件都不知道的情形下,在信息失衡下,要求非舉債人對債權關系證明,債務約定為個人債務;或是要求債權人知道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另有約定,不僅困難度大且不符合實際情況,更別說當夫妻中的舉債方有意虛構債務侵占共同財產的情況,要讓非舉債方舉證以免除自己的責任、保障自己合法權益更是天方夜譚。夫妻任意一方和第三人合意謀劃侵占、騙取夫妻雙方共同財產的案件眾多,甚至是一種嚴峻的社會問題。《司法解釋》的第三條其實是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適用的否定,將之前法律的偏差拉回到《婚姻法》的正軌中,規定家事代理原則,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應當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否則不支持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司法解釋》的頒布,推翻了之前的不合理性,但原則性規定過于籠統,舉證責任分配上不夠明確。
(二)家事代理中的家事范圍不確定
有的學者認為,《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法理基礎來源于日常家事代理權,夫妻雙方有權互為代理對方處理日常家事,未經對方同意的債務可以認為是共同債務。最新司法解釋雖有法條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以個人名義舉債,若借款用于家庭日常事務范圍的,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若超出家庭日常事務范圍的,則債權人就要進行舉證,合理合法證明借款的實際用途。家事代理權在新司法解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責任推定上以借款的實際用途作為責任劃分的標準。夫妻雙方對于日常家事互為代理人,一方得以為他方就日常家事對外與第三人為一定的法律行為即是家事代理權[3]。夫妻雙方都有權因日常家事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但就目前的法律而言,哪些事務算是日常家事,并沒有一個好的解釋或者規定,我們也知道這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可以簡單概括的。
(三)違反民法原則
夫妻雙方雖然對家庭日常生活雜事均有代理權,但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來說,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太高,不利于夫妻雙方獨立人格的發展。并且在民法也沒有夫妻這一主體概念,都是單個的自然人為民法主體。《婚姻法司法解釋(二)》完全免除債權人的舉證責任。婚姻關系仍然存在期間產生的債務,由夫妻雙方中的負債方承擔舉證責任,無法證明債務是個人債務或債權人不知道夫妻雙方對其“表見”共同擁有的財產有單獨約定,不利后果則由夫妻雙方中的非負債方承擔,這違反了民法“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法律制定上的“偷懶”在實踐運用中反應出來,無形之中增加了法院判案的困難度,降低當事人對判決結果的滿意度以及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期待值的降低。《司法解釋》主張“共債共簽”是對夫妻雙方獨立人格的肯定,夫妻二人在民法上仍然是一個整體對外承擔連帶責任,但不在將兩個獨立的人格一味的捆綁,“共債共簽”原則既肯定了夫妻雙方對外承擔連帶責任,又是夫妻兩個獨立個體民事權利能力的體現。同時“共債共簽”原則的提倡,也從源頭上防止了因一方對另一方債務情況的不清楚、不了解,導致權益受損而“被負債”。
二、完善建議
(一)舉債責任分配及證明標準
有學者提出,將債權主張分階段分配舉證責任,發生在非離婚階段和離婚或分居階段。非離婚階段由于感情穩定不存在惡意侵占共同財產的情況,首先推定為共同債務,除非可以證明借款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離婚或分居的情況下,用于日常事務的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其余部分由舉債方證明借款的用途[4]。筆者認為,實際生活中夫妻在沒有離婚的情況下,夫妻一方舉債,即使舉債方對非舉債方隱瞞借款事實會引發雙方爭吵、不愉快,只要是在未離婚的情況下,最后結果非舉債方都是自愿用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償還的,我們所討論的舉證責任存在的前提是夫妻財產要進行分割,債務要進行分割,沒有離婚,財產在法律上就屬于共同財產,就沒有分清歸屬的意義。
有的學者認為,將日常家事代理權的行使作為是否是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將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分為兩種情況。根據債務主張的不同,以及舉證者的身份不同來分情況討論。主張為夫妻共同債務時,由提出該主張的主體進行舉證;主張為個人債務時,由主張為個人債務的非舉債方進行舉證,債權人只需反證該筆債務是夫妻雙方基于日常家事的用途而作出的承諾或者約定,有一定的依據即可[5]。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沒有考慮到主張個人債務的情況下,夫妻中的非舉債方可能存在被負債,甚至對該筆債務不知情的情景,此時由非舉債方來提出反證很困難,此時證明標準決定是否回歸到《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責任推定上。
在主張為個人債務時,考慮到債權人作為第三人在實踐中對夫妻二人的真實情況完全掌握較為困難,適當降低債權人舉證的證明標準,只要證明該筆借款發生時,債權人善意且有理由相信是夫妻共同債務,提供一定的線索或者證據,就完成債權人一方的舉證責任;此時由主張為個人債務的一方提出反證,考慮到夫妻中的非舉債方可能存在對債務不知情的情況,證明標準降低到存在為個人債務的可能性即可;真正的舉債方在證明債權債務關系時,證明標準適當提高,應提交準確且充分的證據來對債權人或夫妻中非舉債方的主張進行反證。在真正的債務關系中,夫妻雙方中的舉債人是這段的債務關系的關鍵人物,連接債權人與夫妻關系中的另一方,且是借款的實際使用人,舉債人的態度與案件的判決結果有很大關系,當舉債人無法證明或者消極證明借款的實際使用情況而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人又無法證明借款用于日常家事以外的,對第三方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它的范圍應當限制在夫妻共同財產范圍內,超出部分應當由負債人用個人財產來償還;夫妻雙方在離婚時對該筆債務產生內部的重新分配,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人就之前以共同財產償還的部分對舉債人享有債權。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對于債權人來說,既考慮到債權人要掌握夫妻之間實際資金流向的困難程度,防止夫妻雙方串通欺騙債權人,損害債權人法益,又避免債權人“睡在權利之上”享受權利;對于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方來說,既考慮到若存在其不知借款而“被負債”的情況下,證明借款的實際用途有相當大的困難性,防止債權人與夫妻雙方中的舉債方惡意串通,制造虛假債務,侵占夫妻共同財產,也避免夫妻雙方中非舉債方沒有法律成本而增加對方的訴訟負擔,對真正的舉債人來說,又避免其消極應訴而損害債權人或者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人的權益。
(二)家庭日常事務的范圍
有的學者提出應當以家事代理權為基礎確定“家事代理之債”,無論是家庭生活之債,還是因家事代理舉債用于家庭生活的都統稱為“家事代理之債”,為保護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方,則由舉債人證明債務是由于家庭生活必須所負[6]。有的學者指出,在確定家事代理范圍時以原則性規定為主,不同的地區經濟水平、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具體到每對夫妻的愛好、收入等各個方面也各具不同,不可能采取唯一的具體標準去衡量[7]。
《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各學者的觀點,可見家事代理逐漸成為確定債務是否為夫妻共同債務的標準,那么確定家事代理的范圍對完善法律有必要性。如何來確定其范圍呢?法律規定不能窮盡所有,由于法律的局限性,法律規定永遠是滯后于實際生活的,另外家庭日常事務也是種類繁多,不可能用幾個法條可以將其范圍限定的,筆者認為與其無法將法條列舉完,不如制定原則性法條,夫妻一方有家事代理權,對日常交易的代理只要符合正當性,用于家庭生活里面即可,當代理所作出的事項對家庭產生比較大的影響時,為避免一方與第三人虛構事件,則不可由一方單獨決定,比如大額的財產權屬變動、大數額的投資活動或者超出日常生活的高消費活動等不可行使代理權。
三、總結
“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當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8]”。當債權人的利益與夫妻雙方中的非舉債方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最終的平衡點就是我們經過法律價值衡量后的結果。原立法體系下,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面臨很多困難,舉證責任、認定標準等各方的遺漏規定,導致實踐發生大量夫妻一方串通第三人來損害另一方合法權益的現象,《司法解釋》規定了“共債共簽”的原則,以及債務用于家庭日常事務的規定,都很好的避免上述現象的發生,解決了原有的法律沖突。不過法律規定仍還有完善的空間,如舉證責任如何合理分配、家事代理權的限定范圍等相關問題。希望可以頒布一部完善的民法典,促進社會、家庭、個人的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