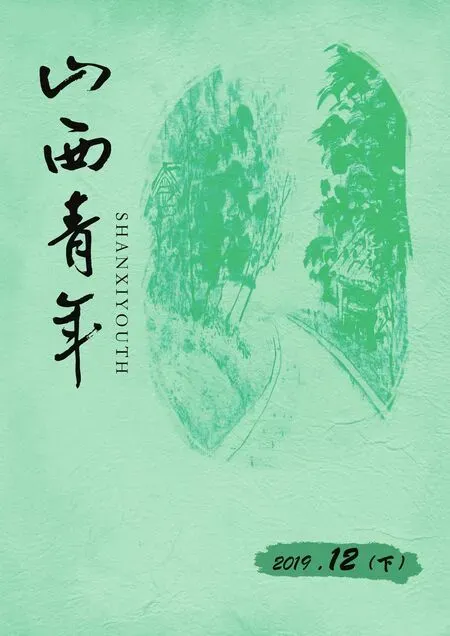新時代增強群眾工作本領的基本認識
張 健
(中共石嘴山市委黨校,寧夏 石嘴山 753000)
經歷改革開放四十年洗禮,我國經濟社會發生質的變化,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社會財富等方面,作為個體每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富起來有自己的直觀認知。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整體的人民群眾與歷史上以往任何社會階段相比,都發生了一些新變化。無論是哪個年齡層次的人民群眾,在富起來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自信、更加敢于去表達自己的意見、更加敢于表明自己的訴求、更加敢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一、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是擁有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人民群眾富起來的四十年。在這場社會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證明了自己具有帶領人民富起來的本領。從國家層面而言,以經濟總量(GDP)為衡量指標,中國經濟總量穩穩占據世界第二位,并且與世界第一美國的差距在逐步縮小。從社會財富層面而言,人均經濟總量由1978年的384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0多美元,逐步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最后就公民個體層面而言,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共造就了接近兩億多人口的中產階層,比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總數還要多。無論是中產階級的絕對數量還是其手中掌握的絕對財富,都在總量上穩居世界第一。
伴隨著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的增加,在其他層面特別是對于政治層面的民主、司法層面的法治、社會層面的公正、倫理層面的正義、生活環境層面的環境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與生活在物資短缺、物質匱乏年代的群眾相比,改革開放以來的群眾逐步實現了自身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關注焦點也從解決溫飽走向更高層次的需求,這就對執政黨的執政提出更高層面的要求,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發生的任何問題,都可能成為一個爆點,而被無限的放大,從而影響執政形象,進一步影響執政地位。
二、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是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民群眾
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直到改革開放前,走出國門放眼世界對于中國絕大多數人而言是遙不可及的一種夢想。在計劃經濟年代里,國際視野屬于一種稀缺資源。能夠走出國門,看看其他國家真實面貌的基本集中在省部高層。群眾對外界的了解更多的是通過新聞轉播來實現,因此屬于間接認知。在這個時間段內,因為群眾不掌握第一手信息資料,無法親眼目睹國際世界的運行,從傳播學方面給執政黨提供掌握傳播內容主動權。根據執政需要,選擇傳播內容。改革開放四十年,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放眼世界,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了更加直觀形象的認識。這種認識逐步形成了群眾的國際視野,會對國際國內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做出比較,形成自己的政治認知。
在走出國門放眼世界的群體中,有兩個群體值得我們關注。一個是代表普通群眾的出境游群體。根據國際統計局的統計,十八大以來中國出境游群體超過1億人次,并且逐年增加,截止到2018年年底達到1.49億人次,意味著平均每十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有過出國體驗。另外一個是代表高級知識分子的留學生群體。改革開放初期出國留學專屬于品學兼優的學子,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富起來的中國家庭越來越多的選擇自費到國外留學,出國留學趨勢逐步由精英化走向社會化大眾化。根據國家留學部門相關統計,截止2017年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超過500多萬,而且這個群體還處于不斷擴大過程中。通過這兩個群體人數的變化不難發現,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有著寬闊的國際視野,直接游走于各國之間,對于信息接觸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官方發布渠道,會對各國執政黨民生政策做出主觀上的判斷,增加執政難度。
三、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是具有法治意識的人民群眾
在富起來的過程中,中國法治教育也不斷推進,群眾的維權意識也與日俱增。從八零后到九零后再到零零后,有兩句口頭禪值得我們關注“不要叫我老百姓,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們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權利”“不要叫我老百姓,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納稅人,我們有納稅人的權利”,這表明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有著強烈的身份意識和維權意識。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其政治身份與社會身份已經由過去的老百姓走向更高層次的公民。身份決定行為,在面對執政黨的公權力時,人民群眾變得更加理性自信,少了悲情維權的成分,多了些理性維權的意味。
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維權意識,底氣源于憲法、源于我們國家的法律。列寧同志曾經講過憲法對于公民的重要性,“憲法是一個國家公民權利的宣言書”,我國憲法在第二章中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擁有的憲法權利與承擔的憲法義務,這些條款都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重要基石。實事求是的講,目前黨內一些干部尚不具備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干工作依然停留在人治時代,缺少規矩意識與制度意識。這種工作方式,與新時代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要求是不匹配的,一旦出現糾紛,容易引發網絡輿情,損害我們黨的形象。
四、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是擁有文化知識的人民群眾
高等教育普及化必然帶來政治社會化。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由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從大專、本科、研究生等學歷層次,人數都在增加。在校學習大學生數量與規模穩居世界第一,各學歷層次的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對知識理解尤其是對于法律知識的學習是基本要求。根據國家教育部數據統計顯示,2010年中國有高校畢業生631萬,2018年中國有高校畢業生820萬,在過去九年中累計7000多萬高校畢業生走向社會。改革開放40年中國高校畢業生累計超過1億多人。與龐大的高校畢業生相比,每年無論國考還是省考,包括事業單位在內,每年進入體制內工作的人群是非常小的。如果僅僅通過自己身邊年輕群體的思想動態,來把握青年群體的整體動態,是不符合統計抽樣的全面性要求,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現象。
高等教育的普及,讓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公權力在現代政治學中的定位。一個執政黨能不能長期執政,關鍵在于有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一個擁有知識的群體,在面對執政黨各種執政目標時會有自己直觀與基于知識的評判,不再是盲從執政黨的政治宣傳。如果執政黨的執政績效達不到預期目標,那么人民群眾會對其執政能力產生質疑,會漸漸失去支持的原動力,甚至會出現審美疲勞。與此同時,伴隨知識增加,會對執政黨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特別是執政效能的要求更高。
五、新時代的人民群眾是擁有現代科技的人民群眾
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各種新技術不斷涌現。在日常生活中,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方便更加高效。在政治參與與社會參與方面,科技的進步極大降低了參與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參與。伴隨智能手機性能提升,直播平臺的快速發展,自媒體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人民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無時無刻不在監督執政黨的執政行為。以2017年發生的昆明城管打人事件為例,處于二樓的群眾直接拿著手機對著全網進行公開直播,瞬間引起了極大的網絡關注。與以往的網絡傳播不同,各種直播平臺的出現,增加了宣傳部門輿論危機處理的難度。
截止目前,根據網信部門統計,中國網民數量達到8.54億,且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網民絕對數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龐大的網民數量,特別是手機網民數量,一方面增加了人民群眾監督執政黨執政行為的絕對人數,讓更多的群眾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參與到監督中來;另外一方面提升了執政黨自身執政本領的要求,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