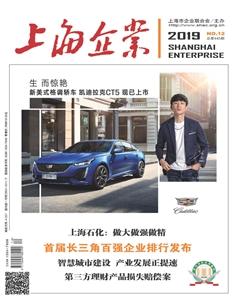保險公司是否應為其保險營銷員私下代銷第三方理財產品所致投資者損失負責賠償
前些年,P2P理財公司和理財產品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高額投資回報的理財產品吸引了廣大投資者競相購買,而對于銷售人員的高額回報亦吸引金融企業阿的諸多業務員與理財公司合作,不顧行業禁止私下向其因履職金融企業而獲知的客戶推銷理財公司的理財產品。而這幾年,這些暴利產品的兇險已一覽無遺。隨著大量理財產品到期后不能兌現及P2P公司紛紛倒閉的情況不斷涌現,曾接受金融公司業務員推銷而購買第三方理財產品的投資者們在向理財公司索賠無果的情況下,不由將目光投向了業務員所任職的金融公司。那么問題來了,在業務員從事金融產品營銷代理工作之外私自接受第三方理財公司的委托,并向客戶推銷第三方理財產品且相關客戶投資購買該產品后,對于該產品到期未能足額兌付本息導致相關客戶遭受的損失,業務員所任職的金融企業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下面,我們通過曾經代理的一則保險公司所涉具體案例來加以分析說明。
一、案例簡介
本案例是關于楊某訴某保險公司的侵權賠償案件。原告楊某,系被告某財產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保險公司”)客戶,曾經購買了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陳某甲系被告保險公司某營業部經理,談某系該營業部的業務主管,李某和陳某乙系該營業部的保險代理人,以上四人均與保險公司簽訂了《個人業務保險營銷員委托合同》。本案原告楊某在訴狀中稱,陳某甲等人多次組織聯誼會等活動,在活動中公開宣傳第三方理財公司帕拉迪公司(以下簡稱:“帕拉迪公司”)的P2P理財產品。在陳某甲、談某、陳某乙、李某的推銷下,原告楊某于2013年7月30日在帕拉迪公司的經營場所,楊某作為乙方與帕拉迪公司(借方、甲方)、帕拉迪集團有限公司(保證方,丙方)簽訂了 《借款合同》,其中約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借款10萬元,借款時間為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7月29日,借款年利率為12%,利息按月支付,丙方作為保證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等;2014年4月18日,楊某再次購買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12萬元,但帕拉迪公司未能按時足額還本付息。之后,以“帕拉迪”為字號的一系列關聯公司因涉嫌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被公安機關刑事立案。2016年5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5)滬一中刑初字第167號”(以下簡稱:“167號案”)《刑事判決書》,判決保險公司業務員陳某甲、談某、陳某乙、李某因參與帕拉迪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對外借款事宜而分別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依法判處相應刑事處罰;扣押在案的贓款發還各被害人,同時責令各名被告人退賠其余不足部分發還各名被害人。2017年5月17日,原告楊某收到法院發還的退贓款11,319.00元。
原告楊某認為:被告對業務員具有管理不嚴的過錯責任,因被告管理層未能及時發現并制止業務員推銷第三方公司理財產品的行為,才導致原告上當受騙并最終遭受了嚴重損失;原告之所以購買帕拉迪公司的理財產品是因為向其推銷該產品的被告是保險分公司的業務員,原告出于對被告公司的信任,以為這是保險公司推銷的產品從而信任并最終決定予以購買。原告的損失與被告管理不嚴的過錯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故被告應當對原告的損失承擔次要(30%)的賠償責任,原告兩次購買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共計投入本金人民幣22萬元未能收回,因此請求判令保險公司賠償其經濟損失66,000.00元。
被告保險公司辯稱:1)保險公司承擔管理責任的前提是被管理的對象營銷的是保險公司自身的產品,或者與保險公司有實際關聯的產品,但楊某投資的產品并非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或關聯產品,而是楊某獨立自主向第三方理財公司購買的理財產品。相關證據顯示楊某擁有豐富的理財投資經驗,屬于成熟的投資者,對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的投資風險具有較高的認識和判斷能力,并且應當能夠分辨出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并非保險產品或者是與保險公司有關聯的產品。楊某在決定投資購買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時明知或應當知道該產品的性質屬于企業經營借款,還款義務人為屬于借款人和保證人的帕拉迪公司及其集團公司,與保險公司不存在任何關系。2)即使李某、談某等人向楊某推薦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的行為客觀存在,這最多也只是楊某得知帕拉迪產品的一個途徑和原因,但在隨后的業務接洽和合同簽訂過程中,楊某應知曉其購買的是帕拉迪公司這個獨立法人的產品,楊某的購買決定是基于自身對于投資和風險承擔等因素獨立考量后作出的決策。3)保險公司提交的大量證據足以證實其對于李某、談某等保險業務員的管理適當,已經盡到相應的管理義務,并不存在楊某所稱的明知違規推銷帕拉迪產品而故意放任或縱容等過錯情況,因而保險公司無需對楊某因購買帕拉迪產品所遭受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4)對于因購買帕拉迪產品而遭受的損失,楊某還有其他救濟途徑行使求償權但未曾行使,其實際所遭受的損失至今無法確定,故楊某不具備向保險公司索賠的條件。
一審法院查明:陳某甲曾以保險公司營業部名義組織客戶參加酒會、一日游等活動,在活動上陳某提到帕拉迪公司的理財產品,然后由業務員(談某、李某、陳某乙等)向客戶具體介紹推銷。上述活動是陳某甲組織的,宣傳單是李某個人印制的。根據保險公司內部相關規定,組織客戶活動應當向保險公司進行申請、備案等,但陳某甲組織的上述活動并未向保險公司事先申請、備案,也未在事后要求報銷費用。而且,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都簽訂了《個人業務保險營銷員委托合同》,業務員承諾:“本人保證不兼職從事保險營銷活動,不代理再保險業務,不兼做保險經紀業務,不為其他保險公司代理保險業務,不從事傳銷、直銷等其他職業。”2014年5月起,保險公司又制訂、頒布一些系列規章制服嚴禁業務員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全公司對防范、打擊非法集資行為進行了培訓,并對從事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的業務員進行了相關處罰。
經一審法院傳喚,業務員談某作為證人到庭作如下陳述:帕拉迪理財產品是陳某甲外部找來的業務,要求業務員幫忙推銷,業務員賺取傭金。陳某甲組織安排過酒會等活動,是否向上級公司報備不清楚,在活動中陳某甲介紹過帕拉迪產品,當時陳某甲沒有說帕拉迪產品是保險公司的產品。談某本人在向客戶介紹帕拉迪產品時并未說過帕拉迪公司與保險公司有合作關系。
一審法院還在審理中調取了167號案的庭審筆錄,并當庭向雙方當事人出示。雙方當事人均表示對庭審筆錄無異議。庭審筆錄記載,檢察官詢問被告人時,陳某甲、談某、李某、陳某乙均表示向客戶介紹帕拉迪公司時并未說過帕拉迪公司與保險公司有合作關系。同時167號案刑事判決查明部分載明:陳某甲、談某、李某、陳某乙介紹帕拉迪產品時并未說過帕拉迪公司與保險公司有合作關系。
一審法院認為:楊某基于侵權要求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主要爭議焦點是保險公司對保險業務員從事營銷活動中對客戶造成的損失是否需要基于管理責任承擔賠償責任。首先,保險公司承擔管理責任需要基于被管理的對象營銷的是保險公司自身的產品,或者與保險公司有實際關聯的產品。楊某購買帕拉迪公司的理財產品,合同是與帕拉迪公司簽訂的,合同標識清楚,且購買亦不是在保險公司營業場所,而是在帕拉迪公司和楊某家中用POS機刷卡購買,資金直接劃入帕拉迪公司所屬賬戶。在相關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刑事案件的調查中,也未揭示帕拉迪公司與保險公司之間存在業務往來或實際關聯。且刑事案件庭審筆錄及刑事判決中關于談某、李某等的供述均證明其在向客戶介紹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時沒有說帕拉迪公司是保險公司的協作單位,故楊某投資的產品并非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或關聯產品。其次,楊某認為自身是經保險公司業務員的推薦,基于對保險公司信用的信任而購買帕拉迪公司的產品。本案中,保險公司作為一家經營人壽保險產品的企業,本身不能開展資產管理業務,也不具有代銷其他理財產品的資質,結合上述的交易地點、方式和合同內容,楊某顯然沒有履行合理的注意義務,缺乏應有的審慎鑒別和判斷。即便是保險業務員最初的推薦使楊某產生某種信賴關聯,但在隨后的業務接洽和合同簽訂過程中,楊某作為普通投資者都應能產生正確的認知和判斷,應知曉其購買的是帕拉迪公司的產品,且知曉帕拉迪公司是獨立法人。故楊某所稱是基于對保險公司的信任購買帕拉迪公司的理財產品并沒有提供足夠證據,不予采信。再次,保險公司已盡到一般管理義務。保險公司與業務員之間是保險代理關系,與一般單位與員工之間的勞動關系有所不同,業務員應履行保險公司授權范圍內的義務行動,不得推銷第三方產品,業務員私下推薦帕拉迪產品,保險公司是無法得知的。保險公司制定了較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個人業務保險營銷員委托合同》中明確要求業務員承諾不同業競爭、不從事傳銷等其他職業,顯然保險公司是明確禁止業務員從事營銷本公司保險產品以外產品的,并要求員工作為一項鄭重承諾簽字,在前端管理上已盡到責任。保險公司在收到業務員推銷帕拉迪產品的舉報后也積極作出回應,制止業務員行為、發短信通知等。雖然四名業務員在將近一年的時間推銷帕拉迪公司的理財產品,保險公司未能及時發現并予以制止,但不能據此認定保險公司的管理行為與楊某投資損失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不構成侵權賠償。綜上,楊某認為保險公司管理不嚴構成侵權,依據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據此駁回了楊某的訴訟請求。
楊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了上訴。
二審法院對一審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同時經審理認為:首先,楊某購買的是理財產品,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相對方為帕拉迪公司。楊某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所購買的理財產品系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或關聯產品,亦無證據顯示保險公司與帕拉迪公司存在關聯。楊某作為投資者,在購買理財產品時,未盡審慎義務,理應自行承擔相應法律后果。其次,保險公司與其業務員之間形成的是保險代理關系而非勞動關系。保險公司已舉證證明其通過與業務員簽訂《個人業務保險營銷員委托合同》及制定有關管理制度來約束其業務員的業內行為。根據167號案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陳某等業務員招攬理財投資者的行為,已超出上述委托合同中約定的保險公司授權范圍。鑒于楊某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保險公司對其業務員的違法行為系明知,故楊某提出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
據此,二審法院駁回了楊某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本文所涉案例,可參閱(2017)滬0109民初32929號《民事判決書》、(2018)滬74民終29號《民事判決書》] 。事實上,因保險業務員推銷帕拉迪公司理財產品引發的投資者狀告保險公司侵權賠償案件,共有二十多起,判決結果均如本案。
二、關于認定保險公司是否應當為其員工私下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而對投資者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的關鍵事實和法律依據
上文所提案例一審和二審法院均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保險公司是否應對楊某的投資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以下是兩級法院均最終判決保險公司無需為楊某的投資損失承擔責任的關鍵事實和法律依據:
(一)保險公司承擔管理責任需要基于被管理的對象營銷的是保險公司自身的產品,或者與保險公司有實際關聯的產品,而本案中無證據證明客戶購買的理財產品系保險公司的保險產品或關聯產品。
(二)客戶為購買第三方理財產品而簽署的《借款合同》合同文件內容及簽約、劃款地點均未出現足以令客戶誤認為第三方理財公司與保險公司存在合作關系的內容。
(三)客戶應知曉其購買的是第三方理財公司這個獨立法人的產品,客戶的購買決定是基于自身對于投資和風險承擔等因素獨立考量后作出的決策。
(四)保險公司對于保險業務員的管理適當,已經盡到一般管理義務,不存在所謂的明知其違規推銷第三方理財產品而故意放任或者縱容等過錯情況,因而無需對客戶因購買第三方理財產品而遭受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三、對于保險公司而言,如何才能盡可能避免保險業務員私下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并由保險公司承擔投資者損失的責任?
(一)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簽訂《保險委托合同》時,應在合同中明確雙方形成的是委托代理關系而非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且禁止業務員代銷其他第三方理財產品。
建議保險公司在與保險業務員簽訂《保險委托合同》時應明確規定:雙方基于委托合同形成委托代理關系,不形成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且業務員的委托授權范圍僅限于保險營銷活動,只能從事《保險委托合同》約定的授權范圍即保險營銷活動。同時,應明確禁止業務員從事營銷本公司保險產品以外的產品,并要求業務員作為一項鄭重承諾簽字。
(二)保險公司應制定、頒布關于規范業務員營銷行為的管理文件,對于保險公司自身的宣講會、產品說明會等需嚴格把控,實施事前報備、事中管控、事后檢查。
建議保險公司應注重對公司保險營銷員的規范管理,嚴格要求營銷員合規誠信銷售保險產品,并對相關宣傳資料的制作、印刷和使用,以及各種形式的產品說明會等方面制訂嚴格規定和要求,明確要求所有的宣講會、產品說明會等都必須向公司總部申請報批,公司總部允許后才能召開,且宣講會、產品說明會的宣傳文件、主講人均需公司總部認可,同時應在全公司范圍內對所有保險營銷員進行培訓,介紹非法集資活動,明確禁止保險營銷員向客戶推銷第三方理財產品。
(三)通過發放宣傳材料、發送短信等方式加強對客戶展開關于非法集資活動方面的宣傳教育,通過多渠道向廣大客戶和投資者提示勿輕信非保險公司的第三方理財產品。
建議保險公司在投保單上印制明確警示,提示客戶勿輕信非保險公司的第三方理財產品,同時制作易拉寶、宣傳冊等宣傳資料,發放在各分支公司的營業場所,并針對第三方理財產品的風險問題向客戶發送提示短信,提醒客戶自覺識別和防范第三方理財產品的風險,以免上當受騙。
(四)若已經發現有業務員推銷第三方理財產品,保險公司應積極作出回應,對違規行為及時采取嚴肅查處并予公告。
建議當保險公司發現有保險業務員存在違規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時,應立即展開調查并在查實后予以嚴肅懲處并予公告,以儆效尤,并要求各分支公司對從事第三方理財活動的相關人員進行排查,以確保有效禁止業務員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同時在保險公司內部召開培訓,反復向保險營銷員宣傳P2P類產品的本質、發文明令禁止保險業務員銷售第三方理財產品。
上述案例以及關于保險公司管理保險業務員的經驗總結,相信對于其他金融企業來說也有相應的借鑒作用。
(作者簡介:王曉英,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法學博士,法案交流郵箱:wangxiaoying@allbright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