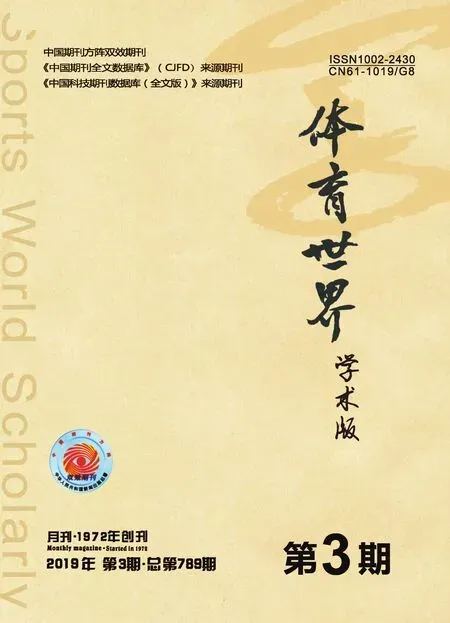我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歷史回顧與發展展望
何石卿
(吉首大學 體育科學學院,湖南吉首 416000)
1.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稱的確立、學科性質及概念
“名副其實,名正言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稱的確立重要性不言而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10月頒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隨之正式成為官方術語和操作概念,在人類文化遺產的范疇中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1]。民族傳統體育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門學科,其名稱是兩種交叉學科經過長期的研究、互動的探討、反復論證所達成的共識,并被官方認定的名詞。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學科在體育領域的應用,是兩者的交叉學科,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派生分支學科,其學科性質是應用學科。萬義[2]認為民族傳統體育就是指特定的民族在一定的范圍內開展的、從傳統社會沿襲下來的、具有濃厚民族文化色彩的、以身體運動為形式,追求身體健康為目的的一種獨立的社會文化形態。非物質文化遺產,2005年,中國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3]中對其定義: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基于此,本文認為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學科是一種包含與被包含和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類屬于體育人類學和體育社會學交叉范疇,具有高度綜合性的學科。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存在概念不清的現狀,學界基本遵循了一致地解釋路徑,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體育”與“非物質文化遺產”2個概念的交織,該類別文化遺產必須同時滿足“體育”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國內外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體育”概念與內涵的解讀不盡相同,至今沒有形成共識[4-6]。本文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是研究民族傳統體育的民俗文化、體育技能、表演娛樂、族群認同等人類社會文化的科學。
2.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有人從種類的角度,把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對象確定為:1.研究傳承人,關注傳承人認定制度,傳承人的身份認同研究等;王書彥,韋啟旺[7]等在《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認定制度探析》中說到:傳承人評審標準模糊、依據來源單一,對瀕危項目及傳承人關注旁落,屬地申報原則對傳統武術類體育非遺項目傳承人保護帶來了一定困擾。2.研究民俗文化,增強民族認同感,增進民族凝聚力;陳利紅[8]在《論民族傳統體育對族群建構的文化意義—以仡佬族、彝族和傣族為例》中認為民族傳統體育強化了族群的圖騰信仰和親祖意識,喚起族群的習俗情感和歷史記憶,培育并傳遞族群的文化心理結構與行為模式。3.研究民族體育項目,傳承與保護民族體育項目,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同時還要預測體育保護與傳承發展趨勢。如春潮[9]在《我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認為成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門機構、保護好傳承人、建立分級保護體系以及以農村和學校為傳承源是當前開展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應采取重要策略。
也有人從研究層次上,把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分成宏觀、中觀、微觀。宏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是從全社會或整個國家的視角出發,以一些宏大的、整體的體育非遺理論問題為研究對象,強調包容性、概括性和整體性,比如白晉湘、萬義和龍佩林[10]發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綱》提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治理體系,實現政府與民眾參與主體的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區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項目群的體育非遺為研究對象,萬義,胡建文和白晉湘[11]《苗族鼓舞文化生態變遷的人類學研究—湘西德夯的田野調查報告》指出民俗體育保護要完善現代體育價值理念,注重文化生態的活態保護,深化政府社會公共政策,保護和教育相結合,增強內源動力。微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是以對某一項目、單個因素或最小體育非遺單位集合體進行的具體研究,白晉湘[12]《少數民族聚居區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建構研究—以湘西大興寨苗族搶獅習俗為例》提出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建構模式。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理出發,結合體育科學特征,筆者認為把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研究對象從宏觀、中觀、微觀分類更合理,因為研究對象從縱向到橫向都有涵蓋,條理清晰,可行性強。
3.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內容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根據不同視角研究的觀點,總結概括如下四大方面:1)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與內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是這樣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眾或某些個人視為其文化財富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活動、講述藝術、表演藝術、生產生活經驗、各種手工藝技能以及在講述、表演、實施這些技藝與技能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工具、實物、制成品以及相關場所。”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研究;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與生俱來具有歷史認識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與社會價值。萬義[13]在《村落社會結構變遷中傳統體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彌勒縣可邑村彝族阿細跳月為例》中闡述:以可邑村彝族阿細跳月為調查個案,采用質的研究范式,分析由傳統走向現代進程中傳統體育的演進規律及其影響因素,探尋村落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路與途徑。3)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項目分類研究;白晉湘,萬義和龍佩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綱》中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征程和新路徑。4)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變遷,旅游開發;盧世菊,柏貴喜[14]在《民族地區旅游扶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調發展研究》中認為相關管理部門應該多措并舉推動民族地區旅游扶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可持續協調發展。
4.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方法
由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派生分支學科,筆者認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的使用需要統籌規劃,合理運用,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方法有:文獻資料法、田野調查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數量統計法等。
文獻資料法:白晉湘,萬義和龍佩林[15]在《探尋傳統體育文化之根,傳承現代體育文明之魂—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民族傳統體育研究述評》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等研究方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演進歷程、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等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歸納分析。筆者認為,文獻資料法是研究的基礎,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參考文獻為基礎,在總結前輩的基礎上,創新思考,提出自己的觀點。
田野調查法:學者萬義是相當嫻熟田野調查法的使用者,其在《體育科學》上發表的代表性論文《村落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的文化生態序研究—“土家族第一村”雙鳳村的田野調查報告》、《少數民族原始宗教與身體運動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態學分析—東巴跳與達巴跳的田野調查報告》和在《北京體育大學學報》上發表的論文《村落族群關系變遷中傳統體育社會功能的衍生研究—蘭溪古寨勾藍瑤族長鼓舞的田野調查報告》是田野調查法的典型代表作。筆者認為,田野調查法是針對體育人類學特點主流的研究方法,該研究方法通過實地調研,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確保了材料的真實性,也可以理解為“活態”研究方法。
訪談法:汪雄,杜寧[16]在《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身份認同研究》中基于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對云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身份現狀進行實地考察,采用“主位”與“客位”相結合的原則,對調查獲取的口述史資料進行質性研究。筆者認為,訪談法可以直接從民間了解最真實、最直接的口述信息等,通過交談,可以了解當地人對民俗文化的觀點。
問卷調查法:劉衛華,龍佩林和萬義[17]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湘西苗族武術文化保護的思考》運用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對湘西苗族武術的起源、現狀和制約因素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提出湘西苗族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終極目標不是單單的傳承和發展,而是應該在保護與開發、傳統與現代之間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筆者認為,通過無記名問卷調查可以了解最真實的看法,及前沿調查研究信息。
數量統計法:王卓[18]在《2003-2011年我國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中采用數理統計法,對2003-2011年我國國內發表的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文獻的年度變化、作者情況、期刊來源、主題特征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目前我國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存在研究方法簡單化、研究內容表面化、研究成果單一化等問題。筆者認為,通過數據分析,綜合對比可以有效刷選更實用的東西,綜合對比,形成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筆者認為,通過采用合理高效的研究方法,綜合交叉學科的交叉統一研究,“對癥下藥、量體裁衣”,研究成果將更加科學。
5. 展望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全球化,傳統民族體育緊跟時代步伐,走進體育現代化時代,各族人民開始從單一注重物質文明轉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追求。本文認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在于從不同的視角深入研究,追求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對傳統觀點敢于科學反駁,以“零和思維”開拓創新,開放“接地氣”的民間組織形式,形成新時代我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脈絡,實現政府與地方、官方與民間相結合,促進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高速科學發展,成為繁榮全世界各民族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