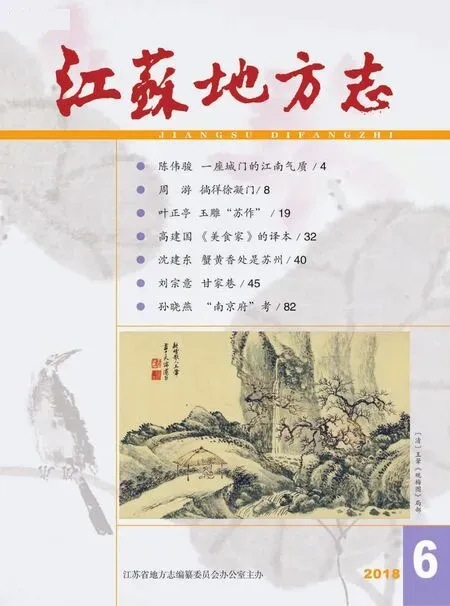玉雕“蘇作”
◎葉正亭

良緣玉雕工作室/圖
中國最好的玉是新疆和田籽料。何為“籽料”? 那是夾生在海拔3500米以上高昆侖山脈山巖中的和田玉原石經過地質運動和冰川運動剝解為大小不等的碎塊,這些碎塊經過雨水、雪水沖刷,流入玉龍喀什河中,又經由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年的沖刷,才形成了和田玉籽料。
中國最好的玉石雕工在江南。“揚州工”是一支,但最著名的當數蘇州玉雕,史稱“蘇作”。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對“蘇作”有如此評價:“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這其中,又以陸子岡最為著名,《蘇州府志》記載:“陸子岡,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其琢玉技藝高超絕倫,可謂巧奪天工。聞名于世的“子岡牌”,便是因他所制的玉牌而得名的。所謂“子岡牌”,其形若方形或長方形,一般都在4×6 厘米左右,故子岡牌又稱“四六牌”,寬厚敦實。其內容通常是一面雕刻文人山水畫,另一面鐫刻詩文印章,高雅脫俗。子岡牌好落款,其實這也體現了蘇州工匠“文者自負”的精神。但就因為落個款,最終竟要了陸子岡的性命。據載,因為陸子岡技壓群工,盛名天下,上到皇帝大臣,下到普通商紳,無不追捧他的作品。萬歷皇帝曾讓陸子岡雕琢一把玉壺,按照規定不能落款,但陸子岡還是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玉壺的壺嘴里,被人告發,惹怒了皇帝,終以欺君之罪被處死。
陸子岡雖逝,但玉器生產在蘇州已快速發展,形成氣候,清道光年間及至全盛,乾隆年間,蘇州琢玉作坊更是多達八百三十多戶,大街小巷,隨處可聞“沙沙”的琢玉聲。閶門吊橋兩側,玉市鱗次櫛比。乾隆帝曾贊曰:“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當時,玉器行會就設在專諸巷內的周王廟,每年農歷九月十三至十六,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著自己最精心的杰作作為祭祀供品去陳列,斯時,同行相互觀摩,各路客商云集,市民爭相觀摩,熱鬧異常。

因蘇州玉工云集、技藝高超,從乾隆二十九年開始,大量的山料被運送到北京,乾隆皇帝命內務府畫樣之后都打算運往蘇州雕刻,但由于玉料沉重,過長江不便,便將山料卸于揚州,再從蘇州抽調玉工到揚州雕刻,由此,蘇州工匠帶出了揚州工匠,形成了“揚州工”。揚州工偏重大件,蘇州工則專注于“中小件”的研究,鑄就了“蘇作”精細雅潔的風格特征:精在用料,細在做工,雅在文化,潔在設計。
始于明朝的“蘇作”玉雕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如今的蘇州玉雕不僅繼承了傳統,更可貴的是在傳承中不斷開拓創新,形成了“新蘇作”,大批能工巧匠如雨后春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楊曦、蔣喜等。楊曦是“新蘇作”的領頭人、創作型琢玉藝術家,他的創作不拘泥于傳統,不重復自己,作品《大音希聲》《自在觀音》《秋語江南系列》等,無不體現著他對于藝術創新的堅持和自我要求。他用自己個性化、藝術化的玉雕語言,為“蘇作”注入新思想。
蔣喜以雕琢仿古件著稱,他創新在于把傳統題材向“蘇作”延伸。他對古韻玉雕造詣頗深,設計的玉雕作品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精神。他認為古韻玉雕并非是一味模仿和拼湊古代的形制及符號,更多的是要表現和提煉出古韻與哲思。他的作品《云天下》取形于古代玉器中的器形——玉琮和玉璧,采用了它內圓外方的特色,又大膽地雕琢出“金字塔”的造型,用以溝通天地,表現天地之間宏大的底蘊。蔣喜于在這些繁雜的元素之中拿捏合度,將它們恰如其分地重新組合,既含傳統意趣又具當代審美,無愧是“傳統蘇作,時代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