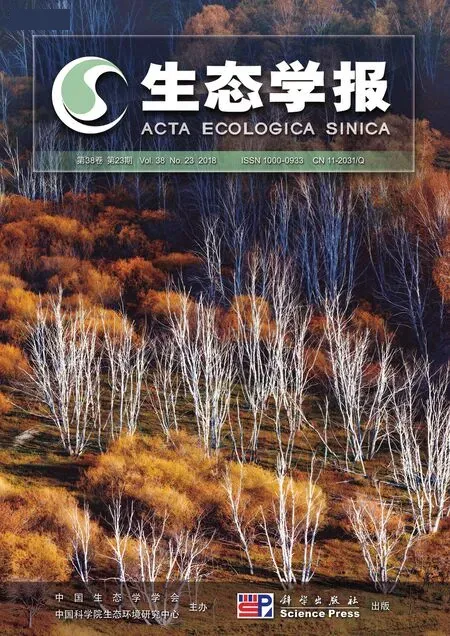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進(jìn)展
胡熠娜,彭 建,,*,劉焱序,王 曼,王仰麟
1 北京大學(xué)城市與環(huán)境學(xué)院, 地表過程分析與模擬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學(xué)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規(guī)劃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 城市人居環(huán)境科學(xué)與技術(shù)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深圳 518055 3 北京師范大學(xué)地理科學(xué)學(xué)部, 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tài)國(guó)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875
隨著世界經(jīng)濟(jì)、人口的快速增長(zhǎng),資源枯竭、環(huán)境惡化、生態(tài)失衡等一系列問題不斷突顯出來(lái),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增長(zhǎng)和區(qū)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造成了嚴(yán)重威脅[1]。如何協(xié)調(diào)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資源節(jié)約和環(huán)境保護(hù)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已成為當(dāng)今世界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問題,也是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作為衡量自然資源滿足人類需求的效率的重要指標(biāo),生態(tài)效率這一概念不但能夠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的核心內(nèi)涵,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資源環(huán)境保護(hù)的和諧統(tǒng)一,也能夠定量刻畫人類與自然的耦合程度。時(shí)至今日,生態(tài)效率已成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的重要實(shí)踐探索,也為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定量評(píng)估提供了重要方法參考。
生態(tài)效率概念由Schaltegger和Sturm于1990年首次提出,認(rèn)為生態(tài)效率是產(chǎn)品或服務(wù)增加的價(jià)值與增加的環(huán)境影響的比值[2]。隨后,國(guó)外眾多學(xué)者和機(jī)構(gòu)對(duì)生態(tài)效率的概念進(jìn)行了辨析,并將其應(yīng)用到產(chǎn)品、企業(yè)、產(chǎn)業(yè)、區(qū)域等多個(gè)層面[3- 6]。自Claude Fussler[7]將生態(tài)效率概念引入中國(guó)以來(lái),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在生態(tài)效率的評(píng)價(jià)與應(yīng)用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8- 10]。整體而言,研究?jī)?nèi)容方面,國(guó)外學(xué)者主要關(guān)注生態(tài)效率的概念界定和模型優(yōu)化,而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則更多關(guān)注于對(duì)評(píng)價(jià)框架的改進(jìn)。理論應(yīng)用方面,國(guó)外學(xué)者主要關(guān)注產(chǎn)品、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等方面,區(qū)域?qū)用娴膽?yīng)用相對(duì)較少;而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在產(chǎn)品、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等層面研究較少,更多關(guān)注于對(duì)區(qū)域、城市以及國(guó)家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等大尺度的研究[11- 13]。
產(chǎn)品、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的生態(tài)效率評(píng)估能夠?qū)崿F(xiàn)產(chǎn)品生產(chǎn)過程中的資源投入與環(huán)境損耗最小化、經(jīng)濟(jì)效益最大化,從而有效提升特定行業(yè)的可持續(xù)生產(chǎn)水平[14]。而在區(qū)域?qū)用孢M(jìn)行生態(tài)效率評(píng)估,能夠客觀評(píng)估區(qū)域整體的資源配置、環(huán)境質(zhì)量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的效率關(guān)系,對(duì)于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意義更為重大。同時(shí),從中、微觀尺度的產(chǎn)品,企業(yè)到宏觀尺度的產(chǎn)業(yè)、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中的關(guān)注對(duì)象各有側(cè)重。尤其是宏觀尺度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將區(qū)域內(nèi)部所有產(chǎn)品、企業(yè)、產(chǎn)業(yè)等要素看作一個(gè)整體,綜合評(píng)估區(qū)域內(nèi)的資源-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效率,較其他層面具有顯著差異。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將不同層面的生態(tài)效率混雜而談,鮮有專門針對(duì)區(qū)域?qū)用嫔鷳B(tài)效率研究的系統(tǒng)梳理。基于此,本文在明晰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概念內(nèi)涵的基礎(chǔ)上,重點(diǎn)總結(jié)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近年來(lái)的研究進(jìn)展,并提出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重點(diǎn)發(fā)展方向。
1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概念內(nèi)涵
生態(tài)效率一詞譯自英文單詞eco-efficiency。其中,eco-既是生態(tài)學(xué)ecology的詞根,又是經(jīng)濟(jì)學(xué)economy的詞根,而efficiency則表示“效率、效益”的含義[15]。因此,生態(tài)效率應(yīng)兼顧生態(tài)和經(jīng)濟(jì)兩個(gè)層面,從社會(huì)-自然耦合的視角來(lái)定量刻畫區(qū)域發(fā)展過程中的經(jīng)濟(jì)和自然協(xié)調(diào)程度。
在Schaltegger和Sturm最初定義的基礎(chǔ)上,1992年世界持續(xù)發(fā)展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huì)(WBCSD)在向聯(lián)合國(guó)環(huán)境發(fā)展大會(huì)提交的《改變航向:一個(gè)關(guān)于發(fā)展與環(huán)境的全球商業(yè)觀點(diǎn)》報(bào)告中將生態(tài)效率界定為“通過提供具有價(jià)格優(yōu)勢(shì)的服務(wù)和商品,在滿足人類高質(zhì)量生活需求的同時(shí),將整個(gè)生命周期中對(duì)環(huán)境的影響降到至少與地球的估計(jì)承載力一致的水平上”[16]。這一認(rèn)知揭示了生態(tài)效率兼顧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資源環(huán)境保護(hù)兩方面,自此生態(tài)效率概念被廣泛認(rèn)識(shí)和接受。
隨后,眾多研究機(jī)構(gòu)分別從滿足人類需求、降低資源消耗、減少環(huán)境破壞等不同視角,提出了一系列生態(tài)效率的概念內(nèi)涵(表1)。盡管各組織機(jī)構(gòu)對(duì)于生態(tài)效率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其關(guān)鍵詞均包含了人類需求、承載力、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等方面,因此其核心內(nèi)涵具有共同性,均是從投入-產(chǎn)出視角,以資源環(huán)境影響最小化和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最大化為目標(biāo),秉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不可以犧牲資源環(huán)境為代價(jià)的理念。
基于生態(tài)效率概念的核心內(nèi)涵,可以認(rèn)為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直接面向區(qū)域這一經(jīng)濟(jì)-資源-環(huán)境復(fù)合系統(tǒng),是對(duì)其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的度量[25],其實(shí)質(zhì)是通過區(qū)域內(nèi)資源和資本的高效配置,在區(qū)域經(jīng)濟(jì)效率最大化的同時(shí),使得其對(duì)資源環(huán)境影響最小,從而達(dá)到區(qū)域內(nèi)部經(jīng)濟(jì)和環(huán)境和諧共贏,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
2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進(jìn)展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是對(duì)區(qū)域內(nèi)部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之間協(xié)調(diào)程度的度量。評(píng)估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有助于揭示區(qū)域的發(fā)展質(zhì)量,從而指導(dǎo)區(qū)域的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國(guó)外學(xué)者對(duì)于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研究主要圍繞概念內(nèi)涵展開,從不同視角對(duì)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定義進(jìn)行解析,有效推動(dòng)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理論發(fā)展。隨后,大量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定量研究(圖1),從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環(huán)境投入的單一比值方法,到DEA等模型方法的客觀評(píng)估,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評(píng)估逐漸成熟和完善,為定量化表征區(qū)域的發(fā)展質(zhì)量和可持續(xù)水平提供了技術(shù)支撐。同時(shí),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逐漸從靜態(tài)的生態(tài)效率研究轉(zhuǎn)變?yōu)殚L(zhǎng)時(shí)間序列的空間動(dòng)態(tài)評(píng)價(jià),揭示了生態(tài)效率的區(qū)域差異和演變規(guī)律。此外,部分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影響因素和驅(qū)動(dòng)機(jī)理的研究,從而為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提升提供理論依據(jù)。

表1 生態(tài)效率概念內(nèi)涵對(duì)比

圖1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進(jìn)展Fig.1 Progress on regional eco-efficiency research
2.1 研究方法:從單一比值到模型模擬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準(zhǔn)確評(píng)價(jià)是有效提升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水平的重要前提。對(duì)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評(píng)價(jià)方法的研究是生態(tài)效率研究中的熱點(diǎn),如何設(shè)計(jì)適當(dāng)?shù)姆椒ㄊ沟迷u(píng)價(jià)更為客觀合理是一大核心問題[17]。目前,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為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比值法和模型法兩大類。
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比值法基于WBCSD對(duì)生態(tài)效率的定義,從投入-產(chǎn)出視角出發(fā),采用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和環(huán)境負(fù)荷的比值來(lái)衡量。然而,學(xué)界目前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和環(huán)境負(fù)荷的定量表征尚未完全統(tǒng)一: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方面,地區(qū)GDP是應(yīng)用最為廣泛的指標(biāo)[26-27],也有學(xué)者應(yīng)用綠色GDP[28]、工業(yè)生產(chǎn)總值[29]等指標(biāo);環(huán)境負(fù)荷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從資源消耗和環(huán)境影響兩個(gè)方面分別選取多個(gè)代表性指標(biāo)。例如,黃和平[30]選取能源消耗、用水、建設(shè)用地等作為資源消耗指標(biāo),COD排放、SO2排放和固體廢棄物排放作為環(huán)境影響指標(biāo)對(duì)江西省進(jìn)行生態(tài)效率研究。然而,多要素的融合往往存在權(quán)重設(shè)定主觀的問題。因此,部分學(xué)者將生態(tài)足跡模型、能值分析、物質(zhì)流分析等方法引入生態(tài)效率研究。例如,季丹[31]基于生態(tài)足跡方法構(gòu)建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模型,分析了我國(guó)30個(gè)地區(qū)的生態(tài)效率。李名升和佟連軍[32]應(yīng)用能值分析和物質(zhì)流分析構(gòu)建了生態(tài)效率指標(biāo),在吉林省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Liu等[33]基于城市物質(zhì)代謝原理評(píng)估了廈門市生態(tài)效率。
隨著技術(shù)的革新與發(fā)展,為克服權(quán)重設(shè)定主觀等問題,學(xué)者們提出了諸多模型方法。目前應(yīng)用較廣泛的模型主要是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該模型由Charnes、Cooper和Rhode[34]于1978年提出,能夠在不設(shè)定具體函數(shù)形式的情況下評(píng)價(jià)“多投入多產(chǎn)出”模式下決策單元間的相對(duì)有效性,不受限于特定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假設(shè),且有效克服了權(quán)重設(shè)定的人為主觀性。CCR模型等早期的DEA模型中的指標(biāo)體系基于投入-產(chǎn)出視角通常以經(jīng)濟(jì)增加值為產(chǎn)出,資源和環(huán)境負(fù)荷為投入。隨著混合DEA模型、超效率DEA等一些新的模型出現(xiàn),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準(zhǔn)確性大大提高。這些模型雖然仍以資源消耗作為投入、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作為產(chǎn)出,但通常將環(huán)境影響作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過程中的負(fù)面產(chǎn)出,而不再作為投入,從而更真實(shí)地反映實(shí)際生產(chǎn)過程[35-36]。例如,Huang等[37]基于改進(jìn)的DEA模型以GDP為期望產(chǎn)出,以資本、勞動(dòng)力、土地和能源為資源投入,以二氧化硫、廢水廢氣等排放作為非期望產(chǎn)出,定量分析了中國(guó)2000—2010年的生態(tài)效率演變。總的來(lái)說(shuō),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研究指標(biāo)逐漸由單要素評(píng)價(jià)向多要素評(píng)價(jià)轉(zhuǎn)變,評(píng)價(jià)方法也逐漸由主觀賦權(quán)評(píng)估趨向客觀模型模擬。
2.2 研究對(duì)象:從靜態(tài)評(píng)估到時(shí)空動(dòng)態(tài)
從時(shí)空尺度來(lái)看,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靜態(tài)和動(dòng)態(tài)的視角,在不同時(shí)空尺度上進(jìn)行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從而探究不同區(qū)域的空間差異性和長(zhǎng)時(shí)序演變規(guī)律。相較而言,早期的研究多為靜態(tài)評(píng)價(jià),主要基于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比值法和DEA等模型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從空間維度上進(jìn)行細(xì)部差異分析。例如,王波和方春洪[38]基于因子分析評(píng)價(jià)了我國(guó)各省2007年的生態(tài)效率,并按東、中、西三大經(jīng)濟(jì)帶進(jìn)行比較分析。

不過,σ收斂系數(shù)、Malmquist指數(shù)等傳統(tǒng)的數(shù)量統(tǒng)計(jì)模型均建立在區(qū)域空間實(shí)體不存在任何空間關(guān)聯(lián)的假設(shè)前提之下[43]。事實(shí)上,生態(tài)效率在區(qū)域之間存在的擴(kuò)散和極化效應(yīng),可以縮小或擴(kuò)大生態(tài)效率的區(qū)域差異。因此,一些學(xué)者嘗試?yán)媚m指數(shù)(Moran′s I)等方法探究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空間聯(lián)系。例如,任宇飛和方創(chuàng)琳[44]在對(duì)京津冀地區(qū)生態(tài)效率進(jìn)行測(cè)度的基礎(chǔ)上,通過全局莫蘭指數(shù)發(fā)現(xiàn)2006—2014年京津冀地區(qū)縣域單元生態(tài)效率存在空間正向集聚趨勢(shì),且鄰域單元生態(tài)效率的差距有所縮減;胡彪和付業(yè)騰[45]運(yùn)用空間自相關(guān)分析了中國(guó)省域生態(tài)效率全局及局域的空間差異,指出中國(guó)生態(tài)效率相近的區(qū)域在空間上表現(xiàn)出波動(dòng)的集聚現(xiàn)象。這些研究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空間地理關(guān)聯(lián),直接指向了對(duì)于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空間分異及其演化驅(qū)動(dòng)機(jī)制的探討。
2.3 研究?jī)?nèi)容:從效率測(cè)度到機(jī)理認(rèn)知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概念的辨析、測(cè)度方法的優(yōu)化和評(píng)價(jià)模型的構(gòu)建等內(nèi)容。對(duì)于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分析尚停留在簡(jiǎn)單的數(shù)值分析,缺少對(duì)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影響因素的探究,更沒能揭示不同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差異的形成機(jī)理。隨著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發(fā)展,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從關(guān)注數(shù)值評(píng)估結(jié)果轉(zhuǎn)向?qū)ι鷳B(tài)效率格局變化的驅(qū)動(dòng)機(jī)理研究。例如,李在軍等[46]借助空間計(jì)量經(jīng)濟(jì)模型對(duì)中國(guó)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城市化水平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而第二、三產(chǎn)業(yè)比重的增加則屬于負(fù)向驅(qū)動(dòng)因素。潘興俠等[47]運(yùn)用空間統(tǒng)計(jì)和空間誤差模型對(duì)我國(guó)省域生態(tài)效率水平的空間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及其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定量分析,發(fā)現(xiàn)利用外資、人力資源、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生態(tài)效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環(huán)境污染治理投資和排污收費(fèi)制度對(duì)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Huang等[37]發(fā)現(xiàn)同種要素對(duì)于不同區(qū)域的貢獻(xiàn)有所差異,例如科技對(duì)于中國(guó)東、中、西和東北地區(qū)的生態(tài)效率增長(zhǎng)貢獻(xiàn)率分別為56.87%、58.21%、18.27%、62.19%。總的來(lái)說(shuō),區(qū)域發(fā)展規(guī)模和模式、資本和環(huán)境投入是當(dāng)前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驅(qū)動(dòng)機(jī)理分析的核心關(guān)注因素。
隨著驅(qū)動(dòng)機(jī)理研究的不斷深入,學(xué)者們發(fā)現(xiàn)既有研究盡管能夠在整個(gè)時(shí)間段內(nèi)揭示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jī)理,但沒能剝離不同城市化階段的差異。為了更有效地指導(dǎo)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城市化關(guān)鍵閾值的識(shí)別成為當(dāng)前研究的熱點(diǎn)。例如,李佳佳和羅能生[48]發(fā)現(xiàn)2003—2013年中國(guó)281個(gè)地級(jí)市城市規(guī)模對(duì)生態(tài)效率的影響呈現(xiàn)N型曲線的特征,生態(tài)效率隨城市規(guī)模的擴(kuò)張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對(duì)應(yīng)的兩大城市規(guī)模閾值分別為54.48、337.22萬(wàn)人。
3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展望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是認(rèn)識(shí)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度、衡量區(qū)域發(fā)展質(zhì)量的有效指標(biāo),能夠?yàn)閰^(qū)域可持續(xù)水平的提升路徑識(shí)別提供科學(xué)支撐。自生態(tài)效率概念提出以來(lái),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以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宗旨,不斷深化生態(tài)效率的概念內(nèi)涵與模型方法,取得了大量科學(xué)成果。然而,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缺少區(qū)域內(nèi)部精細(xì)化評(píng)估、階段性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的探究不足、研究結(jié)果的實(shí)際指示意義缺乏梳理,因此已有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仍難以有效指導(dǎo)不同發(fā)展階段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時(shí)空差異化管理。
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生態(tài)文明已成為基本國(guó)策,建設(shè)美麗中國(guó)和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是中國(guó)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目標(biāo),城市化面臨著轉(zhuǎn)型挑戰(zhàn)。同時(shí),隨著科技的進(jìn)步,大數(shù)據(jù)和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新時(shí)代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面臨新的機(jī)遇與挑戰(zhàn),需要在數(shù)據(jù)方法、研究?jī)?nèi)容和成果應(yīng)用等方面進(jìn)一步創(chuàng)新和拓展[49],為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文明戰(zhàn)略做出科學(xué)貢獻(xiàn)(圖2)。

圖2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重點(diǎn)研究方向Fig.2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n regional eco-efficiency
3.1 地理大數(shù)據(jù)的時(shí)空分析
已有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中使用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指標(biāo)主要依托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因此大多在行政區(qū)域尺度上展開[50-51]。然而,省、市等行政尺度上的研究無(wú)法清晰體現(xiàn)區(qū)域內(nèi)部的空間異質(zhì)性,且難以衡量空間關(guān)聯(lián)、溢出效應(yīng)等對(duì)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影響。另一方面,傳統(tǒng)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往往以年、月為間隔進(jìn)行統(tǒng)計(jì),時(shí)間連續(xù)性較差,嚴(yán)重制約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動(dòng)態(tài)監(jiān)測(cè)。
隨著GIS和遙感技術(shù)的發(fā)展,海量的遙感監(jiān)測(cè)和實(shí)時(shí)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為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在多尺度上的動(dòng)態(tài)空間化表達(dá)提供了重要依托。基于地理空間大數(shù)據(jù),經(jīng)濟(jì)和環(huán)境數(shù)據(jù)趨向于更加多元化和精細(xì)化,能夠更全方位地表現(xiàn)區(qū)域內(nèi)部經(jīng)濟(jì)和生態(tài)狀況以及區(qū)域間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從而大大提升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準(zhǔn)確性。同時(shí),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不再是一個(gè)單一數(shù)值,而是一個(gè)更為細(xì)致的空間化表達(dá)。因此,基于這種多尺度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表征,從空間異質(zhì)性視角探究復(fù)雜的空間關(guān)聯(lián)模式和不同的影響機(jī)理,將是未來(lái)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
3.2 多要素集成的模型研發(fā)
評(píng)價(jià)方法的發(fā)展和完善是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發(fā)展的重要支撐。從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指標(biāo)的比值評(píng)價(jià),到生態(tài)足跡、能值分析等一系列模型的引入,再到DEA等模型的發(fā)展,極大地提升了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客觀性[52]。基于地理大數(shù)據(jù)的內(nèi)在要求,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研究方法也需進(jìn)一步深化。一方面,如何有效融合海量的多源數(shù)據(jù),尤其是空間化的環(huán)境要素和基于統(tǒng)計(jì)的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之間的融合,為模型的研發(fā)提出了挑戰(zhàn)[53];另一方面,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往往在多時(shí)空尺度展開,如何構(gòu)建能夠適應(yīng)不同尺度、不同區(qū)域特征的可重復(fù)性較高的模型算法也是一大難點(diǎn)。同時(shí),社會(huì)系統(tǒng)是一個(gè)開放的系統(tǒng),其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不但對(duì)其內(nèi)部環(huán)境具有影響,也會(huì)對(duì)其外部環(huán)境產(chǎn)生影響,如何利用模型模擬這種空間溢出效應(yīng),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今后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中,有必要考慮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的合理空間化以及多要素多尺度的有效融合。同時(shí),應(yīng)對(duì)社會(huì)-自然耦合系統(tǒng)中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影響的復(fù)雜關(guān)系,借助人工智能等先進(jìn)數(shù)據(jù)分析手段模擬區(qū)域內(nèi)、外部環(huán)境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響應(yīng)機(jī)制,從而準(zhǔn)確評(píng)估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也將是區(qū)域生態(tài)效應(yīng)研究的重要方法創(chuàng)新。
3.3 區(qū)域城市化的重點(diǎn)關(guān)注
全球城市化進(jìn)程加快,城市區(qū)域承載了地球上超過50%的人口和80%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54],城市地區(qū)已成為實(shí)現(xiàn)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的關(guān)鍵區(qū)域[48]。然而,高速城市化進(jìn)程在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帶來(lái)了空氣污染、水質(zhì)惡化、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嚴(yán)重制約了城市地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55-56]。如何在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最大程度上保護(hù)好生態(tài)環(huán)境,即提高城市地區(qū)的生態(tài)效率,已成為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面臨的一個(gè)重要問題[57]。城市發(fā)展與生態(tài)效率演變之間的內(nèi)在機(jī)制,也是當(dāng)前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重點(diǎn)方向。因此,實(shí)時(shí)監(jiān)測(cè)城市發(fā)展不同階段的生態(tài)效率狀況,了解不同城市擴(kuò)張規(guī)模、不同城市發(fā)展模式和城市化不同階段的生態(tài)效率響應(yīng),對(duì)于科學(xué)指導(dǎo)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經(jīng)濟(jì)、資源等要素在全球或區(qū)域城市網(wǎng)絡(luò)中的流動(dòng)作用,城市逐漸從孤立的點(diǎn)狀城市轉(zhuǎn)向相互緊密聯(lián)系的面狀城市區(qū)域[58]。城市群已成為推進(jìn)中國(guó)新型城鎮(zhèn)化的重要空間主體,也是國(guó)家政策制定的熱點(diǎn)區(qū)域[59]。然而,城市群內(nèi)部發(fā)展極不平衡,甚至出現(xiàn)兩極化的狀況,核心城市與邊緣城市間的發(fā)展極不協(xié)調(diào)。針對(duì)這一問題,可通過分析城市群內(nèi)部經(jīng)濟(jì)、資源等要素的空間聯(lián)系,探究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影響的耦合關(guān)系,構(gòu)建城市群內(nèi)部的生態(tài)效率核算和預(yù)測(cè)模型,提出提升城市群整體發(fā)展質(zhì)量的對(duì)策建議,為推動(dòng)特大城市群地區(q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目標(biāo)做出科學(xué)貢獻(xiàn)。
3.4 面向可持續(xù)的區(qū)域管治
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新時(shí)代的主題,也是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60]。在當(dāng)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guó)提出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重大構(gòu)想,加快生態(tài)文明體制改革,建設(shè)美麗中國(guó)。在這種時(shí)代使命下,我們需要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道路。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核心就是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諧發(fā)展水平的探究,因此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提升是可持續(xù)發(fā)展最為有效的實(shí)踐之一。
進(jìn)一步的研究應(yīng)始終面向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將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從效率測(cè)度、影響因素識(shí)別、驅(qū)動(dòng)機(jī)制探究逐步深化到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提升路徑判定,使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成為區(qū)域管治的有效依托。同時(shí),根據(jù)不同區(qū)域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本底特征,高效配置區(qū)域內(nèi)外的資源和資本,從而進(jìn)行具有本底特色的、科學(xué)合理的差異化區(qū)域管治,為生態(tài)文明戰(zhàn)略的實(shí)施和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建設(shè)提供決策依據(jù)。
4 結(jié)語(yǔ)
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是衡量區(qū)域發(fā)展質(zhì)量的重要指標(biāo)之一,能夠?yàn)閰^(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生態(tài)文明戰(zhàn)略的實(shí)現(xiàn)提供重要的科學(xué)依據(jù)。目前,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的概念界定已較為統(tǒng)一,即從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和資源消耗、環(huán)境影響等層面衡量區(qū)域發(fā)展的協(xié)調(diào)程度。隨著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理論的成熟與完善,其研究方法也逐漸從經(jīng)濟(jì)投入/環(huán)境影響的簡(jiǎn)單比值評(píng)估發(fā)展為更為客觀的模型模擬。同時(shí),生態(tài)效率研究不再停留在靜態(tài)的單一區(qū)域?qū)用?而是轉(zhuǎn)向時(shí)空動(dòng)態(tài)評(píng)估,影響因素及其驅(qū)動(dòng)機(jī)理的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
隨著“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shù)的發(fā)展,從全球到地方多尺度長(zhǎng)時(shí)間序列的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將為不同區(qū)域發(fā)展水平的評(píng)估提供科學(xué)基礎(chǔ);借助人工智能等先進(jìn)數(shù)據(jù)分析手段處理多源的海量地理空間數(shù)據(jù)及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是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研究的技術(shù)導(dǎo)向;在全球高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關(guān)注特大城市群地區(qū),探究不同城市化規(guī)模、城市化模式和不同城市化階段的生態(tài)效率,對(duì)于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面向全球和區(qū)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測(cè)度不同區(qū)域的發(fā)展質(zhì)量,厘清不同區(qū)域的影響機(jī)理,將為區(qū)域的差異化管治和特定發(fā)展路徑的識(shí)別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