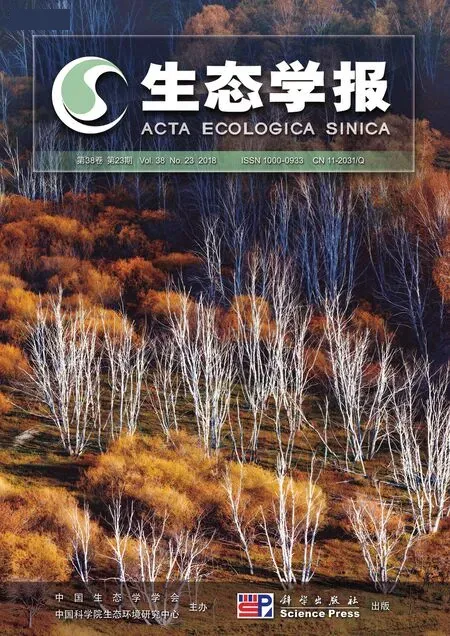種源地氣候對蒙古蕕光響應特性的影響
白雪卡,劉 超,紀若璇,沈 超,王襄平,*
1 北京林業大學, 林學院森林資源與生態系統過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083 2 北京林業大學, 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林木育種國家工程實驗室, 北京 100083
植物的光合作用是決定群落生產力大小的重要的生理生態過程[1]。植物對光強的響應一直是植物生理生態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2- 4]。光響應曲線是研究光強與凈光合速率關系的模型,通過分析光響應曲線可以得到植物的最大凈光合速率、光飽和點、光補償點、暗呼吸速率等重要的光合參數[5- 6],由此可以進一步了解植物的光化學過程及其對光合有效輻射的利用能力[7]。
同一物種長期在不同的環境中為了適應其特定的地理環境,會在表型和基因等方面產生一定程度的變異[8- 10],進而形成不同的種源特性。這是植物在自然選擇條件下的一種適應,這種適應對同一物種造成的改變,稱之為種內遺傳變異[11],造成這種遺傳變異的主要因素是遺傳和環境[12- 13]。由種源地環境的差異造成的種源變異主要體現:(1)表型可塑性(不同環境下基因表達不同);(2)基因型差異(不同環境導致的基因型差異);(3)兩者共同造成的。在不同環境下,植物葉片的光合等性狀會因種源地溫度、水分等環境氣候因子的差異而不同[14],對植物光合能力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影響[15- 16];而把不同種源的植物移植到同一生長環境下,相同的生長環境條件排除了環境梯度的影響,不同種源植物葉性狀表現出差異是由于原種源地環境差異造成的植物遺傳性基因變異,屬于遺傳因素。關于光合特征等葉性狀隨氣候梯度的變化,我國學者已經開展一些重要的研究[17- 18]。不過,這些研究是測定的是不同氣候條件下的植物,其光合等特征受到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的共同影響(包括氣候梯度和種源的影響)。開展在相同環境條件下不同種源的光合特征的研究,有助于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種源地的氣候條件如何影響植物的光合,從而深入理解光合作用的影響因素。
蒙古蕕(Caryopterismongholica)是唇形科(Lamiaceae)蕕屬(CaryopterisBunge)的抗旱性灌木[19- 20],常廣泛分布于內蒙古、甘肅、寧夏等沙丘荒野、干涸河床、礫石山地,是一種耐旱、耐寒兼具觀賞性的固沙綠化灌木[21- 23]。韓磊等[24]研究蒙古蕕的葉水勢與環境因素的關系,發現蒙古蕕葉水勢日變化與氣溫、光輻射強度、大氣相對濕度及土壤含水量顯著相關。謝乾瑾等[25]發現,干旱脅迫下蒙古蕕光合能力的下降是引起其生長減緩的重要原因。目前,研究學者對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光合速率與光強、小尺度環境因子的關系,而是研究大尺度的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如何共同影響植物光合作用,二者的相對作用大小如何等問題[26- 28]。
為了更好的研究遺傳因素對植物光合作用的影響機制,我們將8個不同種源蒙古蕕種植在同一環境條件下,排除外界環境因素差異的作用,對其光合作用光響應曲線特性進行研究,探討以下問題:(1)不同種源蒙古蕕之間的光合作用特性的差異性;(2)種源地氣候對蒙古蕕光合作用的影響作用大小。以期為今后蒙古蕕的研究,以及由環境差異造成的植物基因型差異對植物光合作用機制的影響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點為北京林業大學苗圃(40.01N°,116.34E°),氣候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均降水量在500—650 mm之間,降水集中在7—9月,占全年降水量70%;年均溫為11.8℃,全年最高溫度為37.5—42.6℃,最低溫度為-19.5—-14.8℃,7月溫度約為25.8℃。
1.2 實驗材料
試驗材料為蒙古蕕1年生扦插苗,種源來源及地理信息見表1。
于2016年3月下旬,在內蒙古、甘肅、寧夏等地采取生長良好蒙古蕕植株,剪取長度約為20 cm左右的枝條莖段,放于濕布中保濕,帶回北京。于4月上旬,將不同種源地的扦插枝條經0.1% 生根粉ABT1(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研究所)處理后扦插于450 mm×450 mm的花盆中,每個種源扦插苗木6盆,每盆3株,共18株。種植土壤為沙壤土(沙子∶壤土∶草炭土=45∶60∶60),與蒙古蕕的野外土壤條件相似,田間持水量19.11%,土壤容重1.273 g/cm3。

表1 蒙古蕕種源地基本情況
待苗木正常生長3個月后,于7月中旬選取生長良好、一致的苗木進行試驗,試驗時將每盆水分控制在田間持水量的70%—80%。
1.3 測定指標和方法
為了使本處理穩定在試驗設定土壤含水量內,采用烘干和稱重的方法測定土壤含水量,試驗時每天18:00按照預先模擬盆重與土壤含水量的關系,根據其變化補充消耗的水分。
實驗時期選擇2016年7月中旬連續晴天的上午(9:00—11:30)進行,此時段大氣平均氣溫約為(32±2)℃,光照強度約為(800±100)μmol m-2s-1,處于短期高溫、高光的環境條件。
每個種源隨機選擇3株健康植株,并選取成熟的向陽葉片進行測定,葉位為自上而下第7—8片葉。采用Li-Cor 6400便攜式光合作用測定系統(Li-Cor,USA)進行光響應曲線的測定,光源采用Li- 6400- 40B光源,CO2含量為(360±2) μmol/mol,流速為500 mmol/s,葉片溫度為(26±1)℃,空氣相對濕度約為70%。光合有效輻射梯度設置為: 2000、1800、1600、1400、1200、1000、800、600、400、200、100、50、20、10、0 μmol m-2s-1。采用Ye等[29- 30]的直角雙曲線修正模型進行曲線擬合,得到表觀量子效率(α1),最大凈光合速率(Pnmax),光飽和點(Isat)、光補償點(Ic)和呼吸效率(RE)等光合參數。
直角雙曲線修正模型表達式:
(1)
式中,α是光響應曲線的初始斜率,也稱為初始量子效率,β和γ為系數,I為光合有效輻射,Rd為暗呼吸速率。
最大凈光合速率(Pnmax)為:

(2)
光飽和點(Isat)為:
(3)
光補償點(Ic)為:
(4)
表觀量子效率(α1)為:
α1=Rd/Ic
(5)
式中,α1是光響應曲線在光補償點(Ic)處的斜率。
呼吸效率(RE)為:
RE=Pnmax/Rd
(6)
根據蒙古蕕各個種源地的經緯度,從ArcGIS 10.2中WorldCLIM 全球高分辨率氣候據庫[31]中提取出各樣地的50年月平均氣候數據(1950—2000),計算各個氣候因子大小。包括年均溫(MAT);年均降水量(MAP):反映水分供給情況;生長季降水量(GSP):4月到10月的降水量;生長季溫度(GST):4月到10月的平均溫度;最冷月均溫(MTCM):1月份的溫度,反映冬季低溫;潛在蒸發散(PET):反映年總熱量供給。
1.4 數據分析
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較(ANOVA-Duncan)方法,比較不同種源蒙古蕕光響應參數的差異。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種源地環境因子與各個光合參數的相關關系;并結合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ANOVA分析種源地氣候對蒙古蕕各個光合參數值的影響作用大小[32]。
一般線性模型ANOVA分析中氣候因子選取原則:
1)基于種源地環境因素之間的相關性(表3),及其與各個光合參數值的相關關系(表4),選取代表種源地水分、溫度和光三大元素的4個氣候因子:生長季降水(GSP)、生長季溫度(GST)、最冷月均溫(MTCM)和海拔(Altitude);
2)采用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模型對上述4個種源地氣候因子進行篩選,得到最終進入一般線性模型ANOVA分析中的氣候因子。
數據分析在Excel和R軟件(R3.2.2)中完成。
2 結果
2.1 不同種源蒙古蕕光合參數的差異

圖1 不同種源蒙古蕕的凈光合速率對光強的響應曲線 Fig.1 The response curve of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to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ryopteris mongholica provenances*圖中誤差線代表平均值的標準誤差
由圖1和表2可以得到,各個種源的蒙古蕕光合作用光響應曲線具有明顯差異,且波動范圍較大。從圖1中看,內蒙古蘇尼特左旗種源和內蒙古二連浩特種源的蒙古蕕最大凈光合速率(Pnmax)較高,甘肅民勤種源的較低。
表觀量子效率(α1)是光合過程中指示光能轉化效率的指標之一[33],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種源蒙古蕕光能轉化效率有著差異,α1的范圍為:0.0533—0.0754。甘肅民勤種源的表觀量子效率(α1)最小,內蒙古蘇尼特左旗種源的α1最大,且差異顯著,說明內蒙古蘇尼特左旗的蒙古蕕光能轉化率高。
最大凈光合速率(Pnmax)是植物最大光合速率與呼吸速率的凈值,它代表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反映了植物最大光合潛力[30],這8個種源的Pnmax范圍為:16.69—35.67 μmol m-2s-1,其中內蒙古蘇尼特左旗種源的Pnmax最大,甘肅民勤種源的Pnmax最小。內蒙古蘇尼特左旗、二連浩特與甘肅民勤種源的Pnmax差異顯著(P<0.05),其余5個種源Pnmax差異不顯著。
光飽和點(Isat)是衡量植物利用強光能力的一個指標,蒙古蕕的Isat的范圍為:1122.05—2939.01 μmol m-2s-1,波動范圍較大,其中內蒙古二連浩特種源Isat最大,甘肅民勤種源的最小,大多數種源的Isat在1800 μmol m-2s-1左右,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和大青山種源的Isat差異不顯著,說明這2個種源利用強光的能力較為接近。
光補償點(Ic)是指示植物利用弱光能力的一個指標,Ic越高,說明植物利用弱光的能力越弱[33]。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種源Ic(8.19 μmol m-2s-1)最低,該種源利用弱光的能力強;內蒙古正鑲白旗種源Ic(28.83 μmol m-2s-1)最大,其中內蒙古蘇尼特左旗、陜西神木與甘肅民勤種源Ic差異不顯著,說明這3個種源對弱光的利用能力相似。
暗呼吸速率(Rd)表示植物正常生理活動中提供的必須能量,大多種源Rd范圍在1—1.5 mol m-2s-1左右。Rd最小的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種源(0.46 mol m-2s-1),最大的是內蒙古正鑲白旗種源(1.92 mol m-2s-1),說明內蒙古正鑲白旗種源消耗的能量較多,有機質積累較少。
呼吸效率(RE)表示最大凈光合速率與暗呼吸速率的比值,呼吸是植物重要的生理過程之一。這8個種源的RE差異較大,其中RE最大的是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種源46.22 mol m-2s-1,最小的是內蒙古正鑲白旗種源12.15 mol m-2s-1,內蒙古二連浩特、大青山種源、陜西神木種源和甘肅民勤種源RE大致在20 mol m-2s-1左右,且差異不顯著,說明這4個種源的呼吸效率差異不大。

表2 由光響應曲線所得的光合參數值
* 表中數值為平均值±標準誤差; 表中字母為各個光合參數的一維方差分析進行的Duncan多重比較檢驗分組,同一光合參數的不同字母表示差異性顯著(P<0.05)
2.2 種源地氣候對蒙古蕕光合參數的影響
由表3可得,氣候指標間存在明顯的自相關,且溫度與經緯度密切相關。其中生長季溫度(GST)與年均溫度(MAT)、最冷月均溫(MTCM)相關性極顯著(P<0.001);生長季降水(GSP)與年均降水量(MAP)相關性也極顯著;海拔(Alititude)與緯度(Latitude)相關性顯著(P<0.01),與其他氣候因子相關性均不顯著。
由表4可以看出,Pnmax、Ic、Rd與經緯度顯著正相關(P<0.05),與海拔顯著負相關(P<0.05),說明隨著經緯度的增加和海拔的降低,蒙古蕕的光合能力逐漸增強。降水指標(MAP和GSP)與各個光合參數值的相關性均不顯著;溫度指標(MAT、GST和MTCM)與α1、Pnmax、Ic、Rd均顯著(P<0.05)負相關;潛在蒸發散(PET)只與α1顯著(P<0.05)負相關。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下生長時,蒙古蕕光合作用受種源地的地理位置(經緯度)、溫度(MAT、GST和MTCM)和海拔的顯著影響。

表3 環境之間的相關系數
* MAP: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MAT: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PET: Potential evaporation; GSP: Growth season precipitation; GST: Growth season temperature; MTCM: The temperature of coldest month; ***P<0.001; **P<0.01; *P<0.05

表4 種源地環境因素與各個光合參數值的相關系數
*MAP: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MAT: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GSP: Growth season precipitation; GST: Growth season temperature; MTCM: The temperature of coldest month; PET: Potential evaporation; ***P<0.001; **P<0.01; *P<0.05
通過一般線性模型(GLM)ANOVA分析(表5)可知,種源地氣候作為遺傳因素對蒙古蕕各個光合參數均有顯著作用,其解釋程度在16.65%—73.52%之間。其中,對α1、Pnmax、Ic和Rd解釋程度均大于40%,影響極顯著(P<0.001),但對RE的解釋程度最小(16.65%)。種源地氣候因子中,生長季降水(GSP)對Pnmax和Isat有影響,但不顯著;生長季溫度(GST)對α1、Pnmax、Ic和Rd的解釋程度為:26.66%—58.33%,影響均顯著(P<0.01);最冷月均溫(MTCM)解釋程度為18.35%,且影響顯著(P<0.05);海拔(Altitude)對Pnmax、Ic、Rd和RE的解釋程度在11.75%—16.65%之間,影響顯著(P<0.05)。溫度對蒙古蕕光響應參數的解釋程度大于海拔的。
3 結論與討論
光合作用對植物的生長發育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光是植物光合作用必不可少的因素[35],不同植物對光的響應不同,同一植物的不同種源對光的響應也不同[34, 36- 37]。本研究對8個不同種源的蒙古蕕光響應曲線的研究發現,蒙古蕕光合響應能力在不同種源間表現出明顯的不同,光響應曲線參數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表2),地理梯度上顯示從西到東,從南到北,蒙古蕕的光合能力逐漸增強,最東北部的內蒙古二連浩特和蘇尼特左旗種源蒙古蕕的Pnmax較大,最西部的甘肅民勤種源較小(表2、表4)。相關研究表明,同一植物不同種源為了生存,經過長期對各自生長環境的適應,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光合作用機制[38- 39],即使當不同種源植物移植到相同環境下生存,其光合能力仍存在差異[10, 13, 40- 42]。這種不同種源間光響應特性的差異正是植物趨異適應的體現。鐘培芳[13]、劉海燕[43]、安海龍[42]等對不同種源白刺、沙柳、黃柳光合速率等光合特性及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也發現這種光合趨異性。
表5種源地氣候(生長季降水、生長季溫度、最冷月均溫、海拔)對各個光合參數的GLM分析
Table5Summaryofgenerallinearmodelsfortheeffectofprovenanceclimatevariations(GSP, GST, MTCM, Altitude)onindividualphotosyntheticcharacteristics

氣候因子Climate factor表觀量子效率α1最大凈光合速率Pnmax光飽和點Isat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生長季降水量GSP13.430.12319.370.129生長季溫度GST143.025×10-4***158.332×10-6***最冷月均溫MTCM118.350.031*海拔Altitude111.750.007**殘差Residuals2256.982026.482172.28氣候因子Climate factor光補償點Ic暗呼吸速率Rd呼吸效率RE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自由度df解釋程度%SS顯著性Sig.生長季降水量GSP生長季溫度GST126.660.005**149.023×10-5***最冷月均溫MTCM海拔Altitude115.390.028*114.360.009**116.650.048*殘差Residuals2157.952136.612283.35
df,: degree of freedom; %SS: percentage of explained sum of squares; Sig.:significant; GSP: Growth season precipitation; GST: Growth season temperature; MTCM: The temperature of colddest month; ***P<0.001, **P<0.01, *P<0.05
造成不同種源植物之間光合能力趨異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基因型變異、氣候差異、群落結構不同、地理位置差異等[14- 16]。本研究將不同種源的蒙古蕕種植在相同環境中,排除了生長環境的氣候差異、群落差異等因素,主要研究由種源地氣候差異所引起遺傳變異對蒙古蕕光合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種源地溫度(GST、MTCM)與海拔(Altitude)對蒙古蕕光合能力有著顯著影響(表4、表5)。Sack等[44]報道稱植物光合進化適應主要與溫度決定的生長季長短、海拔決定的植物光脅迫等有關。安海龍等[42]在同一環境對不同種源黃柳(Salixgordejevii)葉性狀的研究中,凈光合速率等光合指標受種源地氣候(MAT、MAP)的顯著(P<0.05)影響。不同種源植物種植在同質園或相同環境下,種源地氣候作為遺傳因素顯著影響著植物的葉性狀[10, 12- 14]。
在同一環境下,蒙古蕕的光合參數(α1、Pnmax、Ic和Rd)受種源地溫度(MAT、GST、MTCM)的影響,隨著溫度的升高,其光合能力逐漸降低(表4);而Isat受低溫影響較大,與最冷月均溫(MTCM)顯著負相關,與生長季溫度(GST)沒有顯著相關性(表4、表5)。馮秋紅[45]、Wright[46]等大尺度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但鐘培芳等[13]對4個種源白刺(Nitrariatangutorum)種植在同一環境中光合作用的研究,卻發現其光合速率不受種源地溫度的影響作用,而受種源地降水的影響較大。季子敬等[10]對不同種源興安落葉松(Larixgmelinii)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其最大凈光合速率與種源地溫度的相關性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不同物種對溫度的適應能力有所不同,進而導致其對種源地溫度的響應有所不同[10, 13, 40]。也有研究指出,隨著溫度升高,植物光合能力下降,可能是植物比葉重、葉氮含量及光合氮素利用效率等的綜合變化引起的[47- 48]。同時本研究中,種源地海拔與蒙古蕕的Pnmax、Ic和Rd顯著負相關,與RE顯著正相關(表4)。而Soolanayakanahally等[49]研究中,在同質環境下,來自高海拔的種源樹木為了長期適應較短生長季節,具有較高的凈光合速率。由于蒙古蕕的種源地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區,光照強度較強,高海拔地區種源為避免紫外線對細胞器的傷害,光合速率較低,會表現為較低的最大光合速率;在弱光下表現為海拔越高,光補償點越低[44, 47, 50- 51]。
將種源地氣候作為導致植物基因型變異的因素之一,本研究通過一般線性模型ANOVA分析發現,種源地氣候對這6個光合參數解釋程度在16.65%—73.52%之間,其中對α1、Pnmax、Ic和Rd這4個光響應參數的解釋程度更是大于40%(表5)。研究將不同種源植物移植到相同環境下生存,排除了外界環境因素差異的作用,更為純粹的反映了環境差異所引發的遺傳變異效果。而在安海龍等[42]的類似分析中,種源地氣候對黃柳光合作用有顯著的解釋力,而其解釋程度相對降低(3.19%—13.77%)則是因為短期干旱處理較大影響了植物光合作用,導致水分脅迫(主因素)對其光合作用的解釋程度較大(26.5%—76.81%)。
除此之外,造成不同種源蒙古蕕光合能力差異的因素可能還有很多,CO2濃度、土壤養分含量等其他種源地環境因素造成的遺傳差異也對植物光合能力具有一定影響[48, 52- 53],它們也可能造成種源間的遺傳差異。種源地氣候作為反映遺傳因素的影響是造成不同種源蒙古蕕光響應特性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為今后蒙古蕕的引種栽培、種源選擇及遺傳資源保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