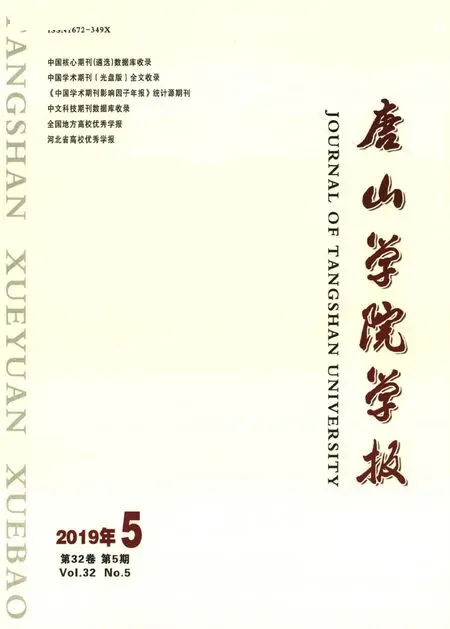對“文如其人”的批判性思考
李劍鋒
(唐山學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自古至今,我國就是一個注重道德修為的國家。縱覽中國文學史,“淡泊寧靜”“高潔傲岸”一類的道德評價是對文人至高的褒揚,而且在儒家思想的文化影響下,為人與為文的統一、言與行的一致、文與道的相促相長,是我國文人在道德修養過程中應該遵守的基本規則。因此,在中國傳統文人的品評體系中,“文如其人”長期占據著正統地位。
然而,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文人為人與為文背離現象在文學發展史中廣泛存在。有些文人做人偽善,為文清高;相反,有些文人做人謹重,為文放蕩。因此一直以來對“文如其人”的質疑之聲、對“文異于人”的辯護之言層出不窮,且都有理有據,言之鑿鑿。
一、“文如其人”的論爭
(一)肯定的觀點
縱觀我國歷代文論可知,是漢朝思想家揚雄首次提出“文如其人”的觀點,他在《法言·問神》中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言為心聲,書為心畫,他認為無論言還是書,本質都是心靈的表現。因為語表心聲,文現心畫,所以透過人的言表和文章足以知道這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這種看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憑借一個人表和里的一致或矛盾,可以看出此人的品性。
在《文心雕龍》中,劉勰認為:“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1]這與揚雄的論述有很大的共性,其中的“言”和“文”如同揚雄所說的“言”和“書”,所以二人都肯定了為人與為文的統一性。不同點在于,劉勰直接以“情”與“理”為主導因素和基礎因素,強調由于內在的因素制約而見諸外顯的符號形態,與揚雄以外在的符號形態而判斷人的內質的思路是相反的。另外,劉勰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要比揚雄更加具體,將“言”與“文”作為文章的表象,認為它受“才”“氣”“學”“習”四個因素的制約,可以說比揚雄更加全面地論證了“文如其人”。
蘇軾的文學成就無不表現出對“文如其人”的執著堅守,其文學創作在作品風格方面堅持返璞歸真,學術方面推崇“自然本體論”。他的詩詞把緣情和言智結合起來,剛柔并濟,體現著其特有的審美主張。蘇軾提出了“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文人合一、文如其人是這位文學大家評價詩文和文人關系的標準。
(二)質疑之聲
梁簡文帝蕭綱在《誡當陽公大心書》中指出“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有力地批駁了儒家詩教觀中為文“思無邪”的道德說教,他提倡以性靈執筆抒懷,放蕩為文,不能囿于“文如其人”的評價理念。
同樣具有“文如其人”的“叛逆”之心的是金代元好問,他在《論詩絕句》中直指揚雄的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2]這里的安仁即是西晉的潘岳,以潘岳的“人”“文”背離反駁揚雄的“心聲心畫”說。
錢鐘書在《談藝錄》中引用《莊子·列御寇》中的孔子言論“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指明人的外表和內質不一定統一,人心太難琢磨。他又說:“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1]他認為文人的為人與為文既可能一致,也有可能大相徑庭。并且他列舉了歷代文人的“文”“人”背離現象,說明了“以文觀人,自古所難”的道理。
諸如此類,從古代到現代對“文如其人”皆有質疑之聲,但由于儒家詩教觀的政治地位,對背離現象的研究并沒有真正引起傳統文人的重視。下面通過列舉為人與為文背離的典例,以事實為依據,闡述在儒道的思想體系下中國文人言行關系的復雜性,說明文人為人與為文背離現象的存在現實。
二、為人與為文的背離
(一)為人偽善,為文清高
前文有言,我國是個注重道德修為的國家。道德說教不僅多見于文學作品中,更體現在對人尤其對文人的道德約束上,如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人文統一等道德要求。“言行不一,道貌岸然”“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是遭人唾棄的,即便這些人有超人才華、曠世杰作,也掩蓋不了其德行上的瑕疵。
在討論偽道德文人的文章中,多會提到潘岳。西晉泰康年間的詩人潘岳,曾經名重一時,其文廣為傳誦,他擅長在作品中描繪自己淡泊利祿、情志高潔、忘懷功名。《閑居賦》以轉繞指之鋼舌,掉絕麗之妙文,寫自己的道德至上,“身齊逸民,名綴下士……教無常師,道在則是”[1]4;寫自己的田園興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姜,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4]9。單從此詩會以為潘岳是一位超凡脫俗的賢人達士,但實際上他卻是一個鉆營利祿、躁求榮利、諂媚權貴、吮癰舐痔的無恥小人。西晉晚期,在賈后的庇護下,賈謐權傾朝野。為了獲得更高的聲望和附庸風雅,賈謐廣招人才,潘岳因為他的才氣被選入賈謐門下。他對賈謐阿諛奉承,遇到賈謐乘車出行就望塵叩拜,盡顯此人的卑躬屈膝的本性。二位賈氏試圖暗算太子以謀取大權,醞釀出了借太子之名寫禱神文以告其謀反的伎倆,這份匯集野心家丑惡行徑的禱神文就是潘岳“秉筆直書”的。得益于自己的諂媚之功,潘岳步步高升,權錢加身。這就是人格復雜的潘岳,為文的清高與為人的偽善集于一身。
談到周作人,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美文。周作人的散文,著力于描寫花鳥魚蟲、美酒佳茗,顯見他閑適淡泊,尤重趣味。他強調:“我很看重趣味,以為這是美也是善,而沒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壞事,這所謂趣味里包含著好些東西,如雅,拙,樸,澀,重厚,清朗,通達,中庸、有別擇等,反是者,都是沒趣味。”[5]在散文的寫作上,他強調,必須“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統制”[6]。可見,周作人在散文中追求的雅致是知識性與趣味性兩重統制的內容與自然大方的語言形式的完美結合。因此,他的散文以簡約親切、清雋幽雅的閑適風格在現代散文史上別具風韻、獨樹一幟,被后人稱作是獨創散文價值標準的美文,他的美文也在意境悠遠和文字耽美等多方面創造了中國現當代散文藝術的極至。周作人的人格傾向于傳統士大夫型,雖然他學貫中西,但他主要以儒學體系為學問根基,他深諳儒學經典,尤其對《論語》研讀很深,儒士的人格性情促成了他對樸實唯美、平和沖淡的寫作風格和日常生活范式的渴望,超脫了當時惡劣的現實狀況,達到了一種超凡脫俗的境界。這么看來,周作人要么是個寄情山水的出世文人,要么是個忠君為民的儒將。然而,讓人失望的是,他卻成為了一代漢奸。在日本占領北京期間,周作人擔任了汪偽政府的要職,成為“漢奸文人”之首,留下了一片罵名。雖然今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歷史可以作出不同的評價,說他是對日本文化的欣賞者也好,或是超脫國家概念的淡漠者也罷,但事實是不能抹殺的,他在亂世中選擇了投敵,他就是漢奸,而且在事后又不能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責任,無異于加深了他自己的罪責。可見,閑適儒雅的文字下掩藏的是一顆“背叛”的靈魂,怎能不令讀者失望?
(二)為人謹重,為文放蕩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等因素對文人的影響,即便是被視為有文化瑕疵言行不一的人,其“言”也是多符合社會約束的,若所做之文都背離了社會規范,怎能稱得上文人?所以,前人的研究主要關注于“為人”的道德失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嚴格歸并我國文人的背離問題,前人單一的研究并不能全面概述此現象,如果這些研究武斷地將“為文”定格在道德層面,那么“為人”的背離勢必在偽善,然而,優秀的文章并非皆因包含或宣揚正確的價值觀見長,犀利的文風、優美的文辭、跌宕的情節等都是好文章的要素。因此,與如前所述的“為人偽善,為文清高”相對立的背離現象也是存在的,根據梁簡文帝蕭綱提出的“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暫以“為人謹重,為文放蕩”概述這類現象(誠然,蕭綱這句話的原義并不是指文人的背離現象,“謹重”和“放蕩”在文學理論中也并非一定背離,但單單對現象而言,兩者確實是背離的)。
蕭綱在文學上積極創新,不拘一格,就像他的文學理論一樣,擅長“不及君子之聽”的“放蕩”文學,在當時被人們稱為“宮體詩”。宮體詩追求聲律,夸耀辭藻,內容則著重描寫情色,這種文學作品是南朝統治階級上層奢靡頹廢生活面貌的集中反映。流傳下來的蕭綱的詩有近三百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宮體詩。這類詩多是關于女性和男女之情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屬于傳統的“閨怨”題材,寫女性愛情生活中的失意和悲哀;另一部分著重描寫女性的容貌、體態、舉止以及女子的生活環境、所使用的器物等,甚至把女人的衣飾、繡鞋、衾、枕、席、帳等都當作描寫的對象。描寫女性,以她們作為詩歌的主人公,本無可非議,但蕭綱詩中所描寫的卻是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樣“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上;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7],粉脂味和色情味極濃,廣受后世非議,若不是他天賦英才,其詩文采飛揚,狀物細膩,他也就早就被后人遺忘在文學的歷史長河中了。然而,作為一朝統治者,他卻為人謹重,為政保守,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家所擁有的野心與謀略,逐步淪落到了受人左右的地步,直至大寶二年為侯景所害。
王小波是在我國當代文學界有著特殊地位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著大膽荒誕的敘事、機智幽默的反諷、循復跳躍的結構、自由深刻的思想,廣受讀者喜愛,使他成為一代年輕人追捧的偶像。幾乎在每一篇小說中王小波都設置了“王二”這樣一位敘述者,而且王二身上有著作者王小波身上的某些特征,這樣沉浸于其作品中的讀者,很容易將王小波塑造的王二理解成現實中的王小波,形成對作者和小說人物等價認同的一種閱讀狀態。現實中的王小波的確和王二有著一樣的人生經歷,在云南農場下過鄉、北京工廠做過工、美國留過學、大學中當過講師……然而王二機智油滑、投機取巧、風流倜儻、猥瑣放浪,卻不是王小波的真實人格形象。王小波為人厚道,正直,講義氣,上學期間是個老好人,對同學提出的要求從來不會說“不”,和每一位同學關系都很好。王小波工作中踏實勤奮,在美國留學時生活困苦,他同時打好幾份工,由于英語不好,也常受人欺負,這是他最不愿回首的往事,敦厚老實的王小波遠不及王二那樣投機、油滑。王小波對待愛情,用情至深,對愛專一,追求李銀河讓他煞費苦心,他愛得熱烈,也愛得浪漫。李銀河近年來整理了王小波當年寫給她的情書,集結成《愛你就像愛生命》后出版,其中的情書語錄“不一定要你愛我,但是我愛你,這是我的命運”“我會不愛你嗎?不愛你?不會。愛你就像愛生命”飽含了王小波對李銀河的真情[8]。另外,王小波和李銀河在美國艱辛求學、相濡以沫的故事更是讓知情人感動。這樣的王小波怎能被視為擁有著陳清揚、二妞子、線條、小轉鈴等諸多“妻妾”的王二?
三、背離現象的原因探析
探究中國文人為人與為文背離現象產生的原因,可分為三個研究方向:第一,就文人角度而言,不能排除他們其中一部分人自身就存在偽飾意愿,由于文人的個人因素,確有個別偽飾分子,不能被歷史原諒;第二,就客觀環境而言,中國社會有著特殊的文藝土壤,在此成長起來的文人都帶有時代的特征,背離現象在我國特有的文藝氛圍中產生也是在所難免的;第三,就文學作品而言,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態,具備藝術的特性,由于一般讀者對文學創作的不解和欣賞技巧的偏差,容易對為人與為文是否背離產生誤解,具體可以從審美活動必需的距離感和文藝的超越性兩方面進行討論。
(一)部分文人的偽飾意愿
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主觀意愿便是文學創作的內因,文學創作的主觀因素,是指進入創作過程并作為創作主體出現的作家的自身條件,包括作家的才情、知識儲備、氣質、世界觀、人生際遇、文藝修養等。它們從各自的角度影響作品的形成。其中,世界觀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從描寫客體的確定,到描寫角度的選擇,再到作者所作的道德倫理評價、社會政治評價和審美評價等,都是在世界觀的影響下展開的。
然而需要重視的是,能夠從根本上制約作品風貌的主觀因素是文人的特定氣質,這就是魏晉文藝理論家劉勰指出的“肇自血氣”。文人特殊的人生道路和生活體驗,文人所經歷的悲歡離合和人情冷暖,都會影響到他的創作風格,從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印記。另外,文人多方面的才能,包括文藝鑒賞力、體悟生活的能力、捕捉細節和形象的能力、表現藝術的能力,以及文學之外的繪畫、音樂、舞蹈等方面的藝術素養,都是影響作品形成的關鍵因素。至于文人個人的才情、稟賦,它們對其作品創造風格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
東漢王充在《論衡·佚文篇》一文,寫到“文德之操為文”,這是指作家在文章中必須流露思想,而思想體現文風,文風則展示文德,文章道德才是文章美感的內在要求。好比一位舞蹈演員,無論她的為人如何,在表演時仍會以最美麗的裝扮,把自己嫻熟的舞姿展現給觀眾。所以說,文學的創作者為人與為文相吻合常常是相對而言的。因此,對于文章道德,有德有才者必有之,無德有才者亦有之。也可以這樣認為,文人的善與惡在為文時,時而脫離,時而相合。有道德修養的人會注重修為,即便在文章中,也會表現出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而無道德修養的人,因還懂得最基本的道德觀,因此,在寫文章時,可能會披上真善美的外衣。
為人偽善、為文清高的文人,大多是具有偽飾意愿的文人,本身就想著如何裝扮自己,做一個道貌岸然的文人。潘岳就是這樣的人,為了滿足個人的仕途野心,將自己寫的那些道德文章拋之腦后,將自己作為一個士大夫應有的道德操守忘得一干二凈,將自己作為一個臣子應有的忠心棄之不顧,阿諛奉承,陷害忠良,為政治野心家服務,親筆書寫污蔑君主的文告,這樣的行為與其文章中宣揚的道德禮教完全不符,后世的評論者將其視為“文”“人”背離的典范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中國特有的文藝土壤
中國文學與其他國家文學的成長土壤最大的區別在于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長期占統治地位。儒家思想奠定了我國文學的理論基礎,對中國文人的塑造和文學風格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主張“仁義”和“禮教”,從“仁”拓展出一系列的社會倫理體系,由“仁”演化出一系列的國家政治系統。以儒家詩教觀為代表的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儒家哲學,依仗政治權力的庇護,始終盤踞在我國封建文人品評體系的統治地位,成為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權威的文化工具。孔子認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9]孔子認為,學詩就是為了從政和專對,否則詩讀得再多,也是沒有用的。孔子還把詩的作用概括為“興觀群怨”(1)興觀群怨:出自孔子《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是對古代詩歌社會作用的申明和贊揚。,而“興觀群怨”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忠君”“孝父”。“興觀群怨”是孔子詩論的核心,對后世有很大影響,歷代文論都對其進行了闡發。
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便是儒家的詩教觀。孔子在《論語》中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針對文人,孔子強調文人的態度和創作動機應“思無邪”,在復雜的文學創作中實現文以載道,文字內容指向大忠大善,對讀者的教化作用要遠高于審美、宣泄等功用;二是針對讀者,孔子認為,讀者應抱著受洗禮的態度去閱讀,“非禮勿視,非禮勿叫,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閱讀的效果要有醍醐灌頂、脫胎換骨之感。這種教人為善的為文思想嚴格地鉗制著整個封建文學的發展,成為中國文人的為人準則和為文標準,我國文藝思想的長期僵化、文學創作的因循守舊是受其影響的結果。人的本性中都有張揚個性的一面,儒家詩教觀恰恰限制住了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人性自由的彰顯,將創作思想格式化,有些在生活中崇尚自由的文人,在創作中也不免拘謹,同樣,那些在生活中違背道德的文人,在創作中也要言說倫理,鼓吹道德。這便形成了讀者眼中的背離。
另外,中國曾長期處于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導致思想相對保守,文藝創新步伐相對緩慢,陷入迂腐發展的怪圈;存在重文輕理、重實踐輕理論傾向,文藝理論雖來源于創作實踐,但理論得不到足夠重視,對創作的指導作用甚微;文藝形態崇尚玄虛唯美,對文人提出過多、過高的理想化的要求……這些都是中國特有的文藝土壤,雖然直接或間接地造就了大批浩然正氣、慷慨激昂的道德文人,但也難免會有濫竽充數的道貌岸然之流。
(三)審美活動必需的距離感
審美經驗中有一個關鍵的概念就是審美距離,其中包括空間距離、時間距離、心理距離和情感距離。審美距離起到連接審美的主體讀者和客體文藝作品的作用,對審美活動的無功利性有著重要的影響。這個概念首先指出了審美對象,其次喚醒了作為審美主體應有的審美能力。由這兩點組成的審美距離在審美經驗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納蘭性德的詞為例,感知納蘭詞的悲劇美、隱晦性和朦朧美需要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才能完成。讀者作為審美主體,只有和審美客體保持適當的距離,審美才能達到神奇的、超脫的效果,才能從中發現美的本質。納蘭詞特有的美源自作者遣詞造句的非凡筆力,作者的稟性、命運、志向以及社會環境制造了納蘭詞的凄清婉麗、幽怨纏綿、哀惻動人的藝術氛圍,然而詩中的悼亡之哀及產生的悲情之美卻是來自于納蘭性德高超的“距離”創造能力,讀者只有達到了這樣的審美距離才能感受得到。
再以背離現象中王小波的文學作品為例,讀者在觀審這些作品時應當保持恰到好處的審美距離,“距離”太近,會將感性的文學作品進行過多的理性加工,會不自覺地思考作品中的王二是不是現實中的王小波,作品中王二有那么多放浪的女人,難道現實中的王小波也有那么多女友?誠然這些思考都是多余的,但熱讀中的讀者對這種思考卻是不由自主的。當讀者一旦真正了解了王小波,自然會感覺為人與為文的背離。那“距離”太遠呢?也是不可取的,一味地沉浸在文字表面的歡愉之中,閱讀的效果便止于膚淺了。只有保持適中的審美距離,才能讀懂王小波那顆崇尚自由的心,才能震撼于王小波神奇、跌宕的文筆,才更能理解現實中的王小波。
一般的讀者在文學欣賞時忽視了審美距離的重要性,在“冷眼旁觀”或“深情熱讀”的過程中,將作品人物與作者本人做盲目對照,主觀臆造聯系,以文觀人,用文如其人加以斷言:高潔的文字即高尚的文人,放蕩的行文即無良的文人。這種忽略審美活動中必需的距離感,難免會出差錯,由此產生為人與為文背離的認識亂象。
(四)文藝自身的超越性
文藝超越于現實,超越性是文藝的特有屬性,超越性主要表現在文藝高于現實的創造性上。相對于理想而言,現實是苦難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文藝世界中的“真善美”正是現實理想的具體化,文藝的宣泄與慰藉功用便是由此產生的。文藝給欣賞者帶來寬廣的想象空間,使欣賞者的精神得以安撫,生活得以激勵。文藝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所以文人在創作過程中構建的精神境界必然高于現實。
說到文藝理論中的“想象”,在此有必要加以闡述,“想象”在文學史上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如今作為文藝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借助科學的分析研究法,我們不僅能夠區分“幻想”與“想象”,而且還可以將想象分成兩種具體情況,即第一位想象和第二位想象。柯勒律治指出:“第一位想象是創作主體在其創造活動中的一種能動的知覺能力,是在自覺的情形下進行的;第二位想象則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而且為了進行‘再創造’,它要‘融化、分解、分散’客體。實用主義美學家杜威從美學的角度肯定了想象的作用。”[10]我們從中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審美的經驗是想象的,想象是結合文藝中所有因素的一種能力。得益于想象的文學之美表達了作家的藝術追求和精神理想,在這點上迥異于自然之美。
文學的超越性決定了文學不能是現實的機械復制,缺乏創造性的文學索然無味,勢必不會被大眾接受。優秀的文學作品探索歷史,拷問現實,抒發理想,憧憬未來……由文學產生的審美效果可見,超越性對于文學藝術的意義至關重要,超越性成為文學作品和文學創作中必備的特征,給文學藝術植入了超越現實的羽翼,有利于人們借此在心理上彌補現實的遺憾,獲得心靈的寄托。
作品的超越性決定了作者其人與其文的不對稱性,這里仍以周作人為例來說明。周作人的文學意境不僅超越了其自身的生活處境,最主要的是遠遠超越了當時的社會現狀和民眾訴求。民國年間,列強入侵,國將不國,經濟蕭條,民不聊生,人民一心想的只有和平與民主,而周作人卻沉浸在花鳥魚蟲、美酒佳茗之中,置國事國難、民情民怨于“不顧”,潛心創作他的美文。更甚的是,沒有政治原則的他隨風倒地服侍了汪偽政府。或許這就是他的文藝的超越性,但是這種在思想上放棄了家國情懷的文藝的超越性終究失去了它的精神內核。因此,在讀者眼中他被看成為人與為文相背離的人也就理所當然了。
四、結語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應該秉持科學的、客觀的態度評價中國文人為人與為文背離的問題,辯證地看待背離現象。
有時讀者眼中的“背離”多是源于對文藝理論的不解而形成的對文人品評的誤解,因此,作為文學的欣賞者,我們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修養,甄辨“背離”的真偽:欣賞文學作品時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避免對作品人物和作者本身的臆斷聯系;充分認識文學作為一種文藝形態所具有的文藝的超越性,對于由此而產生的“背離”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接受。
針對具有偽飾意愿的文人,其文雖善,我們可以鑒賞學習,但是對其為人方式要堅決地批評和抵制。另外,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應秉承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充分認識到肩負的文化使命,嚴格約束自己的言行。文人不僅要創作美文,更要寓之于理,書寫有利于提升民眾思想境界、有利于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華美篇章。在創作之外的社會活動中,文人也必須起到道德模范的帶頭作用,嚴于律己,言行一致,以自身行動引導和感染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