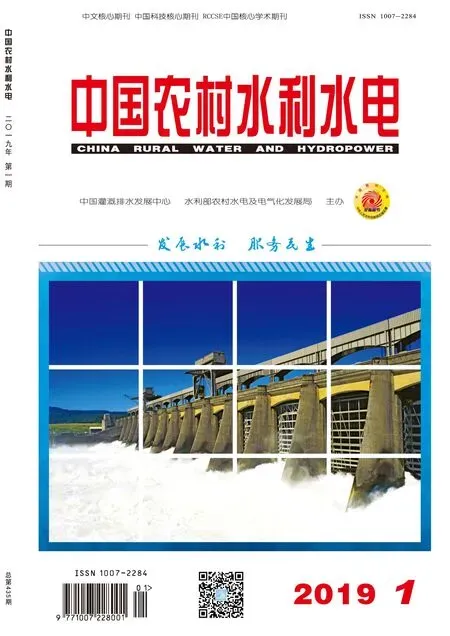基于水文特征參數的1954-2007年鄱陽湖流域徑流演變特征
黃伊涵,尹義星,韓 翠,劉夢洋,王小軍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水文氣象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4;2. 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 水文水資源與水利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9; 3. 水利部應對氣候變化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9)
0 引 言
鄱陽湖流域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形狹長,該流域三面環山,北鄰長江,受特有的地理環境特征和氣候變化特征、人類活動等因素的疊加效應影響,近幾十年來鄱陽湖流域的降雨-徑流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流域水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大,研究鄱陽湖流域徑流變化特征,探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對評估湖泊水量安全、應對湖泊極端水文事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1]。
徑流演變特征及趨勢直接關系到區域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下,流域徑流的演變規律及成因做了大量有意義的研究工作[2-6]。候欽磊等[9]應用Kendall秩相關系數、R/S分析、降水-徑流雙累積曲線法等方法,分析了渭河徑流的徑流變化趨勢,發現導致渭河干流徑流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其次是降水;Hao等[10]利用MK趨勢檢驗,研究了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塔里木河流域地表徑流的影響,得出在20世紀70年代人類活動對徑流變化影響最大,而1980、1990年代氣候變化對徑流變化影響最大。陳立華等[12]用MK趨勢和突變檢驗對西江流域廣西境內序列趨勢性、突變特征等研究徑流演變規律,發現西江干流徑流呈現減少趨勢;葉許春等[13]對鄱陽湖流域徑流變化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人類活動對鄱陽湖流域徑流起著減流的作用。
總體來看,數理統計分析方法是大多研究中分析徑流變化特征的主要途徑,然而,多數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其水文統計參數較為單一。因此,采用暴漲指數、年和干、濕季徑流系數、枯洪季徑流比、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等多種水文統計參數,通過分析和對比各水文統計參數,探究鄱陽湖流域1950年代以來的徑流演變特征,并通過上游和下游站點之間水文特征參數的對比,分析人類活動對流域徑流變化的可能影響,從而深入認識流域降水徑流演變規律及其響應關系,為建立鄱陽湖流域水文水資源的響應機制提供依據。
1 數據和方法
1.1 數 據
選用鄱陽湖流域上游地區的峽山、賽塘、高沙、梅港四個水文站,下游地區的外洲、李家渡、萬家埠、虎山四個水文站的1954-2007年日徑流資料;流域內79個氣象站(1960-2007)日降水資料,氣象站點空間分布均勻。所選擇站點數據可以反映該流域上下游地區水文氣象條件的變化。各水文站集水區面雨量的計算,通過對集水區內氣象站點降水資料進行泰森多邊形的面積加權獲得。鄱陽湖流域內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分別由南、東、西注入鄱陽湖,其中贛江流域上游東支控制站為峽山站,上游西支控制站為賽塘站,下游控制站為外洲站;撫河流域控制站為李家渡站;信江流域控制站為梅港站;饒河流域主要控制站為虎山站;修水流域上游控制站為高沙站,下游主要控制站為萬家埠站。水文和氣象站點的分布情況,以及上游站點所在的子流域,如圖1所示。

圖1 鄱陽湖流域水文氣象站點及子流域圖Fig.1 Hydro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subbasins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1.2 方 法
暴漲這個術語反映的是徑流過程中短期變化的發生頻率和快慢特征,上漲和回落快的徑流過程相對于保持穩定的徑流,其“暴漲”性更強。Baker等[14]提出R-B暴漲指數來定量分析徑流的變化特征,該指數的變化與氣候變化引起的徑流量年際變化無明顯相關性,而對大壩建設、土地利用變化有較高的敏感性。采用該暴漲指數來反映徑流特征,計算上游和下游各水文站的暴漲指數,在此基礎上,分析鄱陽湖流域徑流量的演變特征及與人類活動的可能聯系,其計算公式如下:
(1)
式中:Fi為暴漲指數;q為日均徑流量;i為天數,n=365(366)。
Fi是個無量綱的指數。Fi趨近于0表示流域的徑流恒定不變,Fi值越高表示流域的日均徑流量波動越大。
本文采用徑流系數分析流域演變特征,徑流系數是指一定匯水面積內總徑流量與降水量的比值,是任意時段內的徑流深度Y與造成該時段徑流所對應的降水深度X的比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Q=R/P
(2)
式中:Q為徑流系數;R為總徑流量;P為降雨量。Q是個無量綱的指數,其值介于0到1之間。
研究表明,徑流系數與不透水層表面覆蓋率有關。它綜合反映了自然地理因素對降雨形成徑流過程的影響,故可以很好地說明流域內水循環的程度,較好地監測水循環隨時間的變化;徑流系數的變化,往往也可以反映人類活動影響的情況。
利用季節徑流系數反映季節內徑流變化與降雨變化之間的關系,包括干季和濕季徑流系數,針對鄱陽湖流域,本文定義干季為10月至次年3月,濕季為4月至9月,分別計算干、濕季的面雨量深度和徑流深度,即可得到干、濕季徑流系數。
枯洪季徑流比是枯季(12月至次年2月)的徑流總量與洪季(6月至8月)的徑流總量之比,其計算公式如下:
Qdw=∑枯季徑流總量/∑洪季徑流總量
(3)
日平均徑流超過年平均徑流量的天數所占全年的比例,稱為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TQm[15]。該指數與暴漲指數比較類似,在城市化流域將降低,即該指數一般情況下與城市的發展呈負相關。其在城市化流域的數值較低,是因為在城市地區徑流的退水更快,而且濕季基流較低。在城市化流域,日徑流超過年平均徑流量的天數所占比例會降低,一般情況下,在城市地區的河流,該指數小于30%,而在郊區的河流,該指數往往大于30%。
2 結果與分析
2.1 暴漲指數
計算鄱陽湖流域上游和下游水文站的暴漲指數,結果如圖2和圖3所示。通過線性傾向率分析各站暴漲指數的平均十年上升(下降)率,結果表明,上游峽山站為-0.011/(10 a),賽塘站為-0.012/(10 a),高沙站為-0.02/(10 a),梅港站為-0.005/(10 a),下游地區外洲站為-0.001/(10 a),李家渡站為0.018/(10 a),萬家埠站為-0.001/(10 a),虎山站為-0.011/(10 a)。總體上來說,鄱陽湖流域除李家渡站外,其他站點的暴漲指數都呈下降趨勢。對各站的線性擬合的R值進行顯著性分析,上游的峽山、賽塘、高沙站均通過了0.01顯著性水平檢驗,即暴漲指數下降趨勢非常顯著;下游的虎山站通過了0.05顯著性水平檢驗,下降較為顯著,李家渡站通過了0.01顯著性水平檢驗,上升非常顯著。

圖2 1957-2007年鄱陽湖上游站點暴漲指數Fig.2 The flashiness index from 1957 to 2007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Poyang Lake

圖3 1957-2007年鄱陽湖下游站點暴漲指數Fig.3 The flashiness index from 1957 to 2007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Poyang Lake
圖4為鄱陽湖流域代表站點暴漲指數的MK突變檢驗圖。上游的峽山站暴漲指數UF曲線在1967年之前都呈現出不顯著的上升趨勢,1967年之后呈下降趨勢,且1975年之后的下降趨勢非常顯著。暴漲指數序列的UF與UB曲線在1973年左右出現了交叉點,交叉點位于上下置信區間之內。并且,此后的下降超過0.05顯著性水平,因此判斷在1973年左右發生突變。下游的李家渡站暴漲指數的變化則不同,在1957-1961年期間曾出現短暫的下降,自1961年之后都呈上升趨勢,且在1970-1995年期間上升趨勢非常顯著。突變發生于1962年左右。總體來看,上游站點突變時間發生在20世紀70至80年代,下游除李家渡站發生在70年代附近。

圖4 鄱陽湖流域代表水文站點暴漲指數的MK突變檢驗圖Fig.4 MK abrupt change for flashiness index at typical stations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對各個站點的暴漲指數進行MK趨勢檢驗,結果見表1。Z為正值表示呈上升趨勢,負值則表示呈下降趨勢。Z的絕對值在大于等于1.65、1.96、2.56時表示分別通過了0.1、0.05、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4個上游峽山、賽塘、高沙和梅港的Z值均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暴漲指數下降趨勢都非常顯著;下游的李家渡站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上升非常顯著,萬家埠站通過了0.05顯著性水平檢驗,下降較為顯著。總體來看,上游更多的是自然區域,下游地區城市化明顯,人類活動帶來的影響使流域水文特征產生了顯著的變化。因此,相對于上游地區,下游地區站點的暴漲指數下降趨勢較弱,李家渡站甚至呈上升趨勢。
分析各水文站暴漲指數的統計特征,除外洲站的暴漲指數值總體偏小外,其他各站暴漲指數的值較為接近。上游4個水文站的暴漲指數均值約為0.32,下游4個水文站除外洲站之外的平均值約為0.35(含外洲站為0.29),上游站點暴漲指數的標準差均值約為0.037,下游約為0.044(含外洲站為0.055),下游地區站點暴漲指數的離散程度更大,即年際波動較明顯。

表1 鄱陽湖流域各站暴漲指數和徑流系數MK趨勢檢驗的Z值Tab.1 Z Value of MK trend for flashiness and runoff coefficient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2.2 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
圖5為 1957-2007年鄱陽湖流域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的箱線圖。圖中粗橫線其值代表的是序列中不受極值影響的中位數,描述數據的集中趨勢。從圖5可以看出,上游的峽山站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約為33%,賽塘站約31%,高沙站約28%,梅港站約31%;下游的外洲站的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約為33%,李家渡站約為28%,萬家埠約為26%,虎山站約為27%。總體來看,上游地區除高沙站外,其余3個站點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的中位數均大于30%;下游地區除外洲站外,其余3個站點的中位數均小于30%。上游地區水文站點超過年平均徑流量的天數均值為112 d,且最小值大于100 d;下游地區均值為104 d,最小值小于100 d。總體來說,下游地區站點的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明顯小于上游地區。這說明在人類活動影響較顯著的下游地區,徑流的發生時間更加集中,其中萬家埠與虎山站指數該最小,可以推測其所在子流域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最明顯。

圖5 1957-2007年鄱陽湖流域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Fig.5 The ratio of days over average annual runoff from 1957 to 2007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2.3 徑流系數
計算得到鄱陽湖上游和下游地區站點的逐年年徑流系數。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初,上游站點的平均10 a上升(下降)率,峽山站為0.005/(10 a),賽塘站為0.01/(10 a),高沙站為0.022/(10 a),梅港站為0.003/(10 a);下游的外洲站為0.012/(10 a),李家渡站為-0.005/(10 a),萬家埠站為0.014/(10 a),虎山站為0.006/(10 a)。上游4個水文站中高沙站平均十年上升率最大,上升趨勢最明顯,其次為賽塘站、峽山和梅港站則相對較弱;下游的外洲站、萬家埠站和虎山站平均10 a上升率很接近,年徑流系數變化趨勢較為相似,均呈上升趨勢,虎山站相對其他兩個站點上升趨勢較弱,而李家渡站較為例外,呈現下降趨勢。
圖6為流域各站點年徑流系數的箱線圖。上游站點中峽山、賽塘和高沙站的中位數較為接近,約為0.5,梅港站的中位數則較大,約為0.7。下游站點中外洲和李家渡站年徑流系數的中位數較為接近,約為0.5,萬家埠和虎山站年徑流系數的中位數較為接近,約為0.6。此外,上游4個站點年徑流系數的平均數約為0.57,標準差約為0.13;下游4個站點年徑流系數的平均數約為0.55,標準差約為0.12。總體來說,與上游相比,下游的平均年徑流系數略小,標準差也略小。這可能是由于影響徑流系數的因素很多,除了氣候(降水量、蒸發等)原因外,還受人類活動(如城市化、建壩、植樹造林等)的影響。具體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圖6 鄱陽湖流域各站年徑流系數箱線圖Fig.6 Box plot of the annual average runoff coefficient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圖7為鄱陽湖流域年徑流系數的年代際變化,可見,上游水文站中,梅港站徑流系數較大,一直在0.65以上,1960年代至1980年代年徑流系數變化不大,1980年代后顯著上升,1990年代徑流系數最大,達到了0.73,此后至2000年代明顯下降;峽山站徑流系數總體最小,在1960年代前期徑流系數非常小,1970年代有所上升, 1980年代后持續微弱下降;賽塘站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徑流系數變化不大,至1980年代進入上升狀態,1990 s略有下降,至2000年代有所上升;高沙站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年徑流系數緩慢上升后下降,1980年代后的變化趨勢與梅港站基本一致。
下游水文站中,萬家埠和虎山站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970年代有所上升,1980年代下降, 1990年代上升明顯,而后2000年代下降明顯;外洲站在1960年代前期年徑流系數較小,1970年代有所上升,1980年代下降,1990年代再次有所上升,2000年代略有下降;李家渡站的徑流系數變化不同于其他幾個站,1960年代前期年徑流系數較小,至1970年代有下降,至1980年代略有上升,此后持續下降,總體上該站徑流系數年代際變化幅度不大。

圖7 鄱陽湖流域年徑流系數的年代際變化Fig.7 Decennial change of runoff coefficients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計算得到鄱陽湖上游和下游站點的干、濕季徑流系數,結果如圖8所示。梅港站干季和濕季徑流系數的中位數分別為0.58和0.64,其差值在鄱陽湖流域內最小;虎山站干、濕季徑流系數的中位數分別為0.41和0.65,其差值最大。上游4個水文站的干、濕季徑流系數中位數差值的平均數約為0.11,下游的差值平均數則約為0.15。一般情況下,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流域,濕季徑流系數與干季徑流系數的差別較大;而在城市化水平較低的流域,其差別較小。下游地區的城市化水平比較高,而在上游地區,植被覆蓋率較高,下滲進入土壤的雨量較多,故地下水是其徑流的重要補給源。這樣就造成鄱陽湖流域上游站點的干濕季徑流系數差值小于下游站點。

圖8 鄱陽湖流域各站干、濕季徑流系數的箱線圖Fig.8 Box plots of the runoff coefficients in the wet and dry seasons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對年徑流系數和干、濕季徑流系數進行MK趨勢檢驗,結果見表1,下游李家渡站通過了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其年徑流系數下降較為顯著。對于干、濕季徑流系數,上游高沙站的干季徑流系數呈增長趨勢,通過0.05顯著性水平,增長趨勢顯著;下游的外洲站濕季徑流系數為下降趨勢,Z值通過了0.05顯著性水平,下降趨勢顯著;虎山站干季徑流系數呈增長趨勢,通過0.1顯著性水平檢驗,上升趨勢較為顯著。一般來說,干濕季徑流系數變化的具體原因與當地水文氣候條件、水利因素等相關,根據相關文獻[16],干季徑流系數的上升可能與流域的水利調度有關,而濕季徑流系數的下降可能與流域水文氣候特征的變化有關。這方面的詳細分析,有待作者今后進一步的研究。
2.4 枯洪季徑流比
從圖9中可以看出,鄱陽湖流域上游與下游站點的枯洪季徑流比基本都在40%以下,上游4個站點的枯洪季徑流比的變化區間較為相近,峽山、賽塘、高沙和梅港的中位數分別為25.25%、29.59%、25.10%和26.38%;下游站點枯洪季徑流比變化區間的差別則相對較大,外洲、李家渡、萬家埠和虎山站的中位數分別為27.38%、31.33%、24.52%和28.96%。上游站點枯洪季徑流比的均值為36%左右,下游站點的均值為35%左右。總體來看,人類活動較為明顯的下游地區,其枯洪季徑流比相較于上游數值略小。

圖9 1957-2007年鄱陽湖流域站點枯洪季徑流比Fig.9 The dry/wet runoff ratio from 1957 to 2007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3 結 論
(1)流域各站暴漲指數主要呈下降趨勢(下游的李家渡站例外);相對于上游地區,下游地區站點的暴漲指數下降趨勢較弱。上游站點突變時間點發生在20世紀70至80年代,下游則發生在70年代附近,李家渡站則發生于1962年左右。
(2)受城市化的影響,下游地區站點的超過年平均徑流量天數比明顯小于上游地區,其中萬家埠與虎山站該指數最小,可知其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最明顯。
(3)總體來說,流域各站年徑流系數主要呈增長趨勢(下游李家渡站例外);下游站點的年平均徑流系數略小于上游。這可能是由于影響徑流系數的因素很多,除了氣候(降水量、蒸發等)原因,還受人類活動(如城市化、建壩、植樹造林等)的影響,未來需要進一步分析。
(4)下游的城市化水平較高地區站點,其干季與濕季徑流系數的差值相對于上游站點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