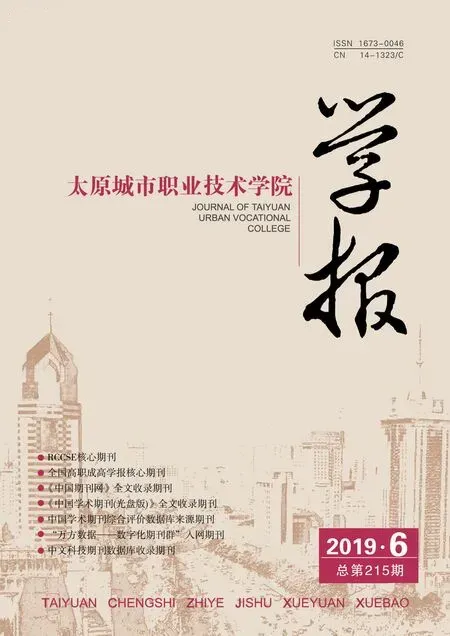語義、句法與語篇功能視角下的迪蘭·莫蘭單口相聲的語言與幽默
劉宜珂
(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4)
現代形式的西方單口相聲起源于18世紀的英國。其后300年間,它由一種生存于音樂廳、服務貴族的支流藝術,逐漸轉變為面向大眾的通俗娛樂。西方單口相聲(stand-up comedy)有別于中國常見的對口相聲(comic cross-talk),沒有后者中捧哏與逗哏的分配。這就導致單口相聲較難在短時間內經由情景制造笑料,因而其往往更加依賴于單純的文本中一字一句間包含的語言上的幽默元素來逗笑觀眾。本文主要節選迪蘭·莫蘭2004年的《怪物》(Monster)、2011年的《是的是的》(Yeah,Yeah)以及2015年的《脫鉤》(OfftheHook)三場演出中的文本,分析其中語義、句法、語篇功能三個層面的操縱對于建構幽默的影響。
一、語義與幽默的創造
在語義學視角下,幽默起源于詞語和句子含義中的不協調。法蘭西斯·哈奇森于1725年在ThoughtsonLaughter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語義不協調與幽默的聯系,維克多·拉斯金其后繼承并發揚了這一論斷,提出“當一段相聲的結尾,也就是最后的包袱,將觀眾對于先前內容的理解完全推翻,并提示出一種與之前截然不同的解釋時,幽默就得以產生了”。在迪蘭·莫蘭的作品中,語義不協調往往以兩種形式存在:詞語概念的變異和語法搭配的扭曲。
(一)語義三角中概念與所指事物不協調的幽默
語義三角理論認為,詞語與其所指代的事物之間沒有直接聯系,而是間接地通過人的頭腦中對于客觀事物基本特征的概括,也即概念(concept)串聯起來的。這種概念雖然因人而異,卻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這種普遍性受到人為的扭曲時,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語義就會顯現得不協調,幽默的效果也就應運而出。
迪蘭·莫蘭賴以成名的《黑色幽默》的主要演繹方式是扮演一個憤世嫉俗的人物形象,這種表演風格意味著他的單口相聲中充斥著尖銳的諷刺與對大眾觀點的反叛,這些內容在文字上的落腳點便是詞語概念的扭曲。他往往將詞語與概念、事物與概念間的普遍聯系割裂,再基于荒謬的認識進行重組,以創造出滑稽的意象和語句。比如,當他談及滑雪這項室外運動時,他對其概念進行了有選擇的人為加工:
(a)Why would anybody want to go skiing?You could sit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kitchen and break your knees with a hammer.
(為什么會有任何人想去滑雪?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家廚房里,然后用錘子砸碎自己的膝蓋。)
在此處,莫蘭對于“滑雪”一詞的普遍認可的概念——“室外運動”進行了兩方面的解讀。一方面,他承認了其中“室外”的概念部分;另一方面卻將其中“運動”的概念成分曲解為“受傷”。這一扭曲帶來的語義概念上的不協調沖擊了觀眾對于“滑雪”一詞的原有理解,帶來了幽默感。同時,本句話前半部分對于滑雪的原定概念的沿用使得后半部分的扭曲顯得更為突然,這種節奏上的變化也有助于幽默效果的迅速滲透。
當一個詞語的概念比較簡單明了時,莫蘭則往往選擇運用簡潔的語句徹底推翻其原有的概念。
(b)You don't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food.You only know there's food there'cause one of the drinks is chewy.
(你并不會在意酒席上飯菜的口味好壞。因為只有當你品嘗到一些有嚼勁的酒時,你才會意識到原來桌上還有菜。)
本句中,莫蘭為了凸顯嗜酒如命的人的特點,有意地以“有嚼勁的酒”指代飯菜。在這一簡單的情景下,發生了兩處語義三角的不協調現象。首先,在“酒”這一詞與其概念、指代事物的三者關系中,其本身概念發生了扭曲,即其原有的被普遍接受的“液體”的認識受到了曲解;其次,“飯菜”的概念也經過藝術加工,發生了轉變,被重新賦予了“有嚼勁的酒”這一認識。在這接連的詞語語義沖突下,莫蘭成功地在簡短的文字中創造出了一系列的悖論,而這種對傳統認識的沖擊也正是其單口相聲幽默性質的重要來源之一。
(二)語句中語義選擇不協調的幽默
在主謂式語法結構中,謂詞的語義選擇限制(semantic selection)要求的論元服從謂詞所限定的語義范疇,一旦論元超出了謂詞所能修飾的范圍,語句整體的意義就會顯現得不協調,甚至呈現出荒謬的意象。在迪蘭·莫蘭的單口相聲中,這一語義選擇規則往往被其反其道而行之,以便于有意地創造滑稽的語句與意義。
(c)[instead of you,] The cats are drinking espressos and reading the Sunday supplements.
([代替你的位置]貓兒們在喝濃咖啡、讀星期天報紙增刊。)
在此句中,兩個謂詞“喝咖啡”“讀報”對于其所能修飾的論元均有或小或大的語義限定性。“讀報”這一行為的潛在主體是擁有語言與識字能力的人類,這顯然與本句的論元不相符;“喝”這一謂詞盡管本身對于論元限定性不大,但是“喝咖啡”這一行為所蘊含的人類文化的背景意義使得其與本句中的論元“貓兒們”的搭配同樣顯得荒謬而滑稽。類似于(a)句中對制造幽默時語言節奏的把握,本句同樣先以“喝咖啡”這一尚能為人接受的謂詞進行鋪墊,再于句尾拋出真正能夠凸顯不協調性的“包袱”,使得幽默效果得以產生得更為突然,語句也更為緊促。這兩處程度不一的語義選擇不協調的現象,使得整個句子所傳遞出的意象十分荒誕,使其呈現出黑色幽默的性質。
除了創造純粹荒誕不經的語句之外,迪蘭·莫蘭還往往通過打破語義選擇規則所創造出的不協調性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以求含蓄地強調某些意象。
(d)You can hear her breasts as she walked behind you.
(當她在你身后走動時,你能夠聽到她的乳房。)
一般條件下,本句中的謂詞“聽”限定了論元的語義概念,規定了論元必須具有“音”的元素,因而其后出現的“乳房”本應被看作是脫離了語義選擇規定的不協調詞語。但是,這一不協調的配對并非純粹為了制造荒謬的意象,而是通過激發聽眾的好奇心,促使其在內心思考能使本詞組合理化的解釋,并最終認識到語句所暗示的意義,即“能聽到乳房搖動所發出的聲音”,進而重新認識到整句話所要表達的內涵,也就是“她的乳房很大”。原句中不協調的語義搭配,使得本來平凡無奇的語句變得新穎、有趣,強調了其內涵,放大了其感染力,這從另一方面體現出謂詞與論元語義選擇上的不協調所能帶來的幽默效果。
二、句法與幽默的建構
不同于語義操縱直接創造幽默效果的功效,句法的編排對于相聲幽默的建構更多地起的是輔助作用。在實際表演中,相聲演員往往“通過對句法結構的巧妙安排和變異來體現幽默效果”,在迪蘭·莫蘭針對句法形式的調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遞歸功能與結構歧義的使用。
(一)句法的遞歸功能與幽默的建構
遞歸性(recursion)是人類語言句法中的根本性質之一。在這一機制下,人們得以通過循環反復特定語法成分不斷延續一個語句,語言也因此獲得了無限的創造性。在迪蘭·莫蘭的單口相聲中,句法的這一遞歸功能常常被應用于語句的延伸以及幽默的鋪墊與建構中,塑造了許多看似冗長卻環環相扣的“一句話笑話”。
(e)If you see a Russian in Hollywood movie,he has a scar;it starts here[pointing at his eyebrow];it goes over his face,over all his furniture in his apartment,out in to the street.
(如果你在好萊塢電影里看到一個俄羅斯人,他一定會有一道傷疤;這道傷疤會從這兒開始[指著眉頭];它會覆蓋這個人的整張臉,穿過他的公寓中所有的家具,然后一路延伸到街上。)
在此句中,迪蘭·莫蘭運用介詞短語的遞歸結構(在中文翻譯中被調整為動詞短語遞歸)創造了一個形式上連貫的有機整體。但是在這一渾然一體的框架中,其嵌入的文字所營造出的卻是愈發荒誕的意象。遞歸結構不僅就句法層面而言使得這種語句得以獲得形式上的合理性,還就語義層面而言從其形式的循環反復中構建出了一種內容上同樣合理的假象。當后者被人為地破壞時,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不協調就會創造出幽默的效果。
遞歸結構對于構建幽默的貢獻不僅限于在其框架下規整的形式與荒誕的內容二者之間的碰撞,還在于這一句法結構對于語言節奏的輔助作用。
(f)He stepped closer,wary,frightened,disbelieving,disoriented but definitely aroused.
(他站近了些,神色警惕、驚恐、懷疑、迷失,但確實感到“興奮”。)
一段相聲能否制造出預期的幽默效果,不僅取決于其內容的好壞,還取決于相聲的語言鋪墊與氛圍營造的水平。此處的遞歸結構被運用于一連串修飾名詞主語的形容詞上。這些詞語的排列賦予了這句話一種緊促的節奏感,簡潔地勾畫出了這段相聲中主人公的形象。盡管其自身并不具備逗笑的功能,但是它在短時間內調動了聽者的想象力與好奇心,為最終的包袱做好了鋪墊。試想如果句法規則不允許遞歸結構,只容納單獨的語法成分,那么此句中原本豐滿的情景描述便會變得十分貧瘠,句末的包袱也會因此顯得較為單薄無力。
(二)句法中的結構歧義與幽默
當對同一個句子進行句法層次的解剖時,有時兩種以上的句法結構均可以成立,并且可以推導出不同的句意,這種現象就被稱作結構歧義(structural ambiguity)。結構歧義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形式句法下關于切分句子層次的原則有時并不一定能得出唯一的解法。結構歧義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種需要避免的事態,但是在相聲表演中,它卻可以成為一種別出心裁的幽默的來源。
(g)Men are not heroes by and large,you know.You make it to middle age,[and then]you're not a hero most of the time;you are just a jelly baby with a few quid.
(總的來說,男人不是英雄。當你步入中年,你大部分時間都不會是一個英雄;你只是一個懷揣幾英鎊的軟糖小人/(因為)沒有多少錢的你就像個軟糖小人一樣(沒用)。)
本段文字的最后一句中,以with起始的短語就其句法成分可以做兩種解釋。其一是作為“a jellybaby”的后置定語成分,一同形成“只有幾英鎊錢的軟糖小人”的涵義,再進一步作為全句的表語;其二是作為本句中主語“你”的伴隨狀語成分,修飾主語的狀態,并交代之所以把主語“你”暗喻為軟糖小人的緣由:即因為缺少經濟支撐而不能成為“英雄”。這種結構上的歧義賦予了本段文字兩種不同的解釋方法,豐富了這一相聲片段的幽默內涵。由此可見,相聲藝術中不僅可以由較為常見的字詞的多義性制造諧趣的效果,同時還可以通過句法結構的多義性來達成以有限的篇章表達多樣的意思的效果。
三、語篇功能與幽默的傳導
一般而言,語言的語篇功能即使語言自身前后連貫,并與語境發生聯系的自我服務的功能。在實際表演中,語言的語篇功能對幽默的傳導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迪蘭·莫蘭往往在其作品中通過操縱語篇的銜接系統與信息結構鋪陳笑料,創設幽默的氛圍。
(一)銜接系統的運用與幽默
在句法的語篇功能視角下,當一段文字中的某個成分的含義依賴于另一個成分的解釋時,便發生了銜接關系。韓禮德和哈桑認為銜接方式有五大類:照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Conjunction)以及詞匯銜接(Lexical cohesion)。這些銜接手段的運用關系到語篇整體的次序與連貫性,是建構預期的語義關系的橋梁。在相聲藝術中,銜接手段的使用還會極大地左右語言的精簡程度,進而影響制造幽默效果的笑料的突然性與感染力。
(h)People enjoy what's bad for them.They always have,you know.Nobody rings up “Abra-kebabra”or any burger house at 4 in the morning and says:“Have you got any salad?I want a radish.I just know I need one.”——Heroin does that to you.
(人們喜歡對身體不好的事物。人們從來都是這樣。沒有人會在早上四點打電話給漢堡店,然后問:“你們有沒有沙拉?我想點一個蘿卜沙拉,我必須得吃一份沙拉。”——只有吸食海洛因的人才會這樣。)
在這段文字中,迪蘭·莫蘭運用了照應的銜接方式,以that一詞簡潔地指代了前文中所構建的情景。這一銜接手段使得語段末句不必再次重復冗長地描述,得以更加直接地轉入最后幽默的妙語中。除了在不犧牲語義內涵的前提下縮減語句篇幅的功能之外,此處用于前指照應的銜接手段還是使得在段末推翻前文意象的做法可行的重要平臺。當最后一句點睛之筆還未出現時,前文僅僅傳遞出了一個意象:沒有人會在凌晨4點特意點沙拉外賣,因為人們不喜歡吃蔬菜一類對身體有益的食物。然而最后一句話推翻了這一構建的情景,并賦予了其全新的解釋:如果真的有人這樣做,那一定是吸食海洛因后引發的癲狂癥狀。這種對于前文語句進行再次解讀的做法是基于前指照應這一銜接手段而成立的。
省略手法與照應手法類似,也可以用于簡潔地銜接前文的鋪墊與最終的笑料:
(i)If you do have a partner,and a family,then you'd think:“What if I died?How would they cope?They wouldn't!They would be out on the street in half an hour stealing food from seagulls'mouths.Or worse,they would [cope with my death]!”
(如果你有一個伴侶,有一個家庭,那你就會想:“我要是死了怎么辦?(沒有我)他們如何能夠活下去?他們活不下去!不過半個鐘頭他們就會流落街頭,從海鷗嘴里搶食物。或者更糟糕的,他們能[脫離我活下去]!”)
在此段文字中,迪蘭·莫蘭通過運用省略的銜接手法,將語篇前文中已經多次出現的“cope with my death”(面對我的死亡/脫離我活下去)的含義在尾句中省去不提,避免了重復,使上下文更加緊湊。同時,經由對于重復出現信息的省略,本句得以更加突出地強調句中的新信息,使得“能”的概念這一句中承載笑料的成分更加凸顯,幽默效果也更加鮮明。
(二)信息結構的操控與幽默
(i)例還從側面反映出,語篇中的信息結構同樣有助于創造幽默的效果。功能句法論認為,語篇的信息可以被分為已知信息與新信息,前者是指言語活動中已經出現過的或是根據語境可以斷定的成分,后者則是指言語活動中尚未出現的或者根據語境難以斷定的成分。單口相聲為了創造出乎意料的情景與意象,往往會嘗試操縱語篇的信息結構,在相聲的最終包袱處創造信息的前后混亂,使觀眾心中預想的已知信息與最后一句話提供的新信息之間產生矛盾沖突,以此制造荒誕滑稽的效果。
(j)[Reading to the audience a dialogue from an erotic romance novel written by himself].
Woman:Yes!Yes!Yes!Yes!Yes!
Man:Who are you?What are you doing in my bathroom?
([給觀眾朗讀他所寫的色情小說中的一段對白]
女人:“嗯!嗯!嗯!嗯!嗯!”
男人:“你是誰?你在做什么,在我的廁所里?”)
在此段中,迪蘭·莫蘭先借由對于這個場景的描述,即通過告知聽眾他將要讀一段色情小說的對白,誘導觀眾從這一語境出發對于所言場景進行信息成分的預判。而后,莫蘭通過使用段中女人的話語進一步誤導性地佐證觀眾心中對于已知信息的判斷。至此,語篇中的已知信息已經十分牢固地被建立于“一對關系親密的男女正在發生性關系”的意象之上。然而本段最后的男人的第一句話突兀地提示了與已知信息全然不同的新信息,打破了聽眾心中對于語篇信息結構的預判,制造了不協調的情景。同時,男人的第二句話通過提示“在我的廁所里”的新信息,將已知的信息結構變更為“一個陌生女人在一個男人的廁所中宣泄性欲”的意象,進一步拉大了新舊信息之間的差距,增強了出乎意料的感受。本段的幽默效果并非來源于某一詞或某一句的滑稽內涵,而是源自整個語篇中制造矛盾沖突的信息結構給觀眾留下的荒誕感受。
四、結語
本文從語義、句法與語篇角度分析了迪蘭·莫蘭單口相聲中用于創造幽默效果的技巧。通過例證,本研究發現在迪蘭·莫蘭的單口相聲表演中,語義的不協調是較為常用的創造滑稽意象的手段;句法的形式功能主要負責為語義不協調等幽默效果的建構提供可行而簡潔的框架;而語篇功能中銜接系統與信息系統的操縱既有助于幽默的有效傳導,也可以從有別于語義不協調的層面產生新的幽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