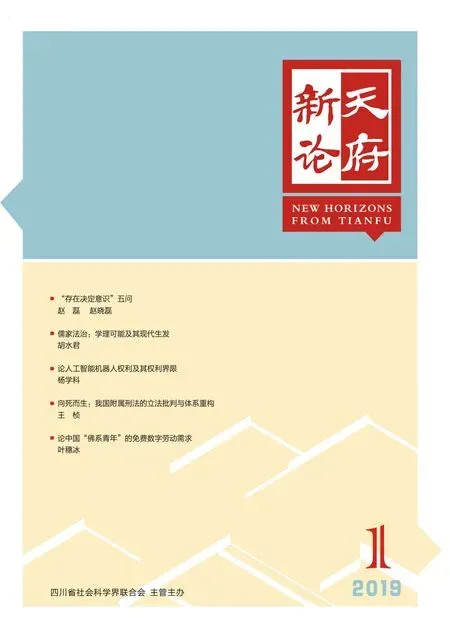玩勞動與玩工的剝削機制研究
劉皓琰
在機器大工業時代,生產力雖然迅速增長,但與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要求仍相去甚遠,因此第二產業便成了促進國民財富增長和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重點領域,而文娛與休閑則是少數人的特權,“資本主義生產在這個領域中的所有這些表現,同整個生產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頁。而隨著技術進步在大范圍內對社會物質需要滿足度的增強以及信息革命對于生產力的跨越式提升,游戲產業、傳媒產業、文化體育產業等開始迅速崛起。與此同時,以平臺為核心的產業發展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勞動組織方式、社交及交易模式,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界限被逐步打破。隨著信息時代娛樂產品的不斷豐富與社會總體參與度的逐步提升,開始有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探究平臺經濟和娛樂產業中價值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他們的研究視角不再限于雇傭勞動制度內部,且非常注重普通用戶在平臺資本主義剝削體系中的地位,交流、傳播、娛樂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行為都被納入生產性勞動的范疇。“玩勞動”和“玩工”的概念應運而生。
一、“玩工”與“玩勞動”概念的提出和發展
最先提出“玩工”概念的是北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的朱利安·庫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博士。庫克里奇長期致力于數字傳媒和游戲行業的研究。他受到意大利學者蒂茲納·泰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免費勞動”概念的啟發,在2005年發表了《不穩定玩工:改編者和數字游戲行業》一文。文中以“反恐精英”中的改編機制為例指出,改編機制與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形式是可比的,玩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在游戲中,并通過修改改編機制創造了更多內容,改善了更多服務。改編勞動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雇傭勞動范疇,也并非單純的休閑活動,反而類似于自由職業或者志愿勞動。改編者作為免費“玩工”,其不穩定性在于他們既不是受到財務方面的驅動也不受強迫,但卻被納入游戲開發商的生產體系之中,這使得他們的活動無法用傳統的工作或休閑歸類。[注]Julian Kücklich,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Journal,Vol.5,2005.庫克里奇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受到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重視,他們立刻將“玩勞動”這一概念納入其“數字勞動”的范疇進行分析。2009年,新學院大學的學者特雷博·肖爾茨(Trebor Scholz)在該校組織了名為“數字勞動:既是游樂場又是工廠的互聯網”的學術會議,并在2012年出版了同名的論文集,嘗試運用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解讀平臺資本主義中的多重勞動形式。肖爾茨在這部論文集的前言中指出,數字勞動與傳統的勞動方式不同,是用戶消耗在網絡傳媒上的創造性勞動,數字時代的游戲、消費和生產變得越發難以區分。[注]③Trebor Scholz,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pp.187-204.麗莎·納卡穆拉(Lisa Nakamura)則在文中考察了職業游戲玩家的工作環境。她以“魔獸世界”中的貨幣交易為例指出,職業玩家將游戲當做生存的方式,他們不停地幫助休閑玩家在游戲中營利和作弊,絲毫感受不到游戲的樂趣,在實質上成為服從虛擬經濟環境的工人。③此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對玩勞動的討論不斷。作為該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也在其代表作《數字勞動和馬克思》中對玩勞動進行了集中討論。他認為,在傳統的資本主義中,享受、性、娛樂等休閑活動往往是業余時間的一部分,而在當前數字媒體的生產過程中,剝削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往往已經被隱藏在娛樂之中,在很多情況下,玩和勞動是無法區分的。當玩被作為生產性勞動商品化時,便會被納入資本的剝削體系之中成為積累剩余價值的來源。[注]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Routledge,2014,p.126.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的思想中看到一些類似于“玩勞動”的理念。譬如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構建的“非物質勞動”概念,也描繪了一種休閑勞動化的趨勢。他們認為,由于非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很多時候是同時進行的,因此越來越難以將休閑與勞動做傳統意義上的劃分。[注]陳瓊珍:《非物質勞動理論——對哈特和奈格里理論的再闡釋》,《社科縱橫》2010年第12期。
與國外學者相比,國內政治經濟學界關于數字勞動和“玩勞動”的討論可以說尚處于相對空白的狀態,更多的是關于國外成果的介紹性和綜述性的陳列。反而是在國內的新聞傳播界,開始有學者運用這一概念分析當前的信息網絡與社交平臺。譬如吳鼎銘就考察了游戲產業中的玩家。他將玩家分為普通玩家、“金幣農夫”和職業選手三類。普通玩家的積極情緒、好奇心、消費欲望等都會被開發商通過商業引導轉化為具有交易價值的數字化勞動與資本;而后兩類玩家卻必須受雇于沒有勞動保障的商業公司,在制度保障和大眾認可度不強的環境中遭受到體力和精神的雙重盤剝。[注]吳鼎銘:《網絡“受眾”的勞工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網絡“受眾”的產業地位研究》,《傳媒經濟研究》2017年第 6期。蔡潤芳則考察了整條電子競技產業的價值鏈,并認為普通玩家會在角色扮演與游戲運營中成為“產消玩工”,通過參與游戲進程成為游戲內容制作的參與者。此外,隨著網絡游戲的發展,游戲通常會與社交媒體綁定,在互相疊加的過程中促進游戲的大眾化,而每個用戶都會成為游戲產品的推手。[注]蔡潤芳:《平臺資本主義的壟斷與剝削邏輯——論游戲產業的“平臺化”與玩工的“勞動化”》,《新聞界》2018年第2期。我們必須看到,“玩勞動”的概念還缺乏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雖然在平臺經濟時代,勞動的場所、形式等都與大機器時代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但玩與勞動是否可以相融,玩勞動是否能作為生產性勞動和剝削鏈中的一維存在等問題都是我們重新把握勞動價值論、認識當前平臺資本主義運作方式所必須討論的要點。
二、玩勞動的概念剖析
(一)玩何以成為勞動
在討論之前,我們必須重新對玩勞動的范疇給出界定。在很多傳播政治經濟學者那里,玩勞動的概念多是狹義的,專指游戲產業中玩工消耗的勞動。而為了考察娛樂活動的普遍規律,我們將廣義上的玩勞動,即除游戲行業外的其他休閑活動,均納入考察范圍。
從字面上來看,玩與勞動的結合似乎是一個荒謬的提法,因為玩、娛樂、休閑等概念與勞動呈現著明顯的對立關系。因此,理解玩緣何成為勞動,首先應當重新梳理馬克思在哲學意義上關于勞動范疇的理解。在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勞動”在人的發展中的地位曾經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都被理解為外在目的性的、被動的、強制的活動,譬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指出“生命屬于實踐而非創制”[注]苗田力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頁。。這里的創制便指代勞動,而實踐則被視作免于生產勞動之人的社會交往活動。直到黑格爾(Hegel)那里,勞動才被認為是人的本質,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中介”[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但是,由于黑格爾“惟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注]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頁,第196頁。,勞動只被當做絕對精神運動的一個環節,因此有著唯心主義所不可克服的缺陷。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繼承了黑格爾的勞動概念,認為勞動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類本質,是人改造自然的對象性活動以及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④。而作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方式的自由勞動,則是生活的樂趣,是勞動、休閑和發展的統一。因此,從哲學意義上講,玩與勞動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從屬關系,娛樂和休閑等活動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之一,理應被納入勞動范疇。
此外,泛泛地將“勞動”與“物質生產”的內涵等同,否認休閑時間擁有的生產功能,也是玩勞動這一概念受到質疑的原因之一,因而有學者盡管認可休閑活動的勞動屬性,也將勞動明確劃分為生產范疇和生活范疇兩類。[注]鄭杰:《作為生活范疇的勞動》,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所以,為了考察平臺資本主義下的剝削過程和對自由時間的異化,僅僅從哲學上肯定玩勞動的概念是遠遠不夠的,還應當將玩勞動放入物質生產的范圍內進行考察,玩勞動是否能進行價值創造,玩勞動是否屬于生產性勞動等,都是必須進行討論的問題。
(二)玩勞動是生產性勞動嗎?
在機器大工業時代,馬克思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具有實物形態的商品。而在數據大批量生產傳播的平臺經濟中,信息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地位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信息在生產、讓渡和消費過程中都具備有別于實物產品的特殊性,但原本屬于意識流的信息在加上簡單的載體后便可以同時具備使用價值和價值,完全具備成為中間產品或獨立商品的條件。因此,信息商品將成為我們討論玩勞動是否屬于生產性勞動的起點。馬克思認為,“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的自行增值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頁。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范疇內討論生產性勞動,一方面要關注價值創造,另一方面則要關注該勞動是否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總體來看,玩勞動創造信息產品無非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在娛樂過程中產生生產行為創造信息,第二種形式則是將娛樂行為本身作為內容加入文化產品的制作。而無論哪一種行為,都有可能創造出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屬性,即具備社會性的使用價值,因而具備了進入交換領域的可能性。在平臺資本主義時代,由于信息采集和加工等能力的高速發展,任何信息產品都有可能在網絡的觸手下被納入生產環節,進而進入交易和流通過程,成為被資本剝削的對象。馬克思也曾以作家、歌女、演員等為例指出:“一個演員,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資本家(劇院老板)雇用,他償還給資本家的勞動,多于他以工資形式從資本家那里取得的勞動,那么,他就是一個生產勞動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8頁。可以看到,馬克思對物質生產的定義也并未局限在實物商品內部,而是承認任何被社會認可的娛樂形式都具備成為生產性勞動的可能。與馬克思的論述唯一有所區別的是,在傳媒資本和產業資本高度融合的信息時代,榨取數字勞動的網絡無處不在,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也不再僅限于雇傭勞動制度內部,普通用戶的娛樂行為也有可能進入剝削體系。當然,我們在這里必須強調的是,玩勞動可以創造價值并不等于必然創造價值,因為玩勞動并不一定可以創造出社會認可的使用價值。這一性質與傳統的勞動方式相較并無二致,只是玩勞動由于擁有更強的主觀性而在程度上有所差異。
(三)玩勞動的價值決定
由于玩勞動生產形式的特殊性,我們是否仍然可以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玩勞動帶來的價值量,是必須探究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并未給出專門的分析,但我們可以通過對不同形式的玩勞動進行具體考察嘗試著給出解釋。
一方面,玩家在娛樂過程中發生兩種能動的、可以創造附加產品的生產行為。一種生產行為是通過信息加工參與產品制造,譬如庫克里奇所重點考察的修改機制。在玩家進行信息加工和修改時,其實是作為免費雇傭工人參與到生產過程之中,其產品的價值決定自然也會參與到包括專業人員在內的所有工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平均化過程。另一種生產行為則是在娛樂過程中進行信息傳輸。根據馬克思關于交通運輸勞動的理論,不改變產品的物質形態但卻使信息商品的使用價值發生空間轉移的勞動也屬于生產性勞動的范疇,其價值量也由運輸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9頁。而玩家在娛樂過程中上傳或暴露其信息的行為正是充當了運輸工人的角色。當然,即便在通信和匹配功能高度發達的平臺經濟時代,單個玩家進行信息傳輸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當娛樂行為本身作為內容加入文化產品的制作時,可以看作是玩家創造行為信息的過程,其產品的價值量也應當由生產某種社會認可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可以生產同種使用價值的娛樂行為,由于規則等的設置可能在生產時間上有長有短,但其價值量依然是通過對所有生產時間的平均化后決定的。當然,由于玩家的技藝有高有低,同時,行為信息又具備獨創性,因此,即便在同類的玩勞動過程之中,價值量的大小也會因為產品質量有高有低。信息作為中間產品,經過傳播和加工制作,并附以載體,成為最終商品。當然,由于消費者在娛樂偏好上會有更大的不同,因此,所形成的信息商品的價格也會較實體商品而言受到更大的波動。這也是造成不同娛樂項目中的雇傭工人工資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在普通玩家的娛樂行為被納入剝削體系之中時,其生產的所有價值量都會流入資本積累的過程之中。
三、玩工的價值剝削機制
隨著平臺信息技術與文體產業的逐步成熟與兩者的深度融合,數字經濟打通了包括資金、硬件、信息、實體等環節在內的、更加包容多樣的價值鏈,其產業模式的覆蓋面也逐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擴展,滲入原本的休閑和娛樂時間,而兩種形式的玩勞動也隨之進入資本積累領域,資本通過無償占有玩工所創造的附加產品或剝削玩工所生產的娛樂行為本身來進行價值榨取。
(一)玩工創造的附加產品
在傳統的娛樂產品的制作模式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自上而下的價值流向是非常明晰的。但隨著信息編程能力和計算機操作技術的簡單化和普及化,為了提高娛樂產品的可玩度,許多開發商選擇在產品中加入了“自定義”機制。廠家會將部分設計和制作的編程開放給玩家,幫助玩家根據個人偏好修改產品內容。在自定義機制中,玩家通過自我創制理念,自我進行編程,改變原產品中的固定樣式,然后將改編信息上傳和保存至原產品成為內容。隨著自定義機制的不斷成熟,可供玩家修改的內容愈發豐富,除固定板塊、游戲主線等核心內容外,其他角色或場景等均可根據玩家喜好獨立編纂。以游戲行業為例,從庫克里奇所重點考察的“反恐精英”到今天大火的“絕地求生”等游戲,廠商一直保持著玩家對游戲的自我設計權,玩家可以自我創建房間、更改角色形象、設計地圖、選擇對戰模式等。而隨著單機游戲向網絡游戲的逐步演變,通過自定義機制增加游戲內容的情況變得更為普遍,玩家不斷將個人活動增添至公共游戲平臺,以開辟新的游戲空間和劇情,對游戲進行多次重復開發。但自定義機制的涉及范圍不止于此。無論是網絡個人空間創建還是社交媒介個性化設置等領域,均存在著典型的自定義機制,玩家可以運用網站和媒介自帶的修改工具形成自己獨立的信息產品。自定義機制更加貼近玩家喜好,滿足了玩家不同的個性化需求,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一模式也成為了玩家向玩工轉變的紐帶之一。在玩家進行自定義修改和編程的過程中,原本純粹的娛樂和休閑行為開始具備生產性特征,玩家在設計和制作時耗費腦體勞動,即便并非受制于雇傭勞動制度之內,但其勞動活動實質上開始與專業工人趨同。而玩工通過自定義機制設計的產品可以看作依附于原商品的附加產品,因此,這一產品并不能歸于玩工個人所有。而在娛樂產業網絡化的大趨勢下,玩工對游戲的修改、網頁的創建、社交媒介的設置等實質上都是對原產品內容上的擴展。[注]Tiziana Terranova,Free Labou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Vol.18,No.2,2000.許多平臺在推出娛樂產品時還會開放豐富的評論、彈幕等功能,玩家簡單的娛樂和消費行為在客觀上卻增加了原商品的價值含量。除此之外,生產制作的大眾化也為產品的進一步更新和改進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設計理念,在知識產權保護涉及這一領域存在重重困難的局面下,廠家可以從中無償抽取玩工的腦力勞動成果。自定義機制實質上意味著娛樂產業的資本家僅僅通過對生產功能的開放便獲取了大批的非雇傭工人,玩工在將個人的制作參數等信息上傳到平臺時,便等同于將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無償轉移給資本家。從整體來看,當原產品的內容擴展或更新升級后,作為受眾的消費者依然是曾經作為生產者的玩工本身,資本家在節約了大量的管理、培訓等成本的同時,卻在無形間使得剝削的程度和廣度進一步擴展了。
另一種由玩工創制的附加產品則是個人信息。這一價值剝削體系除涉及產品廠商和消費者外,還通過廣告商發揮作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alker Smythe)就已經注意到了傳媒資本積累剩余價值過程中消費者群體的作用[注]Dallas Walker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3,1977.,盡管他錯誤地將受眾當做商品看待。玩家在通過網絡進行娛樂活動的同時,會通過網站注冊、資料完善、偏好統計等過程向平臺上傳個人信息,有時還會通過用戶反饋和意見問卷向制作商傳達產品體驗和發展建議。即便玩家并未進行刻意的信息傳輸,在互聯網強大的信息采集和加工功能下,廠商也可以通過對玩家的痕跡管理掌握玩家的喜好、位置、活躍時間等個人資料或隱私,有時甚至在利益驅使下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如暴雪、Facebook等公司就曾多次被曝出隱私泄露事件。一方面,由于信息傳輸類勞動也屬于生產性勞動的范疇,信息時代的玩家便類似于傳統交通行業中的運輸工人,盡管在平臺經濟時代,很多商品的傳播勞動所需要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極小,因此所產生的價值量也十分有限,但經過多次傳播后追加到信息商品中的價值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另一方面,平臺會將收集到的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形成分析結果并出售給廣告商,使廣告商可以根據用戶偏好和個人習慣進行“Feed模式”的分類和精準投放[注]吳鼎銘,石義彬:《社交媒體“Feed廣告”與網絡受眾的四重商品化》,《現代傳播》2015年第6期。。事情遠不止于此。在社交平臺網絡與游戲和其他娛樂活動深度融合的商業模式中,當玩家產生休閑或者購買娛樂產品的行為時,就會自動顯示在其社交網絡上充當廣告并進入傳播領域起到營銷的作用。娛樂廠商可以通過分析用戶偏好生產出更能刺激玩家購買的產品以對用戶的收入流向進行循環控制,廣告商也可以利用商業手段,刺激玩家的消費欲望不斷高漲,從而使其更加頻繁地購買和消費娛樂產品。從社會再生產的總體過程來講,廣告的有效性和力度的增強起到了加速資本流通的作用,因此,玩家在實質上,一方面充當了流通工人,通過信息傳輸和廣告制造幫助剩余價值實現;另一方面,則成為了廣告商的免費勞工。而最終,無論是玩工在信息創造和傳播過程中生產的所有價值,還是玩工作為最終消費者所讓渡的價值,都會被制造商、廣告商和社交平臺所共同瓜分。
(二)娛樂過程本身成為產品
在社會總體財富迅速增長和人們物質資料滿足度大幅提升的過程中,人們對精神文化產品的需求逐漸高漲,開始有大量的以往被看作玩家的群體進入競技、表演等職業領域,而相關的價值剝削體系也隨著產業資本向新領域的轉移而成熟起來。以電子競技行業為例,根據荷蘭市場研究公司Newzoo本年度發布的《2018年全球電子競技市場報告》,在2018年,全球電競的市場規模將達到9.056億美元,同比增長38%。同時,報告估算,今年全球的電競觀眾將達到3.8億人,同比增長13.8%[注]Newzoo:《2018年全球電子競技市場報告》,新浪看點2018年2月28日。。從電子競技產業的價值鏈來看,游戲廠商提供硬件支持,信息平臺和廣告商在賽事傳播和流通領域起到重要作用,核心內容的生產則歸屬于職業玩家。職業玩家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進行練習以保證競技狀態,在他們那里,游戲的趣味性已經成為次要,游戲在實質上已經成為了謀生的方式。在競技領域嚴格的規則下,娛樂行為被局限在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并且需要在短時間內進行高強度的勞動,已然超越了原本的娛樂內涵。當然,不只電子競技行業,其他體育、音樂、表演等行業也是如此,原本純粹作為日常娛樂的活動開始被影音記錄制成商品并廣泛傳播,并以直接售賣或廣告費的方式盈利,玩家也成為專業的雇傭玩工。由于信息商品的特殊性,廠商和傳媒資本僅需進行一次商品制成就可以通過簡單的復制、轉播等手段進行多次傳播,并出售給不同的受眾群體。因此,與實體商品相比,這些精神和文娛產品的制作的投入和產出比將更高,資本家可以付出較小的成本獲取更為高額的利潤。
而隨著視頻門戶網站和網絡直播行業的興起,玩工的工作方式也不再拘泥于競技范圍內。當員工注冊培訓、信息加工制作、轉播、廣告等程序完全可以由一個虛擬平臺集成時,玩工便可以便利地將自己日常的娛樂行為制成產品上傳至網站。這事實上意味著玩工就業的門檻更低,也就是說,更多的雇傭工人會被納入平臺的剝削體系之中。而這些職業玩家、視頻拍客、網絡主播等雖然會被支付工資,但一方面由于日漸降低的就業門檻,玩工間將會面對著比傳統行業更為激烈的內部競爭[注]劉皓琰,李明:《網絡生產力下經濟模式的勞動關系變化探析》,《經濟學家》2017年第12期。,且由于信息傳播行業流量和廣告費的重要性會產生更大的收入差距,少量被曝光的職業玩家和主播等的高薪酬并不能掩蓋更大群體玩工的悲慘現狀;另一方面,由于廠家和傳媒資本在信息傳播方面有著高度的主導權和壟斷性,玩工所創造的價值能否實現極度依賴于平臺和廣告商的營銷手段。同時,在這一領域,工會的力量發展步履維艱,員工很難具備有效的反抗力量,因而資本家在劃定薪酬標準時有著更為自如的決定權。與所創造的價值相比,員工往往只能占據較小的部分,財富大量流入產業和傳媒資本家手中。
四、兩極分化、異化與反抗
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和休閑時間開始具備生產特征和新型剝削體系的形成,意味著將出現較大機器時代而言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異化現象。但是,在平臺資本主義社會,由于信息技術的推動,休閑勞動化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更加深入地認識玩勞動和玩工的特殊性,探索新型的斗爭方式。
(一)玩勞動與兩極分化
從經濟角度講,將玩勞動納入剝削體系的最直接后果是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在傳統的雇傭模式中,資本家以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為剝削的主要來源和提高剩余價值占有量的手段,勞動強度的提高、工作時長的增加、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趨勢等都會造成貧困和失業問題以拉大收入差距。但是,將娛樂活動附以生產特征的價值剝削方式則主要依賴于剝削范圍的擴大。玩工作為產消者,看似處于自由的休閑和娛樂生活中,實質上卻相當于全天候地被控制在生產崗位上,產業后備軍的范圍也由于雇傭勞動制度的打破而無限擴大至全體大眾,出現了大批的非雇傭工人。非雇傭工人在名義上不能參與任何形式的價值分配,這就使得資本家在獲得了更為豐富的財富來源的同時也節省了高額的工資和管理成本。當然不只在生產方面,從消費角度來說,娛樂消費由于具備更強的主觀性,因此,相對于傳統實物產品來說更容易受到資本引導,玩家此很容易在廣告或其他營銷手段的影響下做出非理性消費,[注]福克斯,莫斯可:《馬克思歸來》,傳播驛站工作坊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47頁。從而使財富迅速積累到少數人手中。同樣,根據Newzoo發布的報告,全球已有22億游戲玩家,其中10余億玩家會在游戲上消費,2017年單年度消費總額已經達到1089億美元。
此外,上文所提到的行業內部階級力量的懸殊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從由制作商、平臺、廣告商、玩工等形成的整條價值鏈中可以看出,這相當于資本在保留了傳統的剝削方式的同時,又借由信息技術創造出了新的積累模式,價值來源、收入流向、分配模式等都在技術壟斷和硬性制度保護缺失的前提下向著有利于資本的方向發展,平臺和廠商通過對玩工的支配占有了社會的大量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愈發顯著。
不只是資本家和玩工之間,從職業玩家的生存現狀來看,玩工間的收入差距也較傳統行業要大得多,階級內部的分化趨勢也更為明顯。
(二)另一種視角的勞動異化
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講,玩勞動被剝削意味著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受眾面積來說,異化勞動的范圍都出現了進一步的擴展。馬克思認為,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原本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方式的勞動異化為強制性的、被壓迫的、為資本家剝削需要服務的活動,勞動產品、人的類本質和人的關系等都作為異己的力量與勞動者相對立。[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但必須看到,由于身處大機器工業時代,馬克思在對異化勞動進行考察時,也主要是以物質生產勞動為主要研究對象。被異化了的工人的勞動時間可以被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而剩余勞動時間是完全被資本家所占有的,對工人的生存和發展而言毫無必要的[注]梁豪:《自由時間的生成、異化與揚棄——馬克思時間辯證法探要》,《長白學刊》2017年第2期。。但在平臺經濟和信息資本主義時代,當產業資本和傳媒資本家通過網絡將玩勞動納入積累范圍內時,資本的觸角已經觸及大眾的自由和休閑時間,異化勞動的范圍也不再以是否處于雇傭勞動狀態為標尺。因此,除了從傳統角度研究異化勞動以外,我們還必須從休閑和自由時間的異化這一新視角看待問題。由于生產和消費、休閑之間不再具備明確的界限,因此,一方面,從時間角度來看,資本的入侵使得雇傭工人不再擁有純粹意義上的自由時間,工人原本用于學習培訓、休閑娛樂等的個人可支配時間均被異化為了資本積累的方式和手段,人進一步同自己的類本質相脫離對立,異化現象愈發具備普遍性;另一方面,從空間范圍看,平臺資本主義的存在使得雇傭勞動制度外圍的普通玩家也成了無酬工人,在互聯網技術下不再有人可以逃離被異化的命運。同時,在資本的利益和價值導向下,網絡原本具有的公共性、共享性等特點被很大程度上消解掉,無產階級無論是在分配還是在公共話語權方面都受到了資本最大程度的壓制。
(三)玩工的斗爭
新型的價值剝削形式給勞動者的反抗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困難。首先,由于玩勞動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因此,玩勞動的定性和定量問題在理論界尚未形成共識。玩勞動同時具備生產和娛樂的雙重特性,在客觀上也的確滿足了消費者的休閑需要,因此很容易受到資產階級理論家的詰難。其次,由于對玩勞動的剝削打破了雇傭勞動制度和階級的界限,形式也更為多樣和復雜,玩工間的職業性質、工作環境等往往有著很大的差異,很難形成有效的斗爭組織。而玩勞動的異化還意味著傳統反抗方式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工人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所爭取到的物質利益和閑暇時間等,都會通過娛樂活動中資本對玩勞動的剝削大批量地轉移回到資本家手中,資本家的控制力度和階級力量的傾斜程度得到了質的飛躍。因此,一方面,從理論上重新認識休閑活動勞動化這一過程就變得格外重要。肯定玩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地位,為合理認識玩工在價值分配中的作用做出指導,是研究這一新型剝削方式的首要工作。另一方面,產權的進一步明晰也將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對專業的雇傭工人來說,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在新興行業迅速建立法制保障和工會。但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隨著平臺經濟產業鏈的進一步完善成熟,通過玩勞動進行的剝削大眾化和異化普遍化的現象將更為明顯。因此,對于普通玩家來說,維權意識的提升是應對休閑與生產的矛盾,避免智力成果竊取的重要方式。當然,在普通用戶的維權意識尚為薄弱的情況下,公共組織和政府規制的力量就顯得格尤為關鍵,通過公共壓力和頂層干預,可以有效規制平臺與廠商的運營模式,對玩勞動所形成的知識成果做出產權上的界定減免糾紛,做出正確的價值引導并提高公共權力意識,使得斗爭的方式逐漸向網絡化、大眾化的方向發展。
五、結 語
在資本逐利性的驅使下,玩勞動異化和玩工的出現是平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資本家在追逐更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逐漸將剝削邏輯向更大范圍擴展。平臺的生產和剝削模式依托于成熟的信息集成和處理技術以及產業資本與傳媒資本的高度融合,由此為娛樂休閑活動的勞動化創造了條件。在我國,有關玩勞動的研究相對滯緩。誠然,玩勞動與玩工并非馬克思當年所重點關注的對象,但新型的勞動和商品形式、雇傭模式和剝削方式等都可以用政治經濟學原理加以解釋。特別是在工作場所由機器大工廠逐步向社會工廠演進,精神文化產品在人的發展和生產力進步中發揮顯著作用的信息社會,加深對玩勞動和平臺資本主義的研究便變得格外重要。關注玩工的生產與休閑狀態,抵制自由勞動的異化,將是我們最大限度地發揮互聯網的共享性與去中心化潛力,妥善處理產消者生產與休閑矛盾的重要之舉。